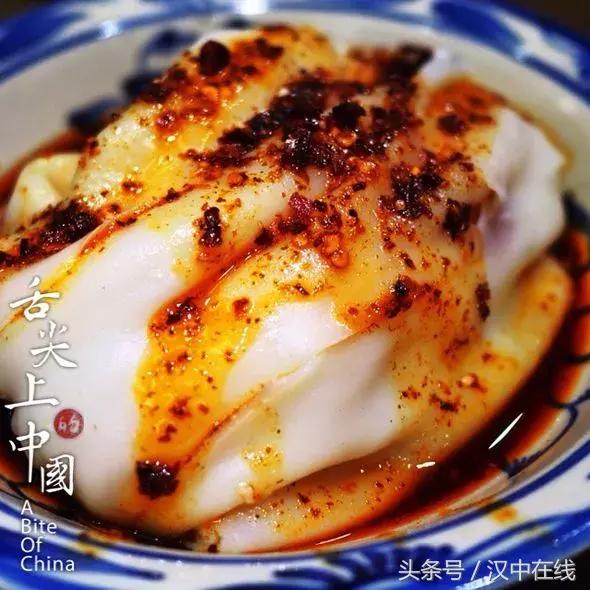劉夢溪沒學問?作者:中國藝術研究院終身研究員、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劉夢溪,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劉夢溪沒學問?以下内容希望對你有幫助!

作者:中國藝術研究院終身研究員、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劉夢溪
“誠”是中國文化裡面非常重要的價值理念,特别對一個人的修為和健全人格的養成而言,“誠”居于核心的位置。作為生命個體的人,總是内在有誠,外面才有信。誠信品質的建構,誠是先在的精神本體。“誠”而能立,精神的本我就自在自足了。故《易》之乾卦雲:“修辭立其誠。”而王陽明在面對一位即将離開京師返歸故裡的學人前來請益時,給出的也隻是兩個字,曰“立誠”。此事發生在明正德十年(公元1515),請益者為林典卿。林氏嘗聆聽過陽明的立誠之說,此次本欲請得能夠通天地古今的為學典則,以為終生教言,不料竟是早已聽聞過的“立誠”二字。林氏不禁追問說:以天地之大、星辰之麗、日月之明、四時之行,引類而言,不可窮盡;人物之富、草木之蕃、禽獸之群、華夏之辨,引類而言,亦不可窮盡;古之學者殚精竭智,尚莫能究其端緒,靡晝夜,極年歲,猶不能竟其說。難道僅僅“立誠”二字,就能盡其窾要嗎?陽明子從容答曰:“立誠盡之矣。”可知王陽明把“立誠”的題義看得何其重要,以至于認為不隻不可替代,而且不能增益。這緣于“誠”之義理在“六經”以及先儒著作中的特殊地位,在于“誠”之一字的執一不二和不息不滅的實理品格。此誠如二程子所說:“惟立誠然後有可居之地。”
誠者,天之道
《禮記》“中庸”篇,論“誠”最為透辟見義。其中寫道:“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所謂“天之道”,即自成之道、本然之道,非人力所能預為。而“誠之者”,則是人之所欲達緻的“誠”的境界,所以是“人之道”。朱熹解“誠”,提出“誠”是“理”,而且是“實理” ,即認為“誠”是獨立自足的價值理念,不失為理學家的特有貢獻。以此,“誠”作為一個學理之概念,必然具有先驗的特征,也就是“自然不假修為”,因而便成為自然而然的“天之道”了。此亦即朱子所強調的“誠是天理之實然,更無纖毫作為”“有一毫見得與天理不相合,便于誠有一毫未至”。主張“立誠”應終生以之的王陽明,在認定“誠”是“實理”的同時,更進而提出“誠是心之本體”。既然是本體,自然就無減無增了。然則“誠之者”或曰“思誠”是何所取義?陽明的解釋為:“思誠”是希求回歸“誠”之“本體” 。換言之,“思誠”就是想“立誠”,亦即對“立誠”的一種向往。但“立誠”不是離開本心,另立一個“誠”,而是回複到自心的本然之誠。回歸也可以視作“複性”。至于如何回歸,我以為孟子的“誠”論,可作為回歸之道。
孟子說:“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孟子·離婁上》)所謂“誠身”,就是修身以“立誠”。這與《中庸》所說的“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屬于同一義谛。“誠之者”,是為思誠之道。可見擇善、明善、向善,是通向“誠”之道的橋梁。所以孟子又說:“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反”即回歸,就是複其自身的本然之誠。因明善而複歸到自身的本然之“誠”,使“誠”之“體”與自身的性自體合而為一,此種境界,還有何不惬意、不滿足(慊)之有?自然“樂莫大焉”了。
此處需要和《禮記·大學》的“正心誠意”說互闡。《中庸》是孔子的孫子子思所作,《大學》相傳為孔子的高足曾參所作,不管其說的可信程度如何,兩書傳達的是為孔子思想,應無疑義。《大學》的開篇寫道:“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朱熹稱之為“綱領”,而格物、緻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朱子稱之為“條目” 。其“八目”的原文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緻其知。緻知在格物。”這是正推。反過來逆推則為:“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中國古代士人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這裡作了環環相扣、密不透風的邏輯推演。無論正推抑或逆推,都可以說是“修齊治平”的漫長道路,須是從格物緻知、正心誠意開始。“格物緻知”是獲得建立在自身經驗基礎上的知識能力,也就是需要形成因物即理(“即物而窮其理”)的認知自覺。“正心誠意”則是修身的要訣。《中庸》引孔子語:“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又說:“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義理和邏輯與《中庸》完全一緻。“知斯三者”的“知”,“知所以”則“知”的“知”,即格物緻知的“知”。這個“知”實際上是将大學之道的“三綱”“八目”,置于理性自覺的層面。換言之,“修身”是“治平”的前提。所以《大學》在反複推演“格、緻、正、誠、修、齊、治、平”的義理之後,緊接着總括地寫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
問題在于何謂正心?何謂誠意?正心誠意和修身究竟是何種關系?如果将《中庸》、《大學》兩篇之文義互相比勘參證,可知“正心”實際上是“修身”的結果和目标。就是說,“修身”的目的即在于使人心歸之于正。“正”者為何?乃歸之于善也。王陽明對此的解釋最為典要,他寫道:“何謂修身?為善而去惡之謂也。”陽明還說:“若區區之意,則以明善為誠身之功也。夫誠者,無妄之謂。誠身之誠,則欲其無妄之謂。‘誠之’之功,則明善是也。故博學者,學此也;審問者,問此也;慎思者,思此也;明辯者,辯此也;笃行者,行此也。皆所以明善而為‘誠之’之功也。故誠身有道,明善者,誠身之道也;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後世學者解亞聖(孟子)的“誠身有道”,以陽明的解釋最能得義之全體。孟子之“誠身”和《中庸》之“修身”,隻是語詞表述有所分别,義理之内涵則無不同。因為“修身”“誠身”歸根結底是為了達到“正心”。
“正心”的前提是“誠意”,即“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但就修身的全部義理内涵來說,“誠意”是單指,“正心”是全提。“好學”“力行”“知恥”是修身的途徑,“知”“仁”“勇”是身修之後的結果。而修身過程的完成,“知”“仁”“勇”的最終實現,全賴誠身與明善。誠身是終極歸宿,明善是回歸的功夫。《大學》的“明明德”,實即明善之意,而“止于至善”,則是“以修身為本”所達至的終極正果。而《中庸》的“誠意”,既是修身的起點,又是修身的歸宿。所以王陽明說:“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總之是在此一“善”。《中庸》第八章引孔子語:“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亦為此義。二程子也說:“能守善,斯可謂誠也已。”伊川(程頤)申而論之曰:“不誠無以為善,不誠無以為君子。修學不以誠,則學雜;為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志;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而況欲為君子者乎?故曰學者不可以不誠。”蓋伊川之論誠,可謂具體而微。“不誠無以為善,不誠無以為君子”,斯為誠之大道。而“修學”“為事”“自謀”“與人”,則是日用常行之小道。然即使小道,行之不以誠,亦難以成其事。
此蓋由于對一個人的修為而言,“誠”是徹頭徹尾、貫徹終始之事,不是此一事“誠”,他事可以不誠;或今日誠之,明日便可無誠。故《中庸》繼而又寫道:“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闡明“誠”的不間斷性。誠而有斷,不能貫徹終始,“誠”即歸之于無。而“誠意”一詞的意象,也可用彌漫周身、無有空隙來取譬。《易》乾卦文言引孔子之言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這是說,即使平常的言論和行動,也須謹慎而能夠取信,使得此誠常存而不留空缺,免得“邪”(非善)乘虛而入。所謂“閑邪”,就是讓“邪”閑置無用。故伊川說:“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于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是的,“閑其邪者”,就是給“邪”放長假,令其永遠休息。“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這些日常的言論與行為,亦即“庸言”“庸行”,最容易失去警覺,而給“邪”以可乘之機。如果這些方面都能夠做到謹慎小心,“誠”就會充滿自性的本體,變成性體之誠,使得“誠”無間斷、無空隙,周身皆誠,從而達到“自誠明”的境界。
“自誠明”的境界,是“誠”的最高境界,其哲學義涵可概括為“天之道”和“人之道”的渾成無隙,天道和性自體合一。所以《中庸》說:“自誠明,謂之性。”所謂“自誠明”,乃是性體因明善、守善、固善而通體澄明洞徹者也。
美意延年,誠信如神
《禮記·中庸》還有一段無法不予重視的話:“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所謂“至誠”和“盡性”,指的就是“天之道”和“人之道”合一的“誠”的極緻。達到此種境界,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同參。也就是達至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境界。換言之也可以說“誠”可通神。所以《中庸》又寫道:“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将興,必有祯祥;國家将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中庸》此處用“至誠如神”表達“誠”可通神的推思理路。
中國古代關于“誠”可以通神、“至誠如神”的話題多有。《荀子·不苟》于斯述論得尤為集中,其中一段寫道:“君子養心莫善于誠,緻誠則無它事矣。惟仁之為守,惟義之為行。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變化代興,謂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夫此順命,以慎其獨者也。善之為道者,不誠則不獨,不獨則不形,不形則雖作于心,見于色,出于言,民猶若未從也,雖從必疑。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為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為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為尊矣,不誠則卑。夫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類至,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操而得之則輕,輕則獨行,獨行而不舍則濟矣。濟而材盡,長遷而不反其初則化矣。”荀子于言,與《中庸》的“誠”論義有同歸。“養心莫善于誠”,即《中庸》的“修身”之謂。“緻誠則無它事”,可齊于《中庸》的“誠外無物”。“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變化代興,謂之天德”,即是“誠”可通神之意。而荀子在《緻士》篇提出的“得衆動天,美意延年,誠信如神,誇誕逐魂”的十六字判語,則直接将“誠信如神”提撕而出。王先謙注《不苟》“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句,認為“化”是為“遷善” ;《緻士》的“美意延年”四句,也以善惡為應,以“遷善”為養生的妙道。“美意”即善,善則情溫意平而親仁。故孔子有言,曰“仁者壽”。可見,荀子與孔門後學殊途同歸,同樣将“擇善”“遷善”作為通往“誠”的不二通道。
“至誠”之“誠”,不僅可以通神,按照朱熹的理解,還可以成為與自己的祖先建立精神聯系的紐帶。祭祀祖先誠然是傳統社會的祭祀大禮,其重要程度,僅次于朝廷的祭天。但“祖”有遠近,如果是祭祀“祖之所自出” ,即最早的初始之祖,古代有一個專指語詞曰“禘”。如果将遠近祖先一起祭奠,稱為“祫”,是為合祭之義。無論是初始之祖,抑或合祭之祖,都距緻祭的後人湮遠弗屆,甚至連牌主影像也早已無影無蹤,後來者的祭儀能達緻預期的效果嗎?《論語·八佾篇》也曾讨論及此,但孔子主要對魯國在祭祀時将僖公置于闵公之上的“逆祀”不以為然,所以對關于“禘之說”之問,回答是“不知也” 。朱子不同,他認為隻要心存“誠敬”,祖先的精神和自己的精神是可以相連接的。他說:“氣有聚散,理則不可以聚散言也。人死,氣亦未便散得盡,故祭祖先有感格之理。若世次久遠,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必竟隻是這一氣相傳下來,若能極其誠敬,則亦有感通之理。”又說:“祖考之精神魂魄雖已散,而子孫之精神魂魄自有些小相屬。故祭祀之禮盡其誠敬,便可以緻得祖考之魂魄。”總而言之,朱熹的意思可以用一句話概括之,那就是:“能盡其誠敬,便有感格。”我們需要注意“感格”這個概念。可知“誠”這個價值理念,“誠敬”之所立,具有怎樣的感通神奇的作用。此正如二程子伊川所說:“至誠感通之道,惟知道者識之。”無論求之于“事”,還是求之于“理”,朱子之為“知道者”,其誰曰不然!
這裡,不妨行筆至宋,看看周子濂溪(周敦頤)對“誠”所作的特殊解讀。周平生為學著述不多,主要以《太極圖》和《通書》名世。而後者實是對前者意蘊的疏通、解說和著論。此兩著本身的學理義涵此處暫不置論,姑專門拈出其“誠”說,以俟知者。《通書》說誠共有三篇:一、誠上;二、誠下;三、誠幾德。每篇字數寥寥,但對“誠”所作的義理闡釋,可謂另出手眼。
首先周子提出“誠者,聖人之本”的理念。他引《易》為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蓋周子的思想,悉本諸《易》,故直接從《易經》裡引出了“立誠”的學說。朱熹對此解釋道:“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人皆有之,而聖人所以聖者無他焉,以其獨能全此而已。”朱子這裡所強調的“誠”為“天所賦、物所受”,即“誠”為天之道、思誠為人之道之謂。而認為聖之所以為聖,全在一個“誠”字,“誠”是聖人之本,則是周子的發明。今本《通書》,朱子的“解附”與之并傳。因此讀《通書》自當參酌朱子之解。而朱子采用的是“以周解周”的義法,故開卷即随順周說,而單标“誠是太極”。這緣于他對“誠”,對《太極圖》的義理内涵的理解。“太極”一語最早出自《易》之系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圖》開篇亦雲:“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 “無極”一語見于《老子》第二十八章:“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常得不忒,複歸于無極。”王弼注“無極”為“不可窮也” ;釋“太極”為“聚有之所極”,是“無稱之稱,不可得而名”。依王注,也可以說“無極”是“無”之極,“太極”是“有”之極。“無極而太極”則是從“無”到“有”之謂,也可以理解為“無”中生“有”。因此朱熹将“誠”歸結為太極,是為最得周子義理,同時也将“誠”提升到“實理”的極緻的高點。
周敦頤還提出誠是“純粹至善” ,這和《中庸》的“擇善”“明善”,《大學》的“止于至善”,以及《荀子》的“遷善”,一脈相承。蓋“善”是“誠”的德品性向和性體歸宗,不能有不善摻雜其間,否則,雜則不純矣。故《易》之系辭有雲:“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猶言宇宙萬物的陰陽變化之道,唯善者能夠承繼開通,而成就此道則是本性所使然。周子“誠”說的第三篇為“誠幾德”,也還是申論“善”對“誠”的性體約定。“誠”是本來如此的性體之自然,不借助表達,也無關對事體真相的訴說,因此“誠”隻是誠,無為而自在。“誠”與“真”不是一回事,“真”不等于“誠”。周子說“誠”是無為,可謂谛言。而在讨論“聖”的時候,他又給出了“寂然不動者,誠也”的結論。“誠”既然“寂然不動”,當然就是無為了。
然一旦涉動,即使是極其微小的“動”,哪怕是念瞬之間,也有善惡的趨導和棄取從事的問題。“善”不等于“誠”,但沒有“善”的固化,“誠”作為性體之德,便瓦解變易了。善使“誠”變而成為活潑潑的實理之體,鸢飛魚躍,不害其誠;相反,如果離開善的導引,“誠”就變而為“死誠”,實即“誠”死,也就是沒有了“誠”的存在。“幾”是至細而微的意思,一旦涉“幾”,已是有“動”萌焉。故《易》之系辭寫道:“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 《易》道正是通過察微識“幾”,來見得吉兇之兆。所謂《易》乃“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的斷判,就是指此而言。然而吉兇之兆,也就是善惡之端。此正如周子濂溪所說:“不善之動,妄也。妄複,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矣。” “誠”是“無妄”之謂,朱子、二程子,均如此持論。但前提是戒絕“不善之動”。故周子又言之曰:“君子乾乾,不息于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後至。”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即使萌動之初而未見斯善,隻要察微識“幾”,及時“懲忿窒欲”,打消妄念,改過遷善,重啟善端,仍然可以還“誠”一個生生不息。所以朱熹稱濂溪此論為“思誠良方”。
修辭立其誠
周子《通書》所闡,全為《易》理。而《易》之涉“誠”,最有名的話,莫過于“修辭立其誠”。《易》之為典,何其淵默高深,難測其奧。而展布“誠”之意蘊,竟出之以“修辭”,此胡為乎?為不失文義之整體,且征引主詞連帶之上下全文,以備查覽。
乾卦之九三爻辭雲:“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乾卦“文言”引孔子的話對此解釋道:“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矣。”
如果将這段話翻譯成明白易曉的白話文,應該是:“君子為人為事,每天都自強不息,無一刻松懈,到了一天的晚上,還嚴格反省自查,看是否有所疏漏,這樣才能避免過失。為什麼要這樣呢?孔子說,一個有修養的人進修德行,成就功業,靠的是忠誠與信義,因此言辭的表達,應該以誠為本,非如此不能站得住腳跟。隻有對此有透徹的認知,方有資格讨論将發未萌之時可能出現的問題;能做到結果未出現時就能預知最終的結果,這樣的人才值得與之研究義理。由于知道最終結果,所以處于上位,也不敢驕慢;處于下位,因知其将變,亦可無憂。也就是說,隻要自強不息而又時時懷有悚惕之心,雖然遇到危難,也不緻沒有轉機。”
我用的是意譯的方法,自問與原文本義能夠相符而不至相悖。由于這段話是對乾卦倒數第三爻的解釋,所以“上位”指的是下卦之上,“下位”指的是上卦之下,都是位将移而兆已萌的時刻。白話轉譯為避免枝語繁奪,未将卦體之象典指實,茲特此說明。然則“修辭立其誠”的義旨,究系因何而立焉?我以為在《易》道裡,固是直接“立誠”之義,同時也是立“忠”之義,又是立“信”之義,亦即“誠”是為了盡忠取信。
中國傳統的“人”論,從不把人視為孤立無援之屬,而是在與他人的關系中彰顯“人”的本性。《孟子》、《中庸》以“人”解“仁”,曰“仁者,人也” ,即是明證。蓋“仁”者,二人之謂也。如果說進德修業靠的是忠誠與信義,那麼要讓所成就的事業站得穩腳跟,就離不開與他人的交往對話,離不開交往對話中言語文辭的端忞誠信了。實際上,這是孔子的一貫思想。《論語》直接講“誠”的地方不多,分疏言語文辭和取信的關系,例證不勝枚舉。最典要明捷的話,是“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論語·學而》),以及“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為政》)。前者雖出自子夏之口,想必為夫子所認可。也許孔子是太深知文辭語言對一個人生平志業的成敗所起的作用。所以他主張,發為言辭要極端謹慎,一再強調要慎言,與其說,不如不說,能夠後說,就不要先說。《論語·學而》寫道:“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為政》章又說:“多聞阙疑,慎言其餘,則寡尤。”《顔淵》章司馬牛問仁,孔子說: “仁者,其言也讱。”“讱”即難于出口也。司馬牛追問說,難道這就是“仁”嗎?孔子以反诘作答:“既然做事情不容易,說話就那麼容易嗎?”此亦即發為言辭,應斟酌再三之意。還有一次,孔子說:“我甯可不說話。”子貢大惑不解,傻傻地問:“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論語·陽貨》)孔子有些不滿地反問他:“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可知夫子之言之慎也。
孔子所以教弟子慎言,是因為孔子知道言之重要。至于重要到何種地步?孔子認為,有時可以重要到“一言而興邦”“一言而喪邦”的地步。當然須是話題涉及如何“為君”的問題。孔子說,如果君的言論是好的,自然不該違背,但如果是不好的,也不準違背,就可能“一言而喪邦”(《論語·子路》)。在另一處孔子還表示:“惡利口之覆邦家者。”(《陽貨》)因能言善辯而喋喋不休,以緻說得口滑,無所顧忌,是為“利口”。這種以逞口說為能事的人,如果得到重位,就可能危及邦國的安全,所以孔子非常厭惡。鑒于孔子對人的長期觀察,他得出一個近乎獨斷的結論是:“巧言令色,鮮矣仁。”(《陽貨》)又說:“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裡仁》)還說:“巧言亂德。”“巧言”就是聽起來讓人感到舒服的話,“令色”則是做出一副讨人喜歡的樣子。此種言說方式與說話時本該如此的“直言正色”适相反對。孔子對這種言說方式,不僅斥之為不德乃至亂德,而且以之為恥。
發為言辭所以需要審慎,還由于言行需要一緻,需要統一,而不能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如果話說得很大,誇張為辭,而在行動上不能跟上,這種情況在孔子看來,屬于“言而過其行”,應該是一件很可恥的事情。“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裡仁》),即為此義。所以甯可“讷于言而敏于行”(《裡仁》),或者“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為政》)。然而人總有疏忽的時候,如果稍不留神,一旦說出來了怎麼辦?那就要說到做到,用自己的行去兌現自己的言。但最好是先做後說,或者做了也不說。當然重要的是,既然說了,就要在行動上體現出來,亦即“言必信,行必果”(《為政》)。“行”是“言”的鏡子,真僞、虛實、妍媸,鏡子的反射,令其毫發畢現。
所以如此,是由于慎言可以少犯錯誤,言多則容易賈禍。一次子張問如何才能當好官,孔子的回答是:“多聞阙疑,慎言其餘,則寡尤。”(《為政》)行動也要謹慎:“多見阙殆,慎行其餘,則寡悔。”(同上)如果真能做到了“言寡尤,行寡悔”,孔子認為“祿”就在其中了。這等于給出了為官的秘訣。然又不止于此,如果事關家國天下的利益,“言”之所影響者更其嚴重。《易》的系辭引孔子的話警示說:“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周易·系辭上》)所謂“密”,就是要守住自己的口。君是否失臣,臣是否失身,關鍵在于能不能守口如瓶,做到“慎密而不出”。言不出口,何據之有。隻要不說話,“慎密”自然不在話下。《易》之為言。以言語為“亂階”,試想這是何等重大判斷,充滿了神秘的政治警示意味。
由此引發出另一個命題,即在人與人言語交接的時候,如何聽言、察色和觀行。孔子在這個問題上顯然有過教訓,所以他說:“始吾于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論語·公冶長》)言的作準不作準,隻有通過行動來驗證。而當一個人發為言說的時候,絕非孤獨者的自語,而是有他者在場的交流互動。故言說對象的身份、場域,包括場景的氣氛,彼此心理變化和詞氣語調,都是言論者不能不顧及的因素。孔子所說的“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 (《論語·顔淵》),就是指此點而言。“慮以下人”是謙退之意,即在說話的時候不要高人一等,盛氣淩人。“觀顔色”則是明其所關注的問題,對症下藥,切中底裡。所以如此,是由于一些佞人會虛飾自己,假裝以仁者的面貌出現,“色取仁而行違”(同前),我們不能聽任其僞而不予置疑。此不僅涉及察色聽言,實亦觀人矣。察色是為了知言,觀人是為了知人。隻有既知言又知人,才能成為一個“知者”。
孔子說:“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論語·衛靈公》)我們的目标,當然是希望做到既不失言,又不失人。茲可見斯旨之深遠重大。所以孔子說:“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隐,未見顔色而言謂之瞽。”(《季氏》)是謂在一個有道德修養的人面前,如果還不到講話的時候,就開始講論,這是急躁傲慢的表現;而在應該講話的時候,卻隐而不發,容易被視作隐瞞;至于在講話的時候,完全不顧對方的面容氣色,自己在那裡亂說一氣,無異于盲目者的言說。《荀子·勸學》亦雲:“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隐;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措意與夫子相同。
言語文辭所影響于人生社會者也大矣。故《易》道有雲:“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樞機”也者,是謂轉捩變遷之關鍵,對一個緻力于進德修業的人而言,能不慎乎,能不慎乎。
但言行導緻的是榮譽抑或恥辱,主要在于言說的善與非善。故《易》道又雲:“‘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裡之外應之,況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裡之外違之,況其迩者乎?’”這是說,言辭的影響傳播,弗遠不屆。即使在戶庭中發為言辭,如果是善言,千裡之外也會響應;反之,如果是不善之言,即使是千裡之外,也會不以為然。所以如是者,是由于言的善與非善,直接與吉兇相關。而善與非善,與有誠存焉與否直接相關。俗雲:“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史家所緻意的言語足可賈禍,豈是虛語哉!然“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易·坤·文言》亦雲:“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則《易》道所謂“忠信所以進德也”,所謂“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易》之系辭下傳在即将結尾之時,對《易》之為道再次予以揭明,鄭重告知世人:“《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纣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無咎。此之謂《易》之道也。”殷周興替,革故鼎新,前朝之失,曆曆在目,所謂殷鑒不遠。故《易》之為作,“其辭危”。新朝之興,縱有“盛德”,亦當慎之,戒之,懼之,以使之“無咎”。人豈能無咎,所謂“無咎”,無非是“善補過也” 。因此無論一個人,還是一個國家的行政,言善令美,是為達道。善言美政,無有不應。但前提是“修辭立其誠”。隻有心體性體立之以“誠”,方能做到不經事先設計,美言自然噴流而出,也就是無為而無不為。立誠而言善,則能避兇趨吉,最終實現“居業”,即人們所希冀的安居樂業。善言的要義在言之有誠,不等于一味地說好話。凡有益于進德之言,有助于修業之言,能夠使民得以安居之言,有助于“補過”之言,都是善言。相反,肥辭谀語、言不由衷,絕非善言。善言有時逆耳,但逆耳卻可以滋潤于心。此在《易》道,是為顯例。《易》之危辭警語,豈是聞之即感耳順之言辭耶?然警語令人警醒,危辭可讓人趨吉避兇,實為至誠至大至精至善之言,或如《易》之系辭所雲,乃是聞之能使人“先号咷而後笑”之言,豈可輕哉,豈可輕哉。
故《易》道重複為說曰:“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前引周子之誠論,亦有“誠”是“聖人之本”的說法。此即“誠”的心體是否得以樹立,隻能因辭以見乎情,由辭而觀其“誠”。《大戴禮記·文王官人》章,嘗有“觀誠”之說,其中寫道:“省其居處,觀其義方;省其喪哀,觀其貞良;省其出入,觀其交友;省其交友,觀其任廉。考之以觀其信,挈之以觀其知,示之難以觀其勇,煩之以觀其治,淹之以利以觀其不貪,藍之以樂以觀其不甯,喜之以物以觀其不輕,怒之以觀其重,醉之以觀其不失也,縱之以觀其常,遠使之以觀其不貳,迩之以觀其不倦,探取其志以觀其情,考其陰陽以觀其誠,覆其微言以觀其信,曲省其行以觀其備成,此之謂‘觀誠’也。”此段細詳,未免繁缛,繁缛則鑿矣。重要的是“考其陰陽以觀其誠,覆其微言以觀其信”兩句,是為大《易》之至道也。通過“微言以觀其信”,實即察看“修辭”是否已“立其誠”。
關于此一層義涵,《易》系辭下傳的結尾一段尤堪玩味。其詞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兇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兇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兇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兇,或害之,悔且吝。将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遊,失其守者其辭屈。”本篇屢引明人來知德瞿唐先生之《易》注,于此處來先生則解釋雲:“相攻、相取、相感,卦爻險阻之情固不同矣,至于人之情則未易見也。則人心之動因言以宣,試以人險阻之情,發于言辭者觀之,蓋人情之險阻不同,而所發之辭亦異。”于是便有了各種不同的人的各種不同的言辭的表現。譬如将要背叛的人,說出話來難免有羞慚之态;心存疑慮的人,語言顯得啰唆枝蔓;樸厚善良的人,常常寡言少語;急躁而缺乏涵養的人,往往話多;存心誣蔑良善的人,說起話來會遊移不定;沒有操守的人,言談的表情會露出一副卑躬屈膝的樣子。
總之言辭的“誠”與不誠,心機的“善”與不善,可以依稀從言說的方式和言者的表情裡察看出端倪。所謂情見乎辭,實為見道之斷判。“何謂知言?”孟子設問之後回答說:“诐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孟子·公孫醜上》)言談之間,藏着,躲着,喋喋不休,胡言亂語,都是心無誠的表現,終瞞不過“知言”者的法眼。故因辭而察情,由見乎情之辭來觀“誠”,便是順理成章之事了。(來源:中國文化報)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