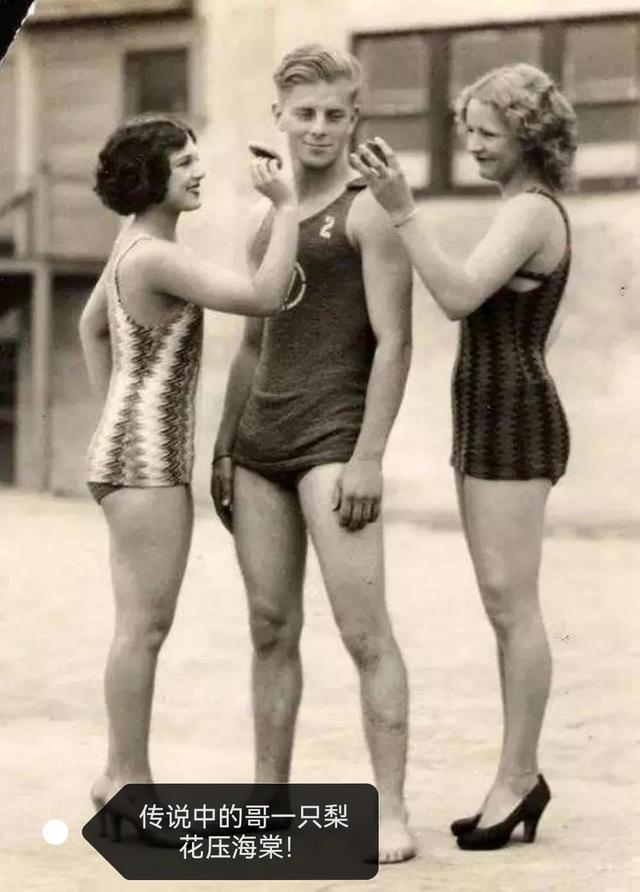“你見過譚鑫培嗎?”這就是譚家第六代譚孝增的言論。
譚孝增先生的談話是這樣說的:“還有一個論斷就說,譚家一代不如一代,覺得後代人丢了譚家人的臉似的,這個論點我也得說說,你們見過譚鑫培嗎?”

譚孝增先生
這叫啥邏輯?先不說譚鑫培是您老人家的先祖,就是外人這樣說也是于理欠妥!滿屏幕都是酸氣,讓人覺得既沒有道理又匪夷所思!
我們理解前輩先賢大師的好,就不能通過方方面面來了解,非得親自去見了才算數?那可壞了,看來我們哪天要是說屈原、李白、蘇轼的好,我們還得學會穿越,因為沒見過呗!
呵呵,你們自己好像覺得沒有丢譚家的臉,那麼為什麼觀衆會說你們丢了臉呢?不從自我找原因,還憤憤不平地指責觀衆,這樣做實在是讓人覺得于理不通啊!

帥哥譚正岩
再說了,你說觀衆沒見過譚鑫培,無非意思老譚你們沒見過,你們怎麼知道我們不如他?是吧,可是還有一句話說得有道理,那就是刮風下雨不知道,自己幾斤幾兩不清楚嗎?何必說出這樣的話,即有侮先人還讓别人更看輕了你們。
說起這不争氣的潭門後人,我們再說說他們的先祖号稱“伶界大王”的譚鑫培先生。
今天的觀衆是沒有見過譚鑫培,但譚大王可留有唱片存世,雖然隻有八張半,并且以當時的錄制水平音質之差可想而知,但就這樣的資料,我們今天的人聽了老譚的唱,其韻味,其勁頭,以及嘴裡的功夫,字音的把控,那都讓人非常的吃驚,如果老譚今天活着,以現在先進的錄音設備還原他老人家的唱腔,那得多麼地震撼!

譚門先祖譚鑫培先生
還有,那時候唱戲,沒有國家給開工資這一說,你荒腔走闆照樣有人往台上扔茶壺,不管你是誰,台下觀衆是用真金白銀來看戲的,你糊弄他們可不慣着你!還有譚大王時不時地還得去宮裡給慈禧老佛爺唱戲,據說慈禧看戲特别苛刻,拿着唱本對着台上的藝人,手裡拿着懷表掐着時間,戲唱幾刻就是幾刻,多一分少一秒都不行,前幾天有豫劇粉問為什麼京劇講究,這是太後老佛爺給訓練出來的,你不講究行嗎?
譚鑫培先生在當時的影響,名氣之大今天的人不可想象!國學大師梁啟超先生有詩雲:“四海一人譚鑫培,聲名廿紀轟如雷”,他除了号稱“伶界大王“這一稱号外,還有一個綽号:“譚貝勒”。

眼光犀利有王者之氣的譚貝勒
“譚貝勒”這個綽号的由來,也是由于他的藝術實在是高超,太後又喜歡他,底下人也跟着捧他,于是到了他老年的時候,名氣已經達到了空前的地步,那時候,他家道也很殷實,不必為了幾兩銀子去天天唱營業戲,哪家大戶如果唱堂會,把譚老闆請來竟然成了一件無上光榮的事情,以至于,到了後來即使重金來請,老譚也不一定去。
有個“那桐屈膝”的故事,就特别能說明問題,事情是這樣的:
因為譚大王的聲名日隆,所以請他唱堂會成了一種有身份的事情。那桐是大清朝光緒年間部長級别的官員,據說有一次那桐為慶親王府堂會做提調聯絡人。
其實他事先與老譚已經商量好了,請老譚演他的代表作,拿手好戲《定軍山》。結果老譚演完了以後,大家都覺得特别好,還吵吵的想看,就私底下和那桐說:你趕快去和老譚再商量商量,再演一出《打棍出箱》吧。

年畫《定軍山》
結果那桐到後台和老譚一說,老譚就有點兒不樂意了,一方面《定軍山》這出戲是靠把戲,演完了很累,而《打棍出箱》雖然不紮靠,但也是一出在台上一會也不消停的折騰戲,演完更累!另一方面,老譚這時候正紅得發紫,太後老佛爺對他都愛護有加,王公大臣們見了他都客客氣氣的,所以他根本也沒把那桐放在眼裡,但是呢,又不好直接回絕,于是開玩笑地随口說:“演也行,您要是能給我跪下,我就演。”

譚鑫培先生演《定軍山》
他本來是句玩笑話,意思給那桐出個難題,這事就拉倒了,沒想到那桐二話不說,直接“窟通”一聲就給譚鑫培跪下了,這下給老譚鬧了一個大睜眼!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伸手也不是,不動彈也不是,臉上表情很尴尬,可是那桐不但不覺得丢人,還笑呵呵地看着老譚,不說話,老譚略微一遲疑,伸手把那大人扶了起來,歎了口氣無奈地說:“好吧!”自那以後京城裡的這些達官貴人私下裡就說,這老譚厲害了,好家夥,王公大臣都給他下跪磕頭,這不成了王爺貝勒了嗎?于是這個“譚貝勒”的名聲就傳開了。
其實譚鑫培的名氣大,主要還是和他的藝術高超有關,如果他的藝術不行,也不會有那麼大的名氣和地位,那都是人家的真本事換來的,沒有能耐,那麼你玩兒出什麼花活都不好使!因為玩意兒這東西騙不了人,你生氣也罷,感歎也罷,那都沒有用,因為台下“座兒”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是鑒賞者評判者,說了才算數。

歡迎關注荷露團珠談戲說戲聊戲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