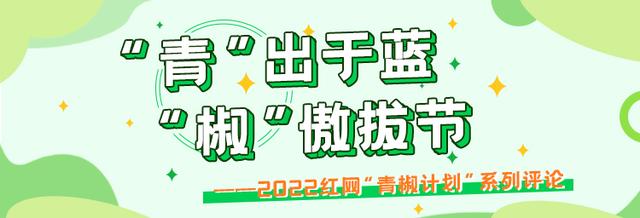
□黎芷筠(重慶大學)
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潘越提出議案:發現被拐婦女知情不報者,應追究法律責任。
一直以來,知拐不報者都是打拐行動的最大障礙。一些人或對買賣婦女行為視若無睹,放任自由,或自甘充當買家的“眼睛”,替其監視被拐者,更有甚者,還與買家聯手欺瞞警方、阻止搜救任務。他們是橫在被拐婦女與美好世界之間的一堵牆,這堵牆一日不除,營救被拐婦女的任務便舉步維艱。
讓“知拐不報”變為“知拐敢報”“知拐就報”,關鍵在一“利”字。人都是趨利避害的,這是物種得以延續的基礎。研究表明,人在判斷是否做某事時,主要受兩個因素影響:感知價值與感知風險,前者是衡量做了這件事能給當事人帶來什麼好處,後者是衡量做這件事需要承擔多大的風險,當前者大于後者時,當事人會選擇去做這件事。
發現婦女被拐,有些人為何知情不報?并非是他們全無良知,而是在他們所處的環境中,“不報”比“報”更“劃算”。拐賣婦女一般發生在山窮水惡之地,這裡的人們普遍收入水平不高、知識涵養較低、求取配偶難度較大,加上交通不便導緻的執法難度大,他們很容易将人情置于法理之上,此時知情者若是選擇告發,他們所能預感到的實際利益寥寥無幾,而可能失去的卻是親族之間的信任、他們賴以生存的東西,這種情況下,要他們自覺舉報無疑難如登天。
改變“知拐不報”還需“懲獎并舉”。一方面,懲治不報者以增加不報的行為風險,而出台相關法律法規,無疑是最好的選擇。法律出台,一可以懲治涉事人員,起到警示作用;二可以達到普法目的,促使相關人員更多地了解法律,以上兩點都有利于糾正“人情大于法律”的錯誤思維。但不可否認的是,該項立法具有困難。首先對“知情”的判定就是難題,是否知情屬于個人主觀思維,難以界定,由此引申出第二個難點——為了防止誤判,懲罰不應過重,應留有糾正彌補的空間——但懲罰過輕又無法達到懲戒效果,這其中的“度”如何把握,更需要小心摸索。
至于提升利益,即對舉報者進行獎勵,當獎勵額度足以使知情者對價值的渴求大于對風險的擔憂時,他們就會有強烈的舉報意願,同時再配以相應的舉報機制,如匿名舉報、電話舉報等,進一步降低其可能承擔的風險,使舉報更具可行性。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