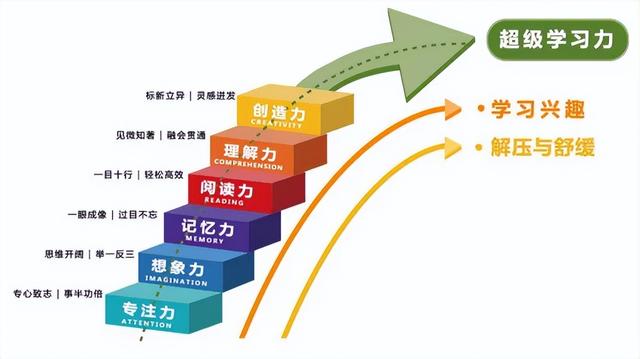《從容的夫君》
即使知道眼前這位落魄的少年将來會權傾天下,我也要向他退婚。
上一世我對他一見鐘情,費盡心機将他從牢中救出,又陪他走過雨雪風霜的七年,不成想最終卻落得個被人厭棄、滿門抄斬的下場。
重來一世,我早早收了真心,他卻像是變了一個人似的,對我百般體貼,精心呵護,甚至紅着眼睛問我——
“阿筝,你當初不是說過心悅我,會一直一直對我好的嗎?”
我隻是靜靜地看着他,後退了一步。
“人是會變的。我從前喜歡你,那是我眼光不好,現在我改了。”
“還有,公子請自重。公子該稱我一聲聞娘子,阿筝這樣親密的稱呼,以後是萬萬不能用了。”
本故事來源于知乎

1
我從夢裡醒來,思緒還有些昏沉。
一閉上眼,我死前的那一幕還曆曆在目。
我死前的那一天,江言帶人去抄了我的家。
他穿着紫色官服,俊雅的臉上是泰山崩于前也不改神色的淡定從容。
從前我最愛他的這份從容。
而我死前,最恨的,也是他的這份從容。
我跪在他面前,求他再想想法子救救我父親,他隻是從容地、慈悲地拂開了我的手。
他讓我不要管這些。
他說無論如何,我還有他,我是他江言的妻子,無論如何也不會牽連到我,這便夠了。
他說話的時候,他的平妻、年少時的白月光就站在他身旁,笑意溫軟地給他遞過一碗甜湯。
而我一睜開眼,年少時的江言就站在府門外,白雪落滿了肩頭。
這是景明四年的冬日,大雪皚皚。
這一年,江言從松江縣遠赴京城,一舉成了探花郎,又在華亭寺遇見了馬車失控的我。
十八歲的江言一劍幹脆利落地砍斷了車轅。我向他道謝,他隻遙遙還了一禮,輕描淡寫地說着不用。
這一年,他年少有成風頭無兩,奈何得罪了不該得罪的人,被人當成了替罪羊,構陷入獄。
而我——
這一年的我喜歡江言,我對他一見鐘情。
我出身将門,自小跟着爹爹在塞北長大,看慣了塞北的孤煙落日,第一次瞧見這樣白衫青袍,青松修竹般的少年。
他那一劍不僅砍斷了車轅,也照進了我心裡。
也因此,在他锒铛入獄、無人相幫時,我翻過圍牆,從府裡偷跑出來去看他,為他打點獄卒,為他送衣送食。
這一年,我闖上金殿為他求情。
我把我收集來的證據擺在聖上面前,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可與他的罪名實在是太大了,聖上也是真的動了火氣,甯願錯殺也不願放過。
我沒有法子,隻好跪在了鳳儀宮外,告訴皇後娘娘我心悅江言,求她去替我說情。
皇後是我的姨母。她向來視為我親女,對我寵愛有加,自然見不得我這樣。
我在雪地裡跪了整整一日,不僅給江言求來了從輕發落的恩典,還給自己求了道賜婚的聖旨。
我知我父兄不喜江言,也依舊捧着一顆真心、滿心歡喜地想要嫁給他,卻不想最終落了個被人厭棄、滿門抄斬的下場。
而這一次,重來一回,依舊還是景明四年,江言還在門外站着,而我已經琢磨起了退婚。
我重生的時機有些不巧,賜婚的聖旨已經下來,江言也已經從牢裡放了出來。他接了聖旨、又聽聞我闖上金殿替他求情的消息,這才來我府裡道謝,想要見我一面。
若是我重生的時候能夠再早一些,回到江言剛下獄的時候,我定然不會再救他。
許是我實在思索得太久了,丫鬟玉煙揣度着我的神色,試探地開口:「小姐,江公子在府外站了這麼久了,咱們要不要出去看看?」
「見什麼見,不見。」
我攏了攏披風,差人打發了他,隻說我因為在宮裡跪得久了,病了。
隻是我沒想到江言竟然那般的有毅力,他見不到我,便日日都來我永甯侯府外站着,一站就是好幾個時辰。
我父親江慮着流言,最終還是讓他進了府,我也還是見了他。
這倒是和上輩子不一樣。
上輩子我聽聞他在府外,便興高采烈地溜出了府見他。
那時候我滿腔的少女情愫,隻知道擔憂他好不好,見他無恙,又隻會一個勁兒地傻笑。
而他則恭敬又疏離的向我道謝,提起賜婚的聖旨,神情更是複雜。
「承蒙聞娘子厚愛,聞娘子大恩,江某不敢相忘。然,江某對娘子無情誼……」
如此直白的話語。
我那時怎麼說的來着?
哦,我那時楞了愣,然後傲然昂首,朗聲一笑。
「江公子現在對我并無情誼,不代表以後也對我并無情誼,不是嗎?」
——那時的我終究還是太過驕傲,不懂得放棄,更不懂愛與不愛這種事情向來不能強求。
想起以前的事情,我揉了揉眉心,有些厭煩了。
「江公子今日過來,若是隻是想向我道謝,那必不必再留了,我身子還有些乏……」
「至于賜婚一事,确實是我魯莽。我知你不願,等過段日子,我自會秉了聖上把這樁婚事取消。」
我說罷,轉身欲走,他卻忽地拽住了我的袖子。
「誰說我不願意?我願意。」
「能與聞娘子結為夫妻,江某三生有幸。」
我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睛,又見他緩緩從袖子裡掏出了一小罐傷藥來。
「這是用我家祖傳藥方制得藥,對止血化瘀有奇效,聽聞娘子為了江某在鳳儀殿外跪了幾個時辰,特意帶了藥來。」
「還有,最近這天越來越冷了,小姐受了風寒,需得按時吃藥才是……」
他又掏出了一包蜜餞來。
是城西的全聚齋獨有的,出了名的好吃又難買。
我向來最喜歡吃他們家的蜜餞。
上輩子同江言成了親後,我也常常差人去買。
我還記得有一次我害了病,那湯藥又實在太苦,我躲着不想喝,江言就去替我買了些來。
他這人向來重規矩,也總是有很多大道理可以說。他不喜歡我喝藥時配蜜餞,卻依舊替我買了遞到我嘴邊,神情無奈:“這下可以吃了吧?”
這也算是我們之間為數不多的溫情時刻了。
我看着這蜜餞呆了呆,一個駭人聽聞的念頭從腦子裡跳了出來。
江言他……不會也重生了吧?!
2
我被我這想法吓了一跳,可轉瞬又覺得不應該。
即便江言他真的和我一樣重生了,也不該是這樣的态度。
他若是真的重生了,隻怕是恨不得離我越遠越好,好讓他去尋他的白月光,同她雙宿雙飛。
那他現在這般又是為何?
我想不明白,可無論如何,這婚還是要退的。
經了上輩子那七年,我再也沒辦法對他升起任何期待了。即便那些事都還沒發生,我也不想再和他有什麼牽扯了。
打發完江言後,我轉身回了前廳。
前廳裡,我父親和我阿兄正面對面飲着茶。
見我進來,父親重重把茶杯往桌上一放,從鼻腔裡冷哼了聲。
“見過人了?”
我父親是嚴父。
我出生後沒多久便沒了娘親,從小跟着父親在塞北長大,父親治軍嚴整,殺伐果斷,對我也十分嚴格,可以說,我是被他拿着棍棒揍着長大的。
我的脾氣也和他一樣,十足的倔。
也正是因為這樣,上一輩子,在他因為我的任性妄為而責備我時,我才會挺直了腰闆,跪在地上和他嗆聲。
那時候的我還太小,不明白他們的一片苦心。
而現在,我又是心酸又是無奈地上前拽住了他的袖子,拉長了聲音:“父親——”
他瞬間便僵直了身子,帶了幾分無措。
“筝兒,你......”
我阿兄也放下了茶盞,他抿了抿唇角,重重歎了口氣。
“父親,筝兒也大了,她向來有自己的主意,若是她真心喜歡,便随了她吧。”
與此同時響起的是我的聲音——
“父親,是我錯了。”
“是我錯了,我不該任性妄為,不該不聽父親的話。”
其實在我闖上金殿、求了那旨賜婚前,我父親一直想為我與謝家二公子謝予珩定親。
我家和謝家是世交。
謝家同我們一樣,都是武将世家,我父親向來敬仰謝予珩父親的品行,贊他家風雅正,有勇有謀,對于謝予珩也是贊不絕口,常誇他少年英才,金質玉相。
也正因為此,父親一直不太瞧得上江言,認為他雖有才華,但性有瑕。可奈何我與謝予珩一直不太對付,又看錯了江言,付錯了真心。
父親聽了我的話,一愣,爾後長歎了口氣。
「筝兒,為父也不是真的怪你,為父隻是舍不得你受苦。」
他說着,又是一歎,「罷了,你要是真的喜歡,為父也不會攔你,這婚約……」
我鼻子更酸了。
「父親,我想清楚了,這件事情是我錯了,是我一時迷了心竅。」
「我想退婚,我不想嫁給江言了。」
退婚一事,說起來簡單,做起來難。
我原本想着,等這件事的風頭過上一過,我再尋了由頭秉了皇後娘娘,把這婚約取消了。
我想着此事雖然是我任性了些,可皇後是我的姨母,她那般疼我,聖上又與我父親是拜過把子的兄弟,他們一起打過天下,他對我也是疼愛有加,此事應該不會什麼太大的問題。
然而終究還是我想的太簡單了。
當我把這事往皇上皇後面前一提,皇後憐愛地摸了摸我的發,正要應下,聖上卻眼含無奈地斥我胡鬧。
“胡鬧,婚姻大事,豈可兒戲。”
“朕問你,前些日子跪在鳳儀宮前,口口聲聲說心悅江言的人是誰?”
“朕看你啊,就是小孩子心性,前些日子還喜歡得要死要活得,一下子鬧了矛盾,又來找朕了,朕若是現在應了你,指不定過些日子你又該來尋朕了,你呀你呀......”
他聲音寵溺,但我也隐隐能察覺出——聖上似乎不想我與江言退婚。
我又想起當初我求聖上赦免江言時,我其實并沒有想要求那一旨賜婚的,是陛下憐愛地撫了撫我的發,道:“筝兒長大了。既然筝兒有了心悅之人,那朕就為你們賜婚,可好?”
當時的我自然是滿心歡喜,并沒有察覺出這中間有什麼不妥,可是現在......
與此同時,江言也像是換了個人似的。
他說無論如何他也不願同我退親。
不僅如此,他還尋了不少些稀罕的小玩意兒來送我,有姑娘家喜歡的簪子,胭脂,石榴花,還有他親手雕的木雕......
我通通沒有收,都退了回去。
上元節那日,他還送了我一盞兔子花燈。
那是盞極好看的兔子花燈,做工精細,栩栩如生,被挂在了所有花燈上頭,攤主也不肯賣,非要人猜出三個燈謎,他才肯把這花燈送出去。
我喜歡得緊,就央了我阿兄同我一起猜燈謎,可我們對詩詞遊戲一道都不甚精通,三個燈謎一個也沒猜出來。
那花燈最終被江言赢了去。
漫天的燈火下,他從人群中走來,接過了那盞兔兒燈,遞到我面前。
春寒料峭,他卻隻穿了件銀灰色的長衫,卻更襯得他人如松竹,公子如玉。
“聞娘子可是想要這盞花燈?”
其實今兒一早他便入了我聞府,想邀我同他一起逛燈會,我不願,并随便尋了個理由拒絕了。而現在,他站在我面前,笑意溫軟,像什麼也沒有發生過似的。
我看着那兔兒燈,忽然想起了上輩子。
其實江言一直是個很好的人。他待所有人都是溫和有禮的,待我也一樣,隻是這溫和中難免透着幾分疏離和冷淡。
我剛同他成親那一年,上元節,我也看上了一盞和這類似的兔子花燈,我央他去替我赢來,可他隻是頓了頓,便拉着我離開了。
我曾經多想要那一盞花燈啊。
可如今,他把花燈遞到我面前,我隻是搖搖頭,往後退了一步。
“方才是想的,可是現在不想了。”
他一頓:“聞娘子不是喜歡這盞花燈嗎?”
“人總是會變的。我方才喜歡這一盞,現在喜歡那一盞了。”
我随手指了一盞,我阿兄見狀,立馬要替我買下來。
攤主有些為難:“姑娘,這盞早被人定了去,要不姑娘換一盞吧。”
我正要點頭,身後傳來道清越的男聲:“既然她喜歡,就贈與她了。”
3
說話的人是謝予珩。
看到謝予珩,我下意識往後退了一步。
......我真的隻是下意識退了一步。
他見狀,冷哼一聲,把花燈塞在我懷裡,便轉身離開了。
我和謝予珩從小就不太對付。
我從小在塞北長大,回京的日子不多,按理來說應該不會有什麼不太對付的人才對,可是謝予珩……
小時候的謝予珩,可以說是人憎狗嫌。
自我和他第一次見面起,我們就結下了梁子。
那一年我七歲,初來謝府,在院子裡閑逛時遇見了正到處尋他的小厮。
小厮問我有沒有瞧見他家公子,我想起方才瞧見的、躲在草叢的少年,随手一指。
接着,一陣雞飛狗跳之後,謝予珩又出現在我面前。
那一年,謝予珩十歲。
十歲的謝予珩生得極好。劍眉星目,唇紅齒白的小少年,臉上的稚氣未脫,眉宇間卻又帶着絲英氣,一笑,更是昳麗動人。
“聞家小妹,我帶你上樹玩好不好?”
我被這笑晃了眼睛,完全沒有聽清楚他說了什麼,便愣愣點頭。等到他真的帶着我躍起,飛到了樹上,我才猛地反應過來——我怕高。
是的,小時候的我天不怕地不怕,單單怕高。
謝予珩把我帶上樹後便足尖輕點,躍了下去,留我一個人呆在樹上。可我也是個硬脾氣的,我怕得要死,就是不肯哭。他把我放在樹上放了一會兒,見我實在無趣,就又把我帶了下來。
而我——
我趁他不備,一把把他推到在地,騎在他身上,對着他的手就是一口,生生咬出了一個血印子。
自那以後,我和謝予珩每次見面,都免不了一陣雞飛狗跳。
再過些年,謝予珩越長越大,性子越發沉穩,也成了京城衆多女娘們夢想中的夫婿人選。可許是幼時的印象太過深刻,每每我見着他時,總是下意識的戒備起來。
也正因此,上輩子,我一直以為謝予珩讨厭我。
我一直以為我與他是那種你看不慣我,我也看不慣你的關系,即便是謝聞兩家都有意讓我們結親,也以為那隻是我們父輩們的一廂情願。
可是上一輩子,我聞家落難後,人人都唯恐避之不及,隻有他站了出來,為我聞家說情。
我家被抄的那一夜,年已三十的謝予珩翻過圍牆,偷偷來了我的院子,隔着屏風對我說了聲别怕。
那時候我已然害了病,我病歪歪地倒在床上,看着屏風外人影晃動,聽着他沉穩而堅定的聲音。
他說:「聞筝,我知你心焦,可你别怕,事情還有轉折的餘地。我這就去向陛下陳情,你别怕,你父親一定會沒事的。」
也正是那一日,我才明白,他從來都不讨厭我。
上一輩子的謝予珩至我死時也一直沒有娶妻。
我還記得,上輩子,我與江言剛定親的時候,父親帶我去謝家拜訪,那一次,謝予珩沒有見我。
後來,我與江言的婚宴上,他送了我一對雙魚玉佩。
他這人一向肆意,送禮也是直接塞在了我侍女手上。
他自己就站在門外,隔着一道門沖我道:「聞筝,你既已出嫁,日後斷不可再像往常一樣了。我呢,虛長你三歲,勉強也算你半個哥哥,當哥哥的也沒什麼好送你的,隻好祝你日後平安喜樂,無風無波,恩愛百年。」
我看不見他的臉,可聽着聲音,大約是在笑着的。
想到這些,我的心亂了亂,忍不住拿眼去看前方的人,越看越不知該如何是好。
也就是在這時候,我聽見身後傳來馬的嘶鳴聲。
「快躲開!」
有人在喊。
我正要往讓向旁側,一隻手先伸了過來。
我一下子撞進了謝予珩懷裡。
我一愣,正要閃開,忽然聽見他開口:“我好看嗎?”
“什麼?”
我有些懵。
“我是說……”
有風輕揚起他額間的碎發,他微微勾起唇角,少年人滿是朝氣的臉上帶了抹極細微的笑意。
「聞筝,别看我,看路。」
4
三月春暖花開的時候,陛下在沂高山舉辦祭典,京城的達官貴人、适齡的公子貴女們大多都前往沂高山參與祭典,嘉熙公主也在沂高山設了賞花宴,廣邀京城的公子貴女們踏春郊遊。
上輩子,我忙着在家惡補女工,沒有參加此次祭典,而這輩子……
我在這宴上瞧見了一個我怎麼也想不到會瞧見的人——許窈。
許窈便是江言年少時的白月光,是上一輩子,江言官至一品後娶進門的平妻。
她原隻是小官家的庶女,憑着出衆的才情和外貌嫁入了個還不錯的郎婿,後丈夫又因病去世。
上輩子,許窈的丈夫喪期剛滿,江言便不江我的反對把她娶進了家門。
我那時十分不喜她,也十分羨慕她,卻也沒有因此對她做過什麼。可我卻總是能感受到她對我隐隐的敵意。
在江言面前,她總是溫柔小意,溫聲細語地訴說着她對我的感激,偶有和我起了沖突,也隻是自江自的垂淚。
可當着我的面時,她又像是換了一個人。她故意引我嫉妒,引我犯錯,又使計換了我的侍女。
我死得那一天夜裡,江言因公沒有歸府,便是她,差人換了我的藥,害我失手打翻了燭台。
瞧見許窈,我的呼吸一窒,很快又恢複正常,大大方方落了座。
賞花宴上,我一直沒有去看她,可是我總能感覺到西南方向時不時有目光向我投來。
我擡眼望去,正好對上了許窈的眼。
我心頭微微一動。
接着,在衆人一同行飛花令時,她又總是時不時把令傳給我。
我不通詩詞這件事幾乎是京城貴女圈裡人人皆知的,作不出詩來,便隻好喝酒。
喝到第三杯時,她過來同我道歉。
“聞娘子,我今年才随着家父一同如京,隻聽說聞娘子乃巾帼女子,心下一直仰慕得緊,實在是不知……方才行令時多有得罪,還請聞娘子海涵。”
我看着她這幅同前世相似的,嬌嬌弱弱、仿佛被誰欺負了似的的模樣,下意識皺起了眉。
上輩子,她就是靠着這副模樣,一點點在旁人面前加深了我跋扈的印象。
“一個遊戲罷了,許娘子多慮了。”
我頓了頓,笑着端起酒杯一飲而盡,心下已經有了計較。
我原以為,許窈對江言的感情伊始,是在她丈夫新喪而江言步步高升後,現下看來,指不定早在這時就已經開始了。
我想了想,找了借口說要出去透透氣,又吩咐玉煙尋了紙筆來,仿着江言的字寫了張紙條,約許窈戌時一刻在溪首池旁的榕樹下見。
“你去尋個公主府的侍女,讓她尋個空檔,偷偷把這個交給許娘子。”
“待會兒你再悄悄去尋江言,約他戌時一刻在溪首池旁的榕樹下見,就說……就說我有事找他。”
想到這段日子江言與上輩子截然不同的舉動,我想了想,又交代了玉水:“等到了時候,你先悄悄躲在一旁,若是許娘子沒來便罷了。若是江言瞧見來人是許娘子後掉頭就走,你就……你就想辦法把她推入水裡。”
玉水和玉煙都是我從塞北帶回來的,武藝卓絕,這些小事還是難不倒她們。
做完這些,我又回了涼亭。
涼亭裡,一衆貴女們還在行着飛花令,說說笑笑間,不少人都被酒氣熏得面色發紅。
見我進來,嘉熙公主李錦樂走到我面前來,問:“你去做什麼了,怎麼去了這麼久?”
“沒什麼,”我沖她眨了眨眼,“晚上我們一同出去走走吧,聽說這沂高山裡夜色極美,運氣好的話還能瞧見流螢呢。”
夜裡,我帶着嘉熙公主往沂高山後山的方向走。走了不過一刻鐘,忽然聽到“撲通”一聲。
「什麼聲音?」
我們對視一眼,加快了腳步。
等我們走到溪首池旁時,正巧瞧見江言抱着渾身濕透的許窈從池子裡爬上來。
月黑風高,孤男寡女。
嘉熙公主下意識看了我一眼。
嘉熙公主乃皇後所生,是我表姐,與我向來交好,自然也知道我為江言做得那些事。
她脾氣火爆又最是護短,瞧見此情此景,立馬皺起了眉頭,上前一步,喝道:「這是怎麼回事?!你們怎麼在這裡?」
我也連忙走上前,卻不急着說話,而是沉默地看着他們,皺着眉,最後化作了一聲低歎:「你們……」
許窈見狀早已垂下頭去,嘴裡喏喏不敢言。
倒是江言,他已經從開始的驚怒中緩過了神來,抿着唇把早就脫在池邊外氅蓋在了許窈身上,又把她放在一邊,這才直直地看着我,笑。
他一貫溫和從容,那笑裡卻帶着罕見的淩厲肅殺之意,像含着千鈞的怒意。
「我為什麼會在這裡,聞娘子不知道嗎?」
「我怎麼會知道。」
我定定地看着他,語氣輕描淡寫,“還是說,你的意思是我把你叫到這裡來,看着你和許娘子兩人月下幽會、卿卿我我?”
文來源于知乎《從容的夫君》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