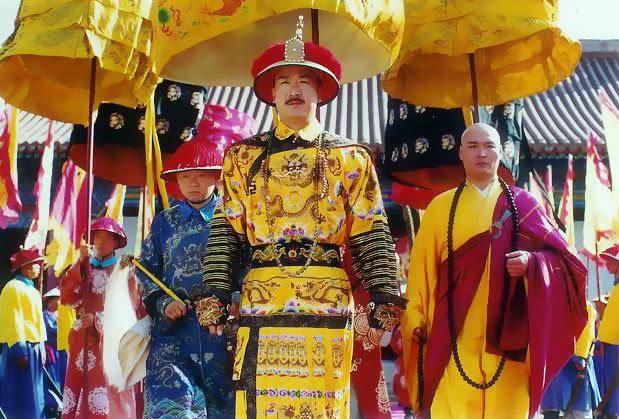伊夏
最近,一段短視頻在網上傳播,視頻裡,華坪女高的張桂梅校長,說自己拒絕曾經的學生,現在做了全職太太的女性的捐款,并且對她說“滾出去”。視頻裡張校長的表達較為憤怒,不斷強調“女人必須要靠自己!”一時間引發了社會熱議。
一種聲音說,為什麼要對全職媽媽這麼大惡意?女性可以選擇任何職業,包括全職做主婦。另一種聲音說,不能僅憑一個兩分鐘不到的短視頻就評判張校長的想法,她所強調的,是女性的自立自強而已。
又有一種表達是,正因為社會上有一股鼓吹“霸道總裁娶嬌妻”的金絲雀生活方式,讓“全職太太”這個不成職業的職業反過來動搖了許多想做獨立女性的人的意志。一種表面看似“輕松”的人生,在整體上瓦解着之前幾十年國家倡導的“婦女能頂半邊天”的意識。所以選擇做“全職太太”的女性,是在女性往獨立道路上努力前進時,拖集體後腿的人。

那麼,張校長口中的“全職太太”,和我們日常生活中說的“家庭婦女”、“賢内助”、“女主内”等概念,有什麼區别?又有什麼不同?為什麼家庭範疇内,女性總和“經濟無能”“情緒化”“婆婆媽媽”等負面詞語相挂鈎?談論家庭事務裡的女人時,她們本人在發聲嗎?
《看不見的女人:家庭事務社會學》是一本1974年的作品,這是首次嚴肅對待家務勞動的研究,它第一次将“家務”這件表面上個體化的事情,放置在更廣泛的公共領域進行讨論。雖然這本書已經距離我們半個世紀之久,但當代的《衛報》依然會在頭條寫:“女權主義運動發展四十年了,女人仍然從事着大部分的家務勞動”。這本書裡提出的種種主婦之苦,眼前的世界依然沒有解決,每一位女性都會被刻闆印象裹挾,從而選擇性地“被看不見”。
本書雖然不是所謂傳統社會學的經典著作,但它在開篇就犀利而明确地指出了社會學這一學科在家務領域的缺席與漠視。由于學科建立的過程中,多數都是不參與家務勞動的男性學者在論述和研究我們這個社會,因此“家務”幾乎從未進入學術言說範疇,更談不上“家務社會學”分支的建立。在西方社會學奠基的五位“元老”——馬克思、孔德、斯賓塞、塗爾幹和韋伯——之中,僅有馬克思和韋伯持有女性解放的觀點,但他們的“解放”也基于“男主外女主内”的刻闆婚姻模式,因此并未真正正視女性在整體社會活動中的價值。而這本書,劃時代地完成了“家庭事務社會學”的顯形,以40名倫敦家庭主婦作為樣本,以深入的定性研究作為依據,讓被調查的全職太太們說出她們的故事,讓學術田野第一次展開在此前未被關注的領域。
媽媽最偉大?作為“職業”它最廉價
張桂梅校長一再強調女性要靠自己,老公靠不住。其實很多女性自己也明白,但或許選擇了“全職太太”,是因為女性覺得自己難以承受家庭和工作的雙份壓力。這并不是說工作和家務皆苦,而是說,家務實在是太苦,苦到如果你順從傳統觀念進入家庭這種組合後,隻能承受這單一的苦痛。
事實上,職場給予女性的精神和經濟支撐,永遠是大于單一家庭生活的。
《看不見的女人》在調查了數十位不同階層的女性後寫道:“在女性的表述中,家務工作與職場工作相比是相形見绌的。因為無論職場工作是何種性質的,它們都能給女性帶來陪伴感,社會認可和經濟效益。”
現在流行一個說法叫“職場媽媽”,這個概念乍一聽,好像是很獨立,給了女性多元身份的詞語。其實,将“有酬勞”的工作和“無酬勞”的家務疊加起來,表面上似乎肯定了兩種角色,卻沒有細細探究:家務本身,也應該被視為工作。
家務不被視為“有價值”,是從一個有毒的三段論開始的:
1、家庭生活中,女主内,男主外;
2、因此,男人工作,女人不工作;
3、因此,家務活動不是一種工作。
第三個論斷似乎是前兩個的推論,但這個三段論是錯誤的。它的錯誤在于,“家庭”與“工作”之間被刻意地切割了。
什麼是“工作”呢?一種定義認為,工作具有五個屬性:它需要消耗能量;它允諾對商品或服務的生産做出貢獻;它定義了社會互動的模式;它為工作的人提供了社會地位;最後,工作會帶來收入。
在此定義下,有薪工作和家務勞動之間的唯一區别是家務勞動是無酬勞的。荒誕的是,僅僅因為一個要素的缺乏,家務在理論以及社會實踐中,就被默認排除于工作類别之中,連帶着做家務的家庭婦女們,根本不知道要怎麼稱呼眼前這一攤子繁瑣事情,逐漸深陷泥潭,既沒有金錢獎賞,也找不到對應的社會地位。
《被縛的妻子》的作者漢娜·加夫隆意識到了“雙重角色”概念隐含的深意:今天的女性被認為有兩種選擇——外出工作或待在家裡。這就意味着留在家裡無關工作。吊詭的是,在其他工業化世界正朝着每周40小時運作而邁進的時代,女人,她們中很多人每周可能工作至少80小時,則被引導要視家務不是工作。
可能很多人覺得,半個世紀過去了,《看不見的女人》裡所說的繁重的家務勞動已經可以被現代化的電器所替代了。那麼,主婦們真的解放了嗎?
《82年的金智英》裡,金智英曾經說過一句名言,大意是,你們認為我的勞動負擔可以被洗衣機,吸塵器解除嗎?那我問你,買來最先進的家電後,操作它們的是誰?還是我,不是嗎?

機械化大生産解放勞動力,放在社會化工廠裡可能是事實,但放在具體的一個個家庭裡,對于一位位具體的主婦來說,并不意味着解脫。赫茨伯格、毛瑟納和斯奈德曼三位學者的研究報告《工作的激勵因素》中觀察到,提供更好的工作條件有助于減少工作上的不滿情緒,但是并沒有起到增加滿意度的作用。也就是說,即便做家務能夠稍微輕松一些,主婦們也隻是抱怨少一些,但幸福感并不可能增加。
由于主婦所從事的都是“時間不靈活”的例行常規勞動,如做飯和洗衣服,而她們對幹淨的标準并無上限,因此會不斷進行自我壓榨,家裡的活兒,永遠會是做不完的狀态。家裡的清潔更是一項孤獨的任務,需要做清潔的感覺與人性想要去社交的願望相沖突。
調查中,一位做了媽媽的主婦說:
為什麼每天要清潔廚房地闆兩次?好吧,那是因為孩子無時不刻在地闆上玩耍,不是嗎?我的意思是讓他爬在肮髒的地闆上不好——他容易從上面感染上什麼。
也就是說,外界認為的家庭主婦反正就是賦閑在家,“做自己的老闆”。其實完全是大錯特錯,她們在家務問題上始終狀态緊繃,心理壓力巨大。
僅僅是因為家務活兒是“在家裡”完成的,就足以讓家庭主婦體驗着某種程度的孤立。當孩子還小時,主婦唯一忠實的陪伴者是她的孩子,但一旦孩子求學離家,家裡就隻剩她自己。出門買菜、購物、遛狗等家務的外延行為,并不能增加她們與社會的連接,相反,白天與陌生人的短暫交流實際上會使她們産生負面情緒。流于表面的社交在不斷地提醒家庭主婦:她缺乏的那些深入而有意義的社會關系是多麼重要。
一孕傻三年?謊言!
最近某平台有一篇題為《我隻是生了孩子,為什麼整個社會都要懲罰我?》的文章指出,65%的職場媽媽有抑郁傾向,工作996+帶娃007的模式,使得她們無法喘息。很多人覺得,做了媽媽,可能确實不必在職場上太有進取心,何況孕産婦會“一孕傻三年”,可能并不适合在職場上擔任要職。由此,“全職媽媽”像一種順水推舟,好像既然“你不行”,不如把機會留給單身者,留給無需孕産的男性,你的“讓賢”,你的“後勤保障”,是一種“偉大的犧牲”。
期許女性“不拼搏”“不奮進”,并不是善解人意,相反,這些觀念可能慢慢侵蝕女性的自我滿足感和成就感,将她們加速推入“無用”的深淵。
懷孕生育這種延續人類族群的重大職責,是如何被貶低的呢?
阿特伍德曾在《使女的故事》裡指出非常殘酷的事實:女性的子宮,可以被高度物化為全社會都可以操弄的工具,女性的身體屬于唯生育論的整個集體,唯獨不屬于她自己。身不由己的女性,在完成了生産後,緊接着面臨的就是生産被剝奪侵占的時間精力和機會如何追回。而“一孕傻三年”等污名,實質上暗示女性不必再追回本屬于自己的職場與社會地位。當然,可能有一部分經濟條件較為寬裕的家庭能夠讓女性開始做全職太太,但負面的話語以一種莫須有的定論,把不同女性的不同追求,拉低到一個共同的低水平的狀态裡。這種輕視其實指向全體女性:無論你選擇做全職主婦還是回歸職場,都将因為精神渙散智商下降而不能具備很好的表現。這種假設本身就是有毒的。
日劇《坡道上的家》就是一部對“失智媽媽”“歇斯底裡的母親”等形象進行透析的作品。高度緊張加勞累,造成了“恐怖”的弑子母親。但我們一定要細想想,她為什麼不能從傳統美德裡歌頌的“偉大媽媽”裡獲得成就感?因為歌頌裡沒有任何實際分擔,當空蕩蕩的家裡,陪伴她的隻有嬰孩,而嬰孩不間斷的哭鬧最終變成了提醒她疲累之源的警鈴,盡管孩子本質無辜,但過勞産生的恍惚讓她失去了理智,最終走上了悲哀的結局。
《看不見的女人》裡有一個比喻,說的是許多人覺得家庭主婦就是“卷心菜”,完全沉浸在家庭事務中。這樣的負面觀念傳遞出的結論是:她們是沒有個性特色,單調乏味,了無生趣的機器人。
可是,這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一孕傻三年”,這份“傻”,“無趣”甚至“歇斯底裡”,是長期被漠視被忽略甚至被壓榨造成的後果。主婦在家裡得到的肯定越少,偏執的可能就越大,為了校正這種孕産期造成的精神創傷,很多女性選擇盡快回到工作崗位。但糟糕的是,即使夫妻雙方在有酬工作方面是對等的,但女性對家庭主婦一角所負有傳統職責的認同程度并沒有降低。
學者拉波波特評論說,雙職工家庭模式實際上更容易引起人們對家庭領域内的傳統性别角色刻闆觀念的過度信奉。某些女人認為職場女性給人冷酷、“男性化”、好強的負面印象,于是轉而在“負責任的家庭主婦”一職上繼續奉獻。
女人不傻,但女人為了證明自己不傻,活得太苦了。
女人要幫助女人,整個社會也是
《乘風破浪的姐姐》裡,萬茜在采訪時說了一句上了熱搜的話:女人是可以幫助女人的。
這句話之所以鼓舞人心,是因為它沖破了很多流俗表達裡,将女性互相樹立為敵人,讓她們為了争奪愛情、金錢或地位而互相攻擊的可怕形象。
在分析張校長的言論時,有微博博主指出,“全職太太”可能和“家庭主婦”是兩個階層,前者養尊處優,十指不沾陽春水,天天就是美容購物;後者面容憔悴,困守廚房,辛勞半生。張校長可能隻是反對後一種生活。

《看不見的女人》,[英] 安·奧克利 著,汪麗 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9月。
其實,在《看不見的女人》裡,我們可以讀到,作者安·奧克利沒有把不同階層的女性嚴格劃分開讨論,她是把所有女性的艱難處境當作某種命運共同體來看。
這位社會學家敏銳地看到,所謂女性的階層分化,很多時候是依附在男性的階層上的。她說,人們根據丈夫的職業将女性分配到某個社會階層,這些人為的區分可能是站不住腳的,主婦之間可能沒有表現出顯著的社會階層差異,這樣建構出來的階級界限實際上可能會轉移人們的注意力,反而讓人們忽視一些确切存在的有意義的比較。
也就是說,中産階層以上的女性的經濟寬裕,并不意味着她們精神和金錢支配上真的自由。中産階層以上主婦地位的提升可能是由于她們從事的活動主要集中在消費領域,但“買買買”會帶來有收入一方(即她們丈夫)家庭話語權的提升,這種物欲的膨脹,恰好構築了更密更大的牢籠。
我想,以張校長一手創辦華坪女高的能量,她應該也不會推崇有錢的“全職太太”,而單獨反對“家庭主婦”。割裂不同階層的女性也是一種偷換概念,所有女性都應該有自立,不依附他人的覺悟,而不是在金錢這種單一維度上形成鄙視鍊。
要想“姐姐妹妹站起來”,不分貧富地走向強大,這本書的作者提出,可能需要做到三個層次:
其一是理論研究的進步。别小看家庭事務社會學,在這本書出來之前,該領域是一片空白。甚至整個學術界因為不把家庭主婦當回事,而從來沒想過研究她們。這種忽視本身,就是很可怕的。
其二就是完善各種制度。随着女性運動的不斷高漲,對各種實際立法等的推進也在進行中。作者提醒我們,不要總說“女性解放運動”已經取得足夠成就,女人受到的壓迫就像是一個長在她們身體内部的惡性腫瘤,全社會必須一起來了解這份痛苦,并幫助她們解除才行。因為善待女性,就是善待我們自己的母親、姐妹和女兒,如果你也是女性,那每一次善待,都是善待你自己。
其三可能是一個美好的長期願景:作者希望,這個社會終有一天能消除對女性的偏見。女人們自己也要認識到,沒有一種低下的位置專門就該女性去占據。所有人應當對女性這種性别具有一定的想象力:想象她能辦到他能辦到的一切,如果辦不到,是否有什麼結構性的不公平在阻礙,是否可以幫一把,是否能夠一起達成。
需謹記,理性、感性、柔軟、陽剛……這些隻是不同面向的個性,既不專屬某個階層,也從來不專屬哪個性别。人類的悲歡,應當相通,有共情能力的人,才會更好地理解他人,理解自己。而由這樣的我們組成的社會,才會更有希望,更能向前進。
在張校長的視頻發出一段時間後,她口中的“全職太太”,當年的學生,也站出來回應了。原來,她在被校長嚴厲批評後,奮發圖強,于次年考上了特崗教師,重回職場。這位黃姓女生說,“張校長話醜理正,她是從我們的立場去說的”。
“我們的立場”,就是自立自強的立場,是所有女性應該共同去走的路,這樣的路走的人多了,“看不見的女人”才能變少。而下一代“被看見”的,是更自信更美麗的女孩。
責任編輯:朱凡
校對:徐亦嘉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