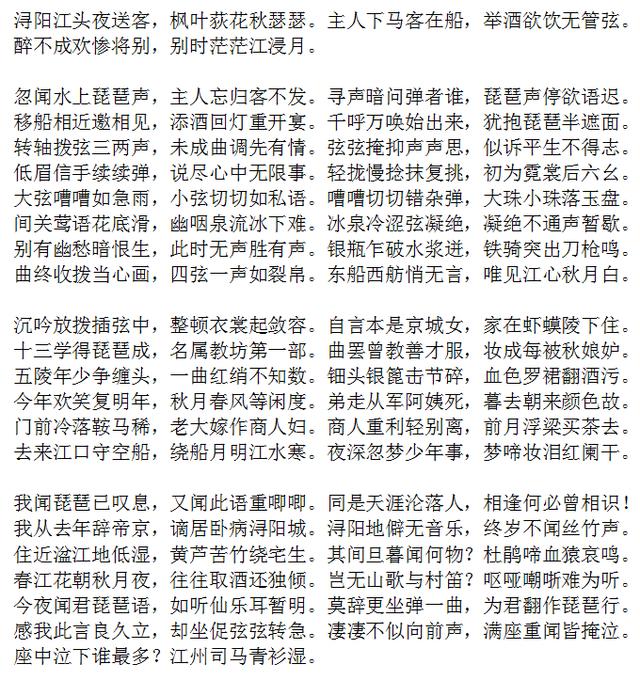喜歡《紅樓夢》是從喜歡《紅樓》詩詞開始的。《紅樓夢》中的詩詞像《紅樓》女子一樣溫婉賢淑,惹人憐愛。她們有鮮明的個性、豔麗的裝飾、動情的眼神。牡丹之所以傾國傾城,在于它綻放出雍容高貴的姿态,玫瑰之所以嬌娆妩媚,在于它釋放出馥郁盈鼻的芳香。當牡丹碩大的花瓣在日暮裡漸漸地凋零,誰人不為之感傷牽腸?當玫瑰芬芳的蓓蕾在夕陽中無聲的落幕,誰人不為之惺惺惜憐?最美與最動人的往往不是她們開放時一刹那的仙姿,而是她們落地時一瞬間的凄涼。嬌花如此,像嬌花一樣的美人如此,像美人一樣的詩詞亦如此。

昨天新買了一本《紅樓夢》,長春出版社出版的,至于是哪個版本的上面沒有标注。我仔細翻了翻,還是一眼能夠看出差别來。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增加了疑難字詞的标音和注解。還有一些重要的詩詞下面也有批語。
比如:警幻仙演奏共計十四支曲子(包括“紅樓夢引子”和“飛鳥各投林”)的解釋。其中【枉凝眉】下面标注的是:這首曲子是專門詠歎寶玉和黛玉的。“枉凝眉”意為白白的皺眉頭,命運太無情,追悔、歎息、痛苦皆無用。這個注釋和我讀劉心武探疑《紅樓夢》所講的不同。他說這首曲子是妙玉和史湘雲的合詠。不論孰是孰非,都可見《紅樓》的魅力。這是見仁見智的事。當然,也有一些事大家都認同、無可争議的。
比如此句,“可歎停機德,誰憐詠絮才。玉帶林中挂,金簪雪裡埋”。也有批注說,這首判詞是寫黛玉和寶钗。一四句寫寶钗,二三句寫黛玉。編者敢下此評語,肯定是有理有據的。盜版書也不至于有嗜好《紅樓夢》至此者。
再比如“堪羨優伶有福,誰知公子無緣”這句就大有文章可做。頁末有注解說優伶指的是琪官蔣玉菡。公子指寶玉。這段講得是襲人後來嫁給了蔣玉菡。根據是第二十八回“蔣玉菡情贈茜香羅”這樣的伏線。更直接的是蔣玉菡唱得詩句“花氣襲人知晝暖”以及他送給寶玉茜香國的汗巾子。這條汗巾子被寶玉轉手送給了襲人,又被襲人壓在箱底。我想它必是襲人與蔣玉菡劫後重逢的見證。《紅樓夢》中提到“公子”的詩詞也非常多。此“公子”是不是指寶玉呢?起詩社的時候寶玉的雅稱就叫做“怡紅公子”,況且襲人與寶玉有肌膚之親,最後襲人沒有嫁給寶玉,那就是“無緣”的體現。寫妙玉的【世難容】中也有“王孫公子歎無緣”之說。據劉心武“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得出結論說是陳也俊。因為在賈寶玉路谒北靜王一回有些蛛絲馬迹,甚至十分重要。原文即“錦鄉伯公子韓奇、神武将軍公子馮紫英、陳也俊、衛若蘭等諸王孫公子。”劉心武說後二十八回裡肯定有他們的重頭戲,并且很多無法解釋的謎也能夠巧妙地銜接上。(馮紫英前八十回已有大段戲份。)
又副冊上歌詠晴雯的判詞也提到一個空牽念的多情公子。頁尾注釋指得即是寶玉。晴雯與寶玉,正是公子對紅妝。在癡公子杜撰芙蓉诔一文中正有兩句“紅绡帳裡,公子多情;黃土壟中,女兒薄命。“公子女兒,顯而易見。

不過,有些卻失之考據,有誤導讀者之嫌。有的甚至讓人犯迷糊,在一字一詞上與我之前所見多有出入。我讀書向來咬文嚼字锱铢必較。隻是現在市面上通行的都是曹雪芹、高鹗合著的一百二十回本。較接近于原貌八十回的《石頭記》已很少見。所以有時候讀得細,就會發現一些值得商榷斟酌的地方。古人作詩講究煉字,一字一句的代換就有一字一句的意味。比如描寫林黛玉的那句“兩彎似蹙非蹙罥煙眉,一雙似喜非喜含情目”,這裡的“罥”字就換成了“籠”字,“喜”字換成了“泣”字。那眉毛的神态自然成另一種模樣了。玉在椟中求善價,有的寫作“櫃”,懷金悼玉,有的寫作“悲金悼玉”。曲子【虛花悟】寫成了【虛花語】,而且末尾的用詞也不考究,“西方寶樹喚婆娑”,乍一看毫無破綻,但佛家人就經常做“娑婆”講。雖然有些詞語的更換能使原文錦上添花,但是因小失大、顧頭不顧尾的做法肯定為卓越的藝術家所不取。而搞藝術的人偏偏與“大行不顧細謹”相反,否則就會有“千裡之堤潰于蟻穴”之危。像這樣傷筋動骨、面目難辨的也真不少。比如“蟾光如有意,先上玉人頭“,有的作“先上玉人樓”講。讓讀者看來,到底是月光有意照上玉人所倚之樓呢,還是月光流瀉于玉人的發髻上呢,真是模棱兩可。還有一首林黛玉寫得《桃花行》,不知道看得是哪個版本,曾誤導了我幾時。原句是“胭脂鮮豔何相類,花之顔色人之淚;若将人淚比桃花,淚自長流花自媚”。可能那個盜版得編輯受了唐寅與崔護的影響,改得也不含糊,道是:“胭脂鮮豔何相類,花之顔色人之媚;若将人面比桃花,面自桃紅花自美。”不僅押韻,而且有含義。我竟被一時唬住。不過仔細品味,林黛玉的那種凄婉動人的悲戚歎息之情就淡了。
反生歧義的豈止一例。比如本書“虎兔相逢大夢歸”一詞末尾的批注是指元春死于寅卯年之交。而我所見,另一種說法是“虎兕相逢大夢歸”。解釋也大相徑庭,說的是關于賢德妃賈元春與紅學家所探佚的具有公主身份的秦可卿的是非之争的。結果是“賈家大小姐受皇帝恩寵賈府藏匿的‘政治籌碼秦可卿’畫梁春盡落香塵”。

劉心武先生更是明察秋毫,在賈寶玉酣睡于秦可卿的卧房裡的時候,身邊出現了一個後文再也沒有出現過的丫鬟叫做媚人的。通過這樣的毫末之微就能揣摩出曹公的心迹,劉先生不愧為解語之人。他還指出“心下暗伏”于“暗服”所表現的人物心态是迥異的。但這個版本裡卻注釋道“伏”通“服”。這又讓我深深的感觸到讀書每有疑窦之時,應當謹慎再三,反複推敲,不可盲目地下評語。
文中第一回就交代了說有一個曹雪芹先生于悼紅軒對《紅樓夢》增删五次、披閱十年。隻是後世之人以訛傳訛地多了去,杜撰編輯的亦是不計其數。恐怕早已失去了它的本來面目。作者反複強調寫書隻是為了記述閨友閨情,并非怨世罵時,更不欲牽涉世态,故曰:甄士隐雲雲,賈雨村雲雲。今日讀來,果真是如此的。
隻是後人連那一點隐去的真實都還不知,連那一點僅存的假語都還未察。就急着篡改文章的原義,忙着續寫人物的命運。看來都是紅塵中的渣滓濁沫,利益熏心之徒,又怎麼會笑的作者“字字吟來皆是血”的肝腸寸斷的用心?此系身前身後事,名煙利雲俱塵土。幾百年後的今天,曹雪芹根本不會想到有那麼多熱衷于《紅樓夢》的讀者,孤獨曹公也許從未曾想過,在世之時不為人所理解為世人抛棄,死後反而功成名就曲高而和者繁。甭管他們是“甄知音”還是“賈知音”?甭管他們是為名還是為利?總而言之,有一二癡者,為了他一本泣血含淚的厚書,茶飯不思,卧榻品讀,更有甚者,耗擲二三十載光陰,研微究細,筆耕不綴,視為畢生重于泰山之事業。若雪芹地下有知,亦必死而無憾、含笑九泉。
然而,據我所察,有些所謂的僞紅學愛好者,對原著粗暴的刊印,俗濫的評語,胡亂的修改,毫不負責任地電視連播等等。遠遠比我們想象的還要可怕。當高雅的東西一味地粗制濫造;當陽春白雪變成了迎合大衆的低級俗物;當人情冷暖不足以警人心撼心靈感肺腑,那麼我們的作者百年前的初衷豈不成了娛樂大衆毒害萬年的蠹蟲與尖刀?或者說世俗的大衆才是真正的坑殺作者十年心血的劊子手?總而言之,這樣的情形,是在天有靈的曹公所不願見的。倘若真如此,曹雪芹隻希望他的作品速朽,要不就像野草,蔓延進每一個讀者的心靈裡。這樣也不至于做個鐘馗鬼,睚眦必報,好把你一口吞食掉,叫你下輩子還做一個祿蠹利賊的小人。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