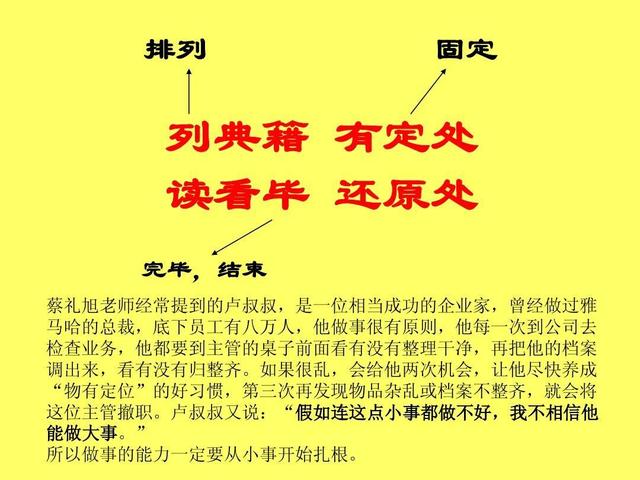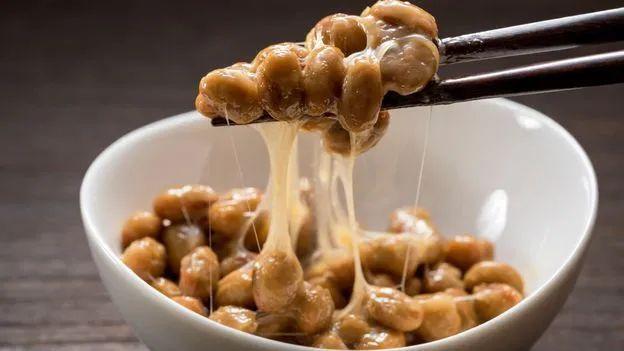王聖人
(一)看過前面文章的老讀者知道(文末點擊閱讀),雖然王陽明是成功人士,但王陽明心學并不是什麼成功學,而是與程朱理學一樣,都是在儒家這顆千年古樹上開的花、結的果。
但兩者又有「異同」。
兩者最大的共同點是「目标相同」:都是在追求至聖的終極真理。
最大的區别在于求的「路徑不同」:
程朱理學是向外求,終極真理——藏在萬事萬物之中;
陸王心學是向内求,終極真理——本就在我們每個人心中。
目标有了,求的路徑有了,那求的方法是什麼呢?
——兩派都說是「格物緻知」。
但就是這四個字,或者就是對一個“知”字的理解不同,不僅讓王陽明與程朱理學分道揚镳,還造就了日久彌新的心學。
一個字,有這麼重要嗎?
不信,往下看。

《大學》
(二)要厘清兩派對「格物緻知」的理解差異,就得先看這四個字是怎麼來的。
「格物緻知」并不是朱聖人,更不是老王的發明,這四個字來自于儒家經典《大學》,本書一翻開就是下面這一段,格物緻知就在段尾: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緻其知,緻知在格物。
這是一個倒裝句式,這意思是說:
要平天下,必須先治國,要治國必須先齊家,要齊家必須先修身,要修身必須先正心,要正心必須先誠意,要誠意必須先緻知,而緻知就要靠格物。
這就是「格物緻知」的由來。
這四個字,是儒家一切的起點,從格物、緻知開始,後面還有「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八點的修煉是有嚴格的先後秩序的,需要你一個台階一個台階的上,你不能“跳級”,不能從格物就跳到平天下了,這是要出大問題的。
就像要做一個德藝雙馨的真藝術家,你必須先練德行、再修表演,比如劉德華。
但凡你反過來或者不修德行直接跳到表演,那你隻能成為吳亦凡和霍尊。
儒家的「格物、緻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是這麼嚴格。
但就在一開始的兩個台階,理學和心學就産生了巨大的分歧。
分歧在哪裡呢?
我們進入正題。

朱聖人
(三)其實,《大學》裡對這些概念本是有解釋的,什麼是誠意、正心及後面的幾點都有解釋,唯獨「格物、緻知」沒有。
或許是這幾片竹簡丢了,原因不知道。
朱熹就在編撰《四書》時,對格物緻知補充了自己的理解。
朱聖人說:
所謂緻知在格物者,言欲緻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衆物都有表裡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 ...。
古文較長,我估計你也不願意讀,但意思很明白:
要緻知,必須先格物,終極真理,就藏在這萬事萬物之中,你之所以沒有成為聖人,是因為你還沒有格透萬事萬物。
所謂格物,就是用打破砂鍋問到底的精神,探索各種事物的終極真理;
所謂緻知,就是将已經格出來的道理觸類旁通,向外推演,便逐漸由掌握一事一物背後的終極真理,到掌握到了萬事萬物的終極真理,大功就此煉成,成為聖人了。
你看理學大家張載的《西銘》,也是在講這個道理,所謂的“理一分殊”,真理其實隻有一個,雖然表現在具體事物上存在差異,差異就是“分殊”,但萬流歸海,九九歸一之理就隻有一個,都在那個“理一”裡,這就是終極真理。
在此,我們就知道了,理學陣營裡的「格、緻、知」的意思:
格——是一個動詞,探索、研究之意;
緻——也是一個動詞,窮盡之意;
知——是一個名詞,就是知識、道理。
朱聖人是儒學裡高山仰止的人物,他的解釋也當成了金科玉律,成了格物緻知的标準版本。
但到了王陽明這裡,他對這三個字的理解,就“離經叛道”做出了不同的解釋。
為什麼他要這樣?他的理解又是什麼?

王聖人
(四)一開始,王陽明也是朱聖人的信徒,但他和千百年來的讀書人完全不同。
其他人都把聖人之言當成了仕途的階梯,讀這些書隻是為了考試、為了能當官、為了能發财。
而當這些世俗的目的達到後,那到底能不能據此找到終極真理又有誰在乎呢?
當官發财,就是這些人的終極真理!
而王陽明卻是真的要立志做聖人的,他可能是世上那唯一嚴格踐行聖人之言的人,他開始格物——從竹子開始(陽明格竹)。
但格了七天七夜後,真理沒有格出來,卻格出了病,虛脫了。
既然一顆小小的竹子都如此難格,如此難找到這顆竹子的“真理”,那還有萬事萬物要格呢,這不是把有限的生命用在無窮的格物上嗎?
到死,也不會進入「誠意、正心」的階段了,後面可還有「修身、治國、平天下」等着呢?
這樣說來,聖人之路就永遠停在了第一步,本想一二三四五,現在卻永遠隻能一一一一一。
此路不通啊!
王陽明斷定朱聖人可能錯了。
錯在哪裡呢?
就從這格物緻知的「知」字上,理解上就錯了,隻要這個理解錯了,後面就全錯了。
我們就來看看王聖人理解的「格物緻知」。

王聖人
(五)我們先看「知」。
如果《大學》裡的這個“知”,不是指“知識”,而是指“良知”呢?是不是就可能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
如果這個“知”真的指的是良知,那“格”是研究、探索之意就說不太通了,探索知識很好理解,探索良知就有點違背常識,沒這麼說的。
如果真的是指良知,“格”就可能不是動詞,而是名詞,意思是“格子”,在心裡畫好了格子,就有了一個标準,一個是非善惡的标準。
如果真的指良知,那“緻”就不是窮盡,而是導緻、達到的意思了。
王陽明理解:
格——不是探究之意,而是一個标準;
緻——不是窮盡,是導緻、達到之意;
知——不是知識,而是每個人心底都有的「良知」。
由此,在王聖人看來,朱聖人就全錯了!
「緻知」不是窮盡天下之理了,而是「緻良知」,到達心底至真至純之善。
「格物緻知」就是:
一件事情的是非善惡,本來每個人心裡都是明明白白的,也就是「良知」就在每個人心裡。遇到了事情,隻要拿出「良知」一框,在框裡合乎良知标準的,就保留就去做,不符合标準的,就舍棄不要做。
這個簡單嗎?
不簡單。
雖然王聖人相信每個人心底都有良知,但也相信:這個良知會随着年齡增長被灰塵遮蔽,從而分不出是非善惡來。
比如,在大多數人看來霍尊就是個卷豬簾的、是“惡”的,但有些孩子卻在力挺他,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這些孩子是他的鐵杆粉絲,孩子們站了邊排了隊,就有了傾向,這個「傾向」就成了心裡的灰塵,把原本的「真善美」給蓋住了。
正因為如此,我們要勤拂去心裡的各種灰塵,一日三省。
也正是這種對「格物緻知」的解釋,王陽明打開了《大學》裡修煉其他台階的通道,直達聖賢的頂點。
怎麼說?

王聖人
(六)你看,格物緻知要是指拿心底的“那杆至真至純的秤去稱萬事萬物”,就比去探究藏在萬事萬物的“理”,要省時間得多。
朱聖人的格物,“物”太多了,是永遠格不完的;
王聖人的格物,方便快捷,遇事就拿良知去套,是非曲直異常清楚。
隻要把蓋在良知上的灰塵都拂去了,就有了誠意、有了至真至誠、心就正了,心正了身自然就修得差不多了、後面的齊家、治國、平天下,就能按部就班,就可能在有生之年完成了。
由此,心學與理學分道揚镳,打開了國人一扇新思想的大門。
雖然現在我們看來不如如此,但這在當時的思想界,就是石破天驚,這就好比:
你想發大财,朱聖人說财富就藏在祖國的每一座大山裡,隻要你拿着鐵鍬挖遍千山萬水,總會挖到的。
于是,你沒日沒夜、千辛萬苦地挖,累得跟孫子似的卻一無所獲。
而就在此時,王聖人說,别到外面去挖了,你被蒙蔽了雙眼,其實金山銀山就在你家後院裡放着呢。
王陽明不僅影響了自明朝以來的中國人,心學還走出國門,影響了整個東南亞,特别是日本。
1905年,日本戰神東鄉平八郎以少勝多,全殲了俄國太平洋艦隊。
在表彰酒宴上,他在包括天皇在内的一緻誇贊聲中,慢步走上演說台,在衆目睽睽之下,他什麼也沒說,便拿出了自己的腰牌舉過頭頂。
衆人皆驚,隻見上面寫有七個大字:
“一生伏首拜陽明。”
(完)
相關文章:
1、不了解王陽明《傳習錄》的背景和前提,讀100遍都會雲裡霧裡;
2、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到底是什麼意思?這次給你講清楚;
3、大聖人王陽明,那也是“凡爾賽”的高手。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