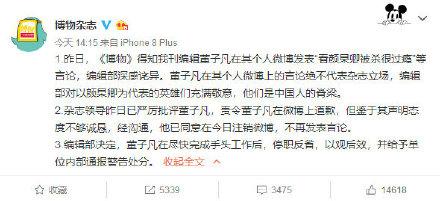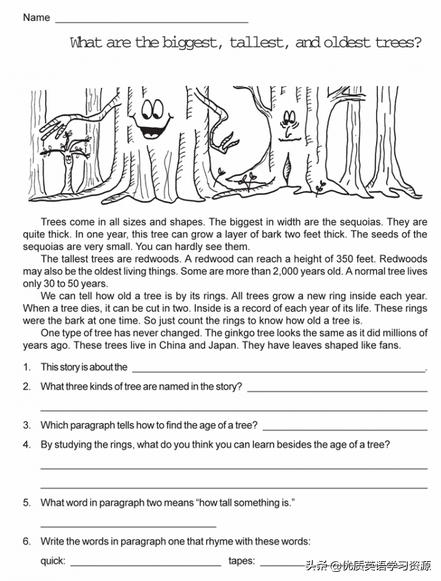2月10日(北京時間),第92屆奧斯卡獎正式落下帷幕,電影《1917》斬獲最佳攝影、最佳視覺效果、最佳音響效果三項大獎。
《1917》由薩姆·門德斯執導,迪恩·查爾斯·查普曼、喬治·麥凱主演,電影的故事主線很簡單,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兩名士兵被分派必須在有限時間内前往前線送達撤退任務,否則前線第二軍團的1600名士兵将陷入德軍的陷阱全部陣亡。電影圍繞這兩名士兵前往送信之路展開,電影一鏡到底的展現方式,使觀衆在觀影時沉浸式地跟随主演一路前行,專注于他們的執行任務的每分每秒。
當任務完成了,觀衆的情緒也開始放松下來,這種沉浸式的吸引也是這部電影的成功之處。詩人、作家廖偉棠的這篇文章,細緻解析了《1917》的戰争美學,同時其中構建的寓言,在今天也依然也有思考價值。
撰文 | 廖偉棠
《1917》成為了今年奧斯卡的一匹黑馬,不僅僅因為它以非常詩意的形式、深邃地表現了一種凄美的戰争美學,同時它還建構了一個關于劫難與救贖的寓言,即使放在和平但依舊充滿天災人禍的今天,也發人深省。
回看西方近代史,每逢瘟疫蔓延的黑暗時期——無論是病毒瘟疫還是政治瘟疫,常常會出現愚人船(The Ship of Fools)的寓言,有歌謠有詩篇,也有畫作。最有名的是Bosch的《愚人船》,畫的是一艘搖搖欲沉的小破船,上面坐着各種愚人、小醜,他們為着種種執念作出可笑的舉動,在某種想必也是愚昧的力量引領下駛向死亡。

《1917》劇照。
但愚人船的極緻表現,是愛德華.李爾(Edward Lear)的诙諧詩《呆頭人》(The Jumblies)所寫:
They went to sea in aSieve, they did,
In a Sieve they went to sea:
Inspite of all their friends could say,
On awinter’s morn, on a stormy day,
In a Sieve they went to sea!
“他們乘着篩籃出海……”全然不顧海水上漲輕易淹沒自己,這明顯是愚蠢至極的行為,但又流露着一種盲信的宗教意味,帶着神秘色彩。春節自閉,在一片瘟疫宣告勝利的消息包圍中,我意外聽到這幾句詩,如在夢魇中驚醒。
說是意外,因為誰也想不到,當《1917》裡的傳令兵Schofield下士對着他在法國淪陷區裡遇見的嬰兒,喃喃背誦出來的,是這樣一首奇異無比的詩。
但也隻有這麼一首啟示錄一般的詩才能配得上電影裡這一段神奇場景,以及這個最不可能的嬰兒——就像照顧他的女郎所說,他并非她的孩子,不知道來曆——這樣的組合,曆史上隻有瑪利亞與耶稣,那麼慷慨照應她們的Schofield,無意擔當了聖約瑟的角色。
很有可能這都是Schofield頭部受傷之後的夢幻,當他走下塔樓,置身于一個燃燒的教堂與幹涸的噴泉前面,這就展開了艾略特《荒原》裡的現代啟示錄——一系列的光影交錯既是現實可能有的照明彈所營造,更是Schofield的内心隐喻。他所穿過的地獄廢墟亟須被照亮,然而這聖光是超乎善惡的,搖曳不定的。夢醒後,Schofield依然得靠自己穿越戰火,給前線帶去停止進攻的消息,然後找到本來就屬于他的那棵可以依靠的小樹。
可以說,廢墟中藏匿的嬰兒就保證了結尾的小樹的出現,就像塔可夫斯基《犧牲》裡那個因為不能說話的孩子保證了電影結尾的小樹一樣。
塔可夫斯基《犧牲》電影劇照。
《1917》的導演薩姆·門德斯在出離全片的現實主義戰場描寫而營造的夢幻感,的确帶有濃烈的向塔可夫斯基緻敬的意味:除了《犧牲》裡的救贖隐喻,曳光彈掠過奔跑的Schofield那段,也讓人想起塔可夫斯基早年作品《伊凡的童年》裡男孩情報員伊凡穿越戰火泅渡夜河那一段。他們都是和平所索求的犧牲,傳令者,這兩天有一個别名:吹哨人。
在這樣的背景下看Schofield讀“他們乘着篩籃出海……”分外觸目驚心,“他們”是被戰火摧毀的一代精英還是好戰的民族主義者?他們都是無辜但又有共業的一代人,最終都會陷入《1917》裡無處不在的死神盛宴一般的地獄變圖卷。經過了一戰,為何沒幾年又有了二戰?經過了SARS,為何還有WARS?人類真的有反省能力嗎?為什麼他們始終都選擇坐上篩籃出海而不看看腳下湧出的海水?
Schofield本來也是篩籃中的一人,但他對信念的選擇拯救了他也局部拯救了世界。在受傷一刻分割的前後兩個世界之前,有一個細節确保了這場拯救:當Schofield與Blake走過那個被遺棄的農莊,隻有Schofield欣喜地留意到牛奶桶裡的牛奶依然新鮮,于是他灌滿了自己的水壺。所以當他後來遇見無母嬰兒的時候,他才得以把這罐牛奶送贈給後者。他珍惜生命,珍惜和平中應該有的牛奶。
也是在這個恍惚出離戰火之外的農莊,有這樣一段對話:“那麼說櫻桃樹沒救了?不,果實腐爛時還會再長出更多的樹”。同理,戰争所遺棄的牛奶也拯救新生,使得Schofield、聖母子以及被Schofield傳信拯救下來的士兵們都成為篩籃上的幸存者。
《1917》劇照。
這些充滿救贖意識的對話、隐喻、潛文本,拯救了《1917》非常單薄的劇情,也使得它所謂的一鏡到底式技術奇迹不至于流于炫技。本來這是一個屬于技術時代的沉浸式體驗電影,結果被塔可夫斯基的靈魂附體,加持成為寓言級别的佳作。如果把一戰換成别的戰争,甚至我們身處的抗疫之戰,我們能否領悟出更多的寓意?
《呆頭人》之外,電影還有一首《遊蕩的異鄉人》(WayfaringStranger)。相對應的畫面是Schofield從激流中掙紮上岸,聞聲尋見一位士兵站在樹林間為一群疲憊的士兵引領歌唱的場景。這一幕堪比杜甫“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鄰人滿牆頭,感歎亦歔欷。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的恍惚悲涼。
這首WayfaringStranger是一首傳統民間歌謠,大意如下:
我隻是一位可憐的流浪者
獨自穿越這個世界
在我所去的那片光明的土地上
沒有疾病,辛勞或危險
我将回家去看看母親
還有所有我所愛的人
我要回家了,不再流浪
我将涉過約旦河
回到我的家鄉
我知道烏雲會籠罩我
我知道我的路艱難險峻
但是金色的田野在我眼前出現
讓我疲倦的雙眼不再哭泣
我将回家去看看父親
我要回家了,不再流浪
我将涉過約旦河
回到我的家鄉
細味這歌詞,像Schofield主觀視角的鏡頭一一流連在沉醉歌聲的士兵臉上,我不禁淚下。回家是多麼奢侈的事,這個春節,中國土地上的每一個人都體會到了,湖北人體會更深。
《1917》劇照。
Schofield與好友Blake送信的目的,不是号召進攻,而是警告前線應該按兵不動——這也是《1917》迥異于大多數戰争片主題的。雖然Blake死于中途,他的兄長還是被Schofield及時送信所救下。Schofield不知道自己還能否回國重見懷中照片上的親人,但這一刻,Blake的兄長就是他在前線的親人——“豈曰無衣,與子同袍”,這句古語說的就是這種災難中新生的親緣。我們也如此寄望與疫區前線的醫護、喪失親人的人,可否?戰争總會過去,如何在廢墟中重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才是最重要的。
撰文 | 廖偉棠
編輯 | 張婷 張進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