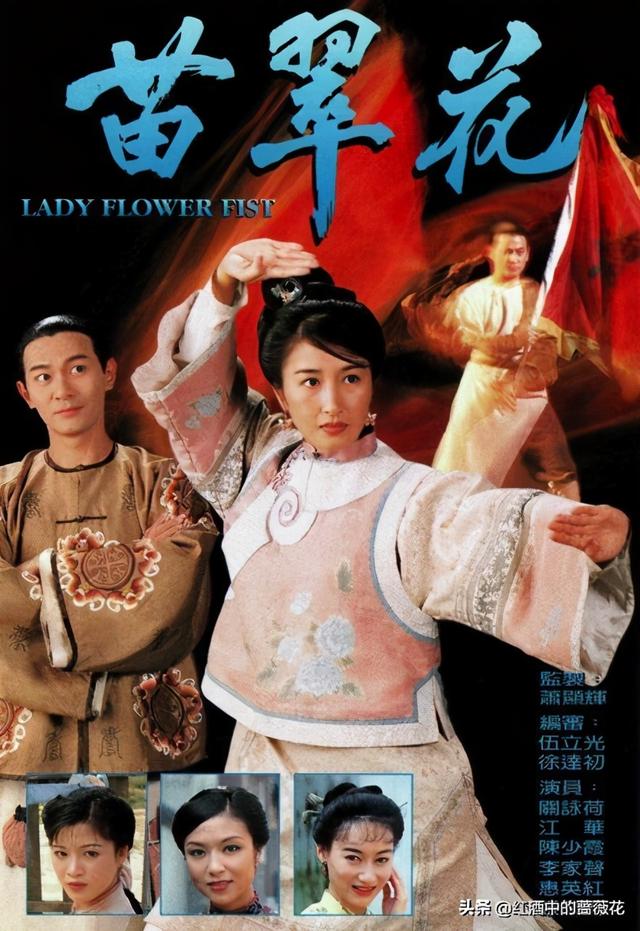黃永玉《雞王鎮宅》。

漢代鬥雞人俑。

趙佶《芙蓉錦雞圖》。

齊白石《大吉圖》。
十二生肖的輪替給了中國人每年爬梳動物的社會文化史的機會。在忙碌一年後,通過這種頗具趣味的文化鈎沉,我們既能回顧那些在匆忙中易被錯失的生活意趣,也能或近或遠地與前人在浪漫風度、想象力上有所接續。
今年要說的雞。如果在十二生肖中國選一個擁有文化意象最多的動物,雞當之無愧。它既可以出現在清朝官服與花翎上,标示權力與等級,又滲透進地方傳說,成為一座座村落神廟的根源。這種可上可下、可俗可雅的特質使中國雞文化打通了不同階層與領域。即便在當代,雄雞既能因與祖國版圖形似成為一種抽象且威嚴的象征;其實體又是深入萬家、與中國人日常生活關系最緊密的家禽之一。
與此相應,中國的雞文化豐富至博雜,本土文化沉澱在開放中也與西方影響交彙,構建着國人關于雞文化記憶的新知。2017年的這份迎新文化盤點便在這樣的過程中,七分懷舊,三分探新。
神侃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昴日星官
昴日星官是二十八星宿之一,住在上天的光明宮,其本相傳說是六七尺高的大公雞,神職是“司晨啼曉”,其母是毗藍婆菩薩。古人用昴宿定四時,《尚書·堯典》中寫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即如日落時看到昴宿出現在中天,就可以知道冬至到了。
昴日星官在西方星象中有一個對應的星宿,天文學稱它為“昴星團”,民間叫做“冬瓜子星”。在冬夜星空,人類的肉眼可在昴星團裡面看到7顆星,希臘神話中稱它們為“七姐妹”。在更流行的西方十二星座體系當中,昴星團屬于金牛座。
昴日星官出現于中國古代的神話演義小說中。如在《封神演義》中,其原名為黃倉,是截教通天教主的門人,因無福成仙,在萬仙陣中陣亡後,輪回進入神道,成為天庭中的一位神。他更流行的形象出現在《西遊記》中,唐僧師徒途經毒敵山琵琶洞時被蠍子精困住,孫悟空經黎山老母指點,懇請昴日星官下界降妖。星官現出公雞本相長叫一聲,蠍子精便被收服了。這個情節與現實中兩種動物的相克關系對應。
2017年,巴黎老佛爺百貨公司的兩扇農曆雞年藝術櫥窗由中國當代藝術家邬建安打造。邬建安正是以昴日星官為主體,借助中國傳統剪紙與皮影的造型語言寓意雞年吉祥。
雞王鎮宅
魏晉時期,雞成為門畫中辟邪鎮妖之物。在門楣上貼雞成為四川成都等地的習俗。在桃花塢年畫中也有“雞王鎮宅”的年畫,圖案是一隻大公雞口銜毒蟲。
天雞
上古神話中住在天上的神雞。南朝梁任昉《述異記》: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裡。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則鳴,天下雞皆随之鳴,漢代陶器已有其像,在三星堆遺址中出土的青銅雄雞抑或是古人心目中呼喚日出、光明的天雞的反映。
雞腳神
雞因在日夜間承上啟下,在民間傳說中也有陰陽使者的身份。在一些村鎮或較偏遠的山區,流傳着雞腳神的傳說。人去世三天後,停放棺材的屋子裡會出現動物腳印,通常是雞腳印,傳說是陰間使者帶死者亡靈去見閻王的向導雞腳神所留。
雞圖騰
少數民族都有動物圖騰,雄雞是白族先民崇拜的圖騰。至今白族人家的小夥看上某位白族姑娘,男方家就請媒人帶上小夥在月圓之夜悄悄地上門提親,無論提親是否成功,女方都要以雄雞款待求親者。
雞神廟
一些村落中的廟群中常見山神廟、娘娘廟等,雞神廟則往往與地方傳說有關。如在山西省洪洞縣流傳着這樣一個傳說,村口有一隻大公雞專啄人的影子,“小唐”(唐王李世民)聽說很多人死于此因,便在微服出巡時射死這隻雞,投入井中,以石封口,村民在井址築起雞神廟。這樣的傳說口口相傳,至今在一些傳統村落中老人仍能講述。
墨畫
冠紅如火,尾黑如漆
漢代 鬥雞紋、鬥雞俑
“鬥雞”是古代一項給人刺激又無危險的娛樂活動,上自王公貴族下至平民百姓,鬥雞都很流行。據《漢書》記載,漢宣帝登基前常“鬥雞于杜鄠之間”。曹植曾作《鬥雞詩》:“遊目極妙伎,清聽厭宮商。主人寂無為,衆賓進樂方”。漢畫像石生動記錄了鬥雞的生猛場面:二雞如猛禽,怒目相對,昂首曲腿,厮殺即将開場。而漢代鬥雞俑則對此有更立體的呈現:陶人懷中抱雞,準備放開這隻鬥士,與等在前方的另一隻雞展開搏鬥。鬥雞活動的盛行也在語言文化上留下痕迹。今人用“呆若木雞”指人反應遲鈍,但這個成語的原意是指,訓練出的鬥雞鎮定自若的最佳狀态。
宋徽宗趙佶《芙蓉錦雞圖》
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等俗語則在強調雞有信德不失時。雄雞被賦予勇武品格與守時信德,因此上千年來不斷出現在花鳥畫中。
北宋徽宗趙佶繪制的《芙蓉錦雞圖》描繪了一隻錦雞飛臨芙蓉枝頭,回首翹望彩蝶的場景。錦雞,即雉雞,按儒家“瑞應”說,其出現是“聖王”出世的象征。因此宮廷畫中的錦雞多有政治含義,與雞相關的繪畫在中國藝術史中多有出現,從元代王淵《花竹錦雞圖》到清代郎世甯《錦春圖》,都以錦雞喻君子五德,具有教化功能。
段建宇《藝術雞》
70後的藝術家段建宇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藝術雞”系列。2002年,段建宇的藝術雞走下畫布,被做成玻璃纖維雕塑,然後一隻隻親手繪制,每隻雞均獨一無二。《藝術雞》首次露面是參加2002年韓國光州雙年展,2003年《藝術雞》參加第50屆威尼斯雙年展,一群雞在世界頂級大展——威尼斯雙年展軍火庫展區自由散步,讓人又驚又喜又忍俊不禁。将日常叙事引入卻又穿梭于現實與虛幻之間所形成的具有荒誕意味的圖像,顯露出了當代繪畫所實驗的新方法與策略。
呂勝中《大公雞》
現當代藝術中,齊白石、韓美林、黃永玉等對雞主題的創作則超越了教化意味,更多是基于雞本性及吉祥寓意的傳承。50後藝術家呂勝中一幅5×3.6米的巨幅作品《大公雞》在2015年底展出。呂勝中的原作以一張油畫布繪成,鱗甲覆蓋的鳳爪穩于岩石之上;五色羽毛挺拔,尾羽如絲緞一般簌簌。展覽現場,原作被按比例縮放至76×49.72cm,通過逐行拍攝将18平方米原作拼接制作成高清數字文件,再以藝術微噴的工藝将作品完整還原在油畫布上,畫框結構則采用中國傳統的榫卯方式。
呂勝中曾回憶這幅畫的創作原由;“幼時春節,鄰居家見一張大公雞年畫,喜愛不已,而難以獲得,日思夜想,夢見它站在我家牆頭引頸高歌,呼喚着童年理想化鄉土田園……我重新演繹這隻上世紀的大公雞,讓它就站在這塊幸存的石頭上靜觀驚奇,啼聲中幾十年拂曉,農業社會的現代化進程在理想化的不斷演繹中越發濃豔,渲染着我心中遠去的故鄉。”
徐悲鴻《雨中雞鳴》
至近代,雄雞常被畫家借以表達君子正義情懷,以及為理想而戰鬥的精神。徐悲鴻曾繪各種雄雞圖,如《雨中雞鳴》繪一隻雄雞霸氣立于一塊大石上,引吭高歌,鳴音似有沖破壓抑大雨的氣勢。徐悲鴻筆下的雞,冠與爪之刻畫精細嚴謹,尾巴以濃墨大筆掃出,冠紅如火,尾黑如漆,粗與細、紅與黑的對比中呈現出一種和諧。畫雞成為他在畫馬以外的另一絕,并内涵深意:徐悲鴻以此呼喚那些有血氣的志士,奮起拯救民族危難于水火之中。
(下轉A16版)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