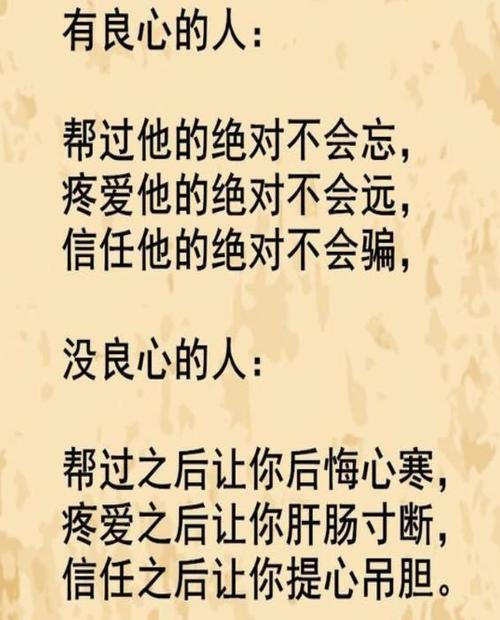作者 王鑫蕊
對薛寶钗的解讀一直是一個熱度不減的話題,部分讀者出于對“兩位玉兒”的愛不啻将寶钗的一舉一動都做出一個陰謀論的解釋,讀來令人隻覺逼仄寒冷。《紅樓夢》旨在“懷金悼玉”,作者在神瑛侍者與绛珠仙草的美好神話之外時時不忘懷“金”,為何而“懷”,有何可“懷”,這“懷”字又從何說起呢?
餘英時在《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中認為,作者塑造了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大觀園内的理想世界與大觀園外的現實世界。大觀園作為曹雪芹苦心經營的一個烏托邦,是女兒們青春的王國,其中的建築與居所分别契合了不同人物的人格特點。李纨的稻香村缟素寡淡,探春的秋爽齋明亮闊朗,林黛玉的潇湘館曲折幽深。而蘅蕪苑作為主要人物薛寶钗的居所與性格投射,作者也在其安排上下了不少功夫。
蘅蕪苑外表的平淡無味契合寶钗的外在觀感,“白”與“冷”是寶钗的主要基調,且看關于她的意象:雪洞一般的屋子,雪裡埋的金簪,興兒說她:“竟是雪堆出來的。”她的詩:“胭脂洗出秋階影,冰雪招來露砌魂。”白色,寒冷,無味,這是薛寶钗的外部表象,就連冷香丸的那一縷幽香竟也是“涼森森”的。
而内在的她博知冷靜,寬容善良,她替湘雲作東開社,周濟邢岫煙,将香菱帶在身邊,幫探春理事,于母兄份上聰明懂事……同時,她也是寶黛二人的道德導引者。曹雪芹是熱衷于用兩個玉兒的唐突與狹隘來反襯寶钗的,于是便有了“寶钗借扇機帶雙敲”,坦白自己的胸懷坦蕩,也有了“蘅蕪君蘭言解疑癖”,告知她欲望的終點。
“金蘭契互剖金蘭語”一回,是全書三位靈魂人物的一次最終融合,是這本書裡最讓人動容的一章,孟光接了梁鴻案,黛玉被寶钗的寬容與博愛感動,坦誠了自己往日的多疑猜忌,于是不知幾時休的風雨中有寶姐姐送來的燕窩,有穿的漁翁一般的寶玉的殷殷叮咛,也有相贈玻璃繡球燈的拳拳之意,這三個最高貴的靈魂相互觀照,交相輝映。
薛寶钗亦是少有的懷着憂慮看待家族命運的冷靜者,保持着大廈将傾前的警覺。她見邢岫煙身上的玉佩,便道:“你看我從頭至腳可有這些富麗閑妝?然七八年之先,我也是這樣來的,如今一時比不得一時了,所以我都自己該省的就省了。”她又及早看到賈家衰退的趨勢,及早搬出了園子,抄檢大觀園時也就省去了許多麻煩。
宿命論下黛玉的前身來自一個美麗的天上的神話,三生石畔的绛珠仙草為償還神瑛侍者的眼淚随其來到人間。而寶钗的金鎖來自一個和尚,是一個勘破人間風月的凡人,以一顆冷香丸諄諄告誡。
蘅蕪苑的“别有洞天”,意為在寶玉與黛玉之外的另一種理想人格,它克制,順從,寬容,博大,是另一種曹雪芹認同并且尊敬的生命狀态。作者充分展示了黛玉與寶钗兩種人格的方方面面,一個屬于性靈,一個屬于現世,他把賈寶玉擺在這兩番天地之間做出一番抉擇。而無論選擇哪一個,另一個也不是沒有意義,也并非不美。
賈寶玉夢遊太虛幻境,因警幻仙子偶遇甯榮二公之靈,囑咐她:“吾家自國朝定鼎以來,功名奕世,富貴傳流,雖曆百年,奈運終數盡,不可挽回者。故遺之子孫雖多,竟無可以繼業。其中惟嫡孫寶玉一人,禀性乖張,生性怪谲,雖聰明靈慧,略可望成,無奈吾家運數合終,恐無人規引入正。幸仙姑偶來,萬望先以情欲聲色等事警其癡頑,或能使彼跳出迷人圈子,然後入于正路,亦吾兄弟之幸矣。”此處甲戌側批:“這是作者真正一把眼淚。”甯榮二公期待着警幻仙姑将寶玉“規引入正”,使其“繼業”,然遊曆一番的寶玉“癡兒”到底“竟尚未悟也”。三春事業盡付東風,作者也難免為此灑一把眼淚了。
“濟世”是賈寶玉的祖父甯榮二公對賈寶玉的期待,亦是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平生的理想。而寶钗,是這理想人格狀态的具象化身,是從“癡”中解脫出來回歸正統的儒家理想。她有着對家族前途的憂慮和清醒認識,有着對德性和“仕途學問”的追求意識。
黛玉說自己不過是草木之人,正對應了她绛珠仙草的前身,草木,象征着生長,象征着旺盛不滅的生命意識,而寶钗的金鎖,卻象征着封閉與安全。寶钗早年也曾淘氣過,背着大人看些《西廂》《琵琶》,《元人百種》,也曾愛那“富麗閑妝”,卻早早地看清了這些的無意義。她的理性是那無節制的浪漫與自由的對照,是在青春終将落幕,繁華終将散場前的一條生路。薛寶钗是祖輩理想中的看清了繁華瞬間,領悟聲色最終走向正途的寶玉的形态。
在第二十二回《聽曲文寶玉悟禅機》中,黛玉道:“至貴者為寶,至堅者為玉。”寶钗與黛玉各分得寶玉一字,寶钗的貴,貴在世事洞明後的淡然與寬容,黛玉的堅,在于對青春與靈魂契合的執着追求。“戕寶钗之仙姿,灰黛玉之靈竅”,二者一樣可悲可歎,世事歸于虛空之時,仙姿與靈竅俱滅,也就是一場夢的散場。追求個性自由也好,踐行倫理道德也好,最後的結局仍是情的枯竭和德的失落。
然而“運敗”與“時乖”下真正的出路在哪裡呢?我們與作者都不得而知了,“歎人間,美中不足今方信”,困惑,到底是文學永恒的主題。
“可憐辜負好韶光,于國于家無望”。愛與自由讓人動容,可現實的殘酷卻證明了理性的意義。精神的一旦幻滅,要以何來支撐生命呢?寶玉是世事與人情的體驗者,寶黛二人是其引導,黛玉指向人情,寶钗指向世事,二者不可兼美,寶玉必須在二者之間作出取舍。作者站在茫茫大荒裡,身處太虛幻境中,肯定與歌頌的是這樣的情感,但對于人世生活的無常,作者卻也意識到這理性的重要意義。
但最終的結果我們已不需再提,賈寶玉到底未能繼承先祖的遺志,成了“古今不肖無雙”。作者借薛寶钗之名,向着祖輩的夢想和期待,遙遙地點頭緻意,向甯榮二公,也向着楝亭公曹寅:您那閃光的理想我理解并懂得,您那曾經的輝煌功業澤被了後世,使我得益于您的庇蔭,可這生隻有一次,縱使再來一次,空對着山中高士的寬容與仁德,終不忘那曾使我靈魂震蕩的愛與熱情。您說得懇切,我于“貧窮難耐凄涼”之時或許總會了解,可生命終将化作那無形的灰與煙,那條雪白的膀子也畢竟沒有長在黛玉的身上,到底是摸不得的呀。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