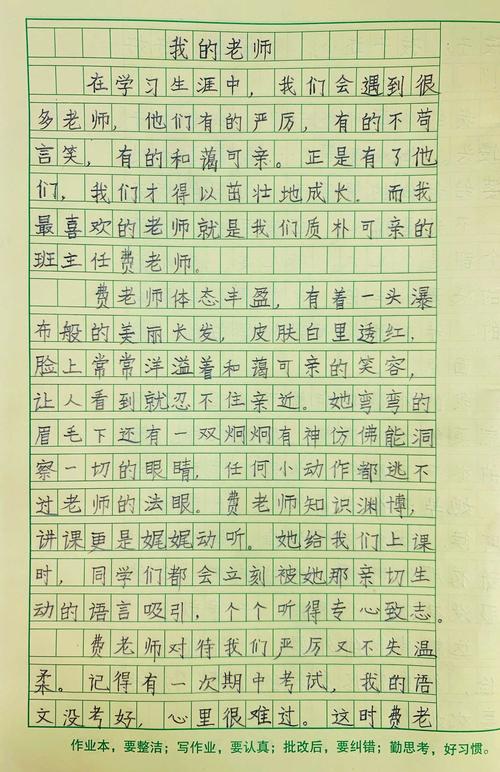上海一戶居民樓裡,兄妹三人爆發了一場争吵。
“我不同意!”
“這是媽剛生病的時候就交代過的,我是順着媽的意願的。”
“老娘是年紀大了,被他們的宣傳搞暈了頭,這破壞家族風水你知道嗎?”
卧室裡床上的老人安詳睡着,剛剛客廳發生的激烈争吵似乎都與她無關。
大兒子坐在床邊,拉着病重母親的手呢喃:“你為什麼要我們做這麼難的決定啊......”

你,為什麼會選擇捐獻自己的遺體?
這是老人三個孩子難以理解的選擇,也是很多人心中的未解之問。
為醫學貢獻VS讓遺體保全,選擇哪一個都無關對錯。
但做出捐贈遺體的決定,無論是對當事人還是身邊人,都是關于人性和愛的考驗。

01▼
“我老婆要去做老師”
死亡、清潔、裝袋、急速冷凍、送入醫學院保存......
這是遺體捐獻者死亡後,8小時内的曆程。
徐玉娥,大體老師,女,48歲,往生日期:101/02/23。

2012年2月,徐玉娥患病去世。
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台灣開始推動宣傳遺體捐贈時,徐玉娥和林惠宗夫妻倆便給遺體捐贈中心打了電話,填寫了捐獻遺體的同意書和信息表。
身邊人是不是都能接受他們的決定,他們不在意。因為他們願意給彼此簽下同意書,這就夠了。
妻子先走一步,按照20年前約定的那樣,她的遺體被捐贈出去,分配到了輔仁大學醫學院。

他和還不知道妻子去世消息的朋友說:“我老婆要去做老師了。”
朋友問:“什麼老師?”
“大體老師。”

遺體捐獻者,被醫學生們尊稱為“大體老師”。
但遺體捐獻出去後,最快要兩年後,才會被送上解剖台。
防腐一年後,還要再放一年,這麼做是為了照顧家屬的心情。

去世的第三年,徐玉娥的遺體仍被放置在輔仁大學醫學院中。
她被裹在密封的塑料袋中,蓋着白布,躺在格子裡。
每回他去看妻子時,都會隔着厚厚的袋子撫摸她的腦袋。
妻子去世後,林惠宗隻在夢裡見過她一回。朋友說,這是因為生前對她好,所以死後她不願來打擾他。

他對妻子說家裡一切都好,說想讓兒子去當警察,說他多麼以她為驕傲......
“老婆,你現在是大體老師,那你以後要去哪裡?可能你現在也已經不在了。我講的話也沒有聽到,也沒人知道,但是還是要跟你講。”
他絮絮叨叨,然後慢慢哽咽。

兩年裡,林惠宗每隔一兩個月,都會開車從嘉義到台北去看望妻子。在輔仁大學“大體老師”們的家屬中,他是去得最頻繁的一位。
徐玉娥去世後就被送到了醫學院,沒有辦葬禮等任何儀式。也正因如此,女兒總覺得還有些事情沒完成,媽媽還沒離開。

02▼
她以生命
教導我關于死亡的課題
遺體需要通過評估,經過處理後,才能成為“大體老師”。對處理這些遺體的工作人員來說,這個過程也有些煎熬。
輔仁大學一名工作人員在工作半年後,才慢慢調整好自己的心态。

他經常看到林惠宗過來看望妻子,在某次林惠宗準備離開時,他說:“我希望我不會處理到你。”
林惠宗笑着回答:“那有什麼關系,反正你經手這麼多了。”
“可是那個都不認識。我還沒有做過認識的,所以我不知道有沒有辦法。”

遺體處理好後,貯存在冷藏格中。但在他們真正被送上醫學解剖台前,還要經過一道道鄭重嚴肅的流程。
首先,醫學生們需要和大體老師的家屬進行一場真誠對話:大體老師的生日、性格、喜好、生前的故事、捐贈目的......
這些了解,讓一具遺體回歸為一個鮮活的人。

在解剖課程開啟前,醫學院還會邀請家屬參加感恩禮。
學生代表緻辭:“他們不但慷慨将自己的身體當作禮物奉獻給輔大醫學院,并親自以身體來教導我們,他們是我們所尊敬的無言良師。”
緻辭結束,上香,鞠躬。
這些看似繁瑣的流程,卻是關于生命最重要和觸動人心的一堂課。

此後,他們開始真正成為一個大體老師:
解凍、剃掉頭發、解剖、觀察身體構造和器官變化、探讨病情......
每堂解剖課結束後,學生都會向大體老師鞠躬喊道:“謝謝老師。”

但事實上,做出遺體捐獻這個決定,對在乎“身體發膚”和“入土為安”的中國人而言,尤為艱難。
因此不少醫學院都缺大體老師。
沒有多少人能直面被解剖過的親人,為了讓家屬不産生怯意退縮,解剖課程一旦開始,家屬們就不能再見他們。

在遺體将要被用于解剖課程前,林惠宗去看了妻子最後一眼。
他像往常一樣平靜地同妻子說話:
“那些學生,他們會好好對你啦。
以前來看你都沒什麼感覺,就是你在這邊已經很安穩。
然後今天早上要出門,越想越不舍。
常常跟人家講好像沒什麼,可是,可是......”
林惠宗哭了。

而那位一向理性的解剖學教授,面對母親想把自己的遺體捐獻到她所在大學的要求時,也忍不住表現出抗拒。
“很多人說你學解剖的,應該看淡生死,其實并沒有。
如果我媽要成為大體老師,那我有兩個要求。
第一,她不要捐來我任教的學校;
第二,那一學期的課程我不要參與在裡面。”

徐玉娥的女兒在參加完感恩禮後,也拒絕了最後一次去看媽媽的機會。
福馬林将媽媽的身體泡得發暗,變色,她不願将這個身影,與記憶中笑意盈盈的母親重疊起來。

但即便如此,她們還是沒有退縮,也不後悔地做出了決定。
在學期解剖課程結束後,女兒林映汝作為家屬代表上台發言:
“我的母親是一位平凡的女性,她賦予子女生命,而最終又以她自己的生命教導我關于死亡的課題。
我的母親又是如此不平凡,雖然她的生命已經結束,但她以自己的肉身作為教材,帶領同學們認識人體的奧秘。
我的母親如此平凡,卻又如此不平凡,她的生命已經結束,但她留下了無盡的愛。”

03▼
無言良師
在某個問答應用上,有個問題是:第一次見大體老師是什麼感覺?
同互聯網上常有的戲谑、惡搞、抖機靈畫風不同的是,這個問題下面的回答,滿屏都是敬畏與嚴肅。

有個答主說,印象最深的大體老師是一位三歲男孩。在他病危時,父母将他的眼角膜捐了出去。他去世後,遺體就捐給了醫學院。
那個小男孩躺在解剖台上,小小一隻,但足以讓在場的醫學生們,滿懷敬意地鞠躬喊聲”老師“。
性别、年齡、職業......無論他們生前擁有怎樣的身份和角色定位,在那裡他們都值得最大的敬意。

而這樣的故事,實在太多。
今年2月22日上午,山東青島一對新人領證結婚。當天下午,兩人去辦理了器官和遺體捐獻手續。
面對不吉利的說法,他們隻說:“隻要器官能夠救别人,比吉不吉利重要多了。”

浙江23歲的退伍軍人屠樓宇,将遺體捐贈給了杭州師範大學醫學院。
而在此之前,他還捐獻了自己的眼角膜。

45歲男子胡宏奇突發腦溢血死亡,年邁的母親将兒子的器官捐獻出去,給6人帶來了新生。而他當初是随同母親一起簽下的遺體捐獻協議。
母親說:“他沒走,他的心還在别人心裡跳。”
而兩年前疫情剛暴發的時候,武漢市火神山醫院收到了28具捐獻遺體。
強忍突失親人的悲痛,他們無私捐出親人遺體,與來勢洶洶而陌生的病毒抗争。

雖然完成”使命“後,他們的遺體會被縫合,卻仍然無法複原成最初的樣子。
但是,他們接下了醫學生從醫路上的第一刀;他們是無言良師;他們是生命延續的希望。
曾有患者病逝前留下遺言:“你們可在我身上切千刀萬刀,為的是你們以後不要在患者身上切錯一刀。”

他們本身的存在,讓未來的醫者們感受到了肩膀上沉甸甸的重量。
死亡讓人恐懼,生命讓人敬畏,而“大體老師”,讓死亡的冰冷和痛苦,擁有了溫度和光亮。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