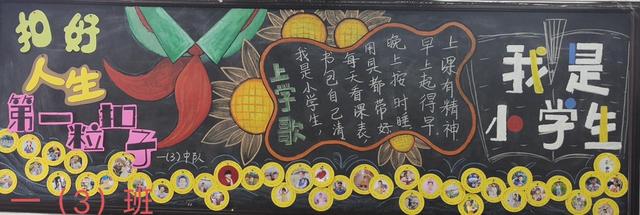“就深層次來看農村與城市婦女是有聯系的。即便是城市婦女結婚,也常常要男方或男方家庭買房,依稀可以看到男娶女嫁的影子。我從2000年起一直緻力于農村婦女權益保護,正是基于城市婦女與農村婦女的深層聯系。” 
本文首發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王佳薇
編輯 / 周建平 [email protected]
2021年12月24日至2022年1月2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修訂草案)》(以下簡稱“修訂草案”)通過全國人大網面向全社會公開征求意見。截至2022年1月22日,意見征求共有8.52萬人參與,收集了42萬餘條建議。
這部頒布于1992年的法律再次修訂,引發了極大關注。與上一版本相比,新的修訂草案明确列舉了性騷擾的常見形式,闡釋了歧視婦女的具體含義,禁止各種形式的精神虐待等等,被許多學者視為進步的信号。
在衆多的修改細則中,我們注意到,針對農村婦女土地權益受損的問題,修訂草案增加了“婦女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确認,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一項。同時,修訂草案強調“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應組織婦女參與制定村規民約、居民公約以及有關婦女權益事項的協商議事活動”。

中國人大網上,參與婦女權益保障法(修訂草案)的人數是同期在征集的其他法律草案參與人數的近百倍
由李慧英帶領的中央黨校課題組與河南社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梁軍将河南周山村作為試點,在此推動性别平等、糾正生男偏好。過去,“出嫁女”一直是農村頗有争議的群體。在夫家,她們的利益深刻地與丈夫捆綁在一起。當她們的婚姻狀态發生變動,回到出生村,卻被視為“潑出去的水”,無法分得集體組織的土地和經濟收益。從2008至2015年,課題組協助周山村黨支部和村委會一共進行了三次村規民約的修訂。如今,周山村的村規民約明确規定“婚出男女因離婚或喪偶,将戶口遷回本村者,可享受村民待遇”。
繼周山村之後,黑龍江、安徽、江西、江蘇、廣西、陝西等地的多個村落相繼依照周山村村規民約的範本,制定性别平等的村規民約。2012年,原國家人口計生委在河南登封召開現場會,組織全國16個重點省的48個縣領導進行培訓和考察,并與聯合國人口基金合作,在重點省份推動修訂村規民約的工作。多年來,這些工作取得了許多成效。例如,從2011到2018年,安徽省長豐縣作為“中國/聯合國人口基金第七周期社會性别平等項目”的試點縣,通過種種做法打破傳統觀念,包括用村規民約明确女性的政治經濟權利;主張女性通過村民代表大會行使權利;鼓勵新生兒随母姓;通過公廁改革去改變政府分配公共資源的性别盲區;通過技能培訓幫助女性提高收入,提升家庭地位,從而建立性别平等的社會氛圍。
以修訂草案為契機,《南方人物周刊》采訪了社會性别與公共政策研究學者、原中央黨校社會學教授李慧英,談修訂草案的進步性與待完善之處、周山村修訂村規民約的實踐。在李慧英的觀察中,婦女面臨的困境無法用單一的原因概述,農村婦女土地權益受損牽連着生男偏好、性别比失衡等一系列問題。

2019年,陝西商洛柞水縣營盤鎮龍潭村,一場喜氣洋洋的婚禮 圖/視覺中國

“出嫁女”問題,從集體成員資格談起
南方人物周刊:從修訂草案聊起吧,在财産權益那一章,新的草案明确規定了“婦女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确認、土地承包經營、集體組織經濟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安置補償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婦女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确認”這一點是新加的。
這點非常有必要。土地承包以來的婦女地權受損,從根本上說,就是取消了“出嫁女”的成員身份(資格)。沒有了成員身份和資格,就得不到集體收益。2015年以來,農業農村部門開始推動集體産權制度改革,涉及了産權主體的明晰化,成員資格認定被提了出來——集體資産和土地如何分配?它的主體是誰?2007至2020年,全國農村搞集體成員資格認定,出嫁女的資格認定同時被提了出來。
南方人物周刊:一個外嫁的女兒為什麼不能獲得出生地的集體成員資格?
認定集體成員資格,各地各村做法不盡相同。一般而言,有三種做法。第一類是原始取得,父母是本村人農村戶口,作為男性後代在村子裡出生、長大,就可以自然取得集體成員的資格;第二類是法定取得,有了法律手續,結婚的媳婦、領養的孩子、變遷的移民都可以取得集體成員資格;第三類是申請取得,通常是集體組織有争議的、流動性強的人群,比如大學生、非農化的公務員、出嫁女等被列入申請取得,要經過集體成員2/3認可。
這其中,“出嫁女”是最有争議性的群體。在一些鄉土文化看來,婦女一定要外嫁,不再具有出生地的成員資格。此外,還包括喪偶、離婚、改嫁的婦女。這些人都是按照男娶女嫁的規則認定成員身份,她們的婚姻一旦發生變動,村内會立馬排斥,覺得她們不再是村内人,要把(她們)享有的權利拿回來。而且,她們的子女也被視為不應享有村内集體資源的分配。而村民自治大多通過多數表決,隻要多數人不贊成就可以立即取消她們的成員資格。
這種現象在全國都十分普遍。我們(中央黨校性别平等政策倡導課題組)2016年曾通過安徽、廣西、湖北3個省6個縣的計生辦挨村發放調查問卷,在收回的1508份問卷中,我們發現:“出嫁女”、離異喪偶、上門女婿及其子女不享有村民待遇和福利的占84.45%;服刑人員不享有村民福利的占20.43%;而已經脫離了農村的公職人員仍享有村民福利的平均占35.77%。由此可見,一旦涉及集體成員資格的認定,多數決總是将婦女排除在外,這個問題變得很普遍。我們應該想辦法保障農村婦女的成員資格與土地權益。
南方人物周刊:“出嫁女”一定要通過丈夫認定成員資格說明她們不被視為獨立的個體?
婦女要想得到土地權益,一定要到丈夫的村莊,通過自己的丈夫。她不被視作一個主體來看待。這跟我們國家法定的男女平等精神是相悖的。我們現在的法律中明确規定:“婦女在農村土地承包經營、集體經濟組織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補償費使用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問題是怎麼讓法律的平等主張落地,具體怎麼做才能不讓法律被架空。
南方人物周刊:通過裁判文書網,我們可以看到很多與“出嫁女”有關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益糾紛案件,法院對此類案件的判決往往以“出嫁女”是否具有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作為其能否獲得土地收益或集體資産收益的前提。由于全國沒有統一的資格認定标準,各地人民法院在相關案件判決中對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認定依據和認定标準很不統一。關于集體成員的資格認定,你認為如何界定才能更好地保護婦女權益?
村内的成員資格認定一般都是通過村民自治的多數決原則,對很多法官來說,他們找不到法律上對成員資格的認定,無法依法約束并糾正侵犯女性權益的做法。因此,國家從立法層面對有争議人群作出具體的規定很重要。這是依法治理的第一步。法律有明确條文規定後,地方政府必須依照規定執行,法官在判定時也可以有法定依據。
2009年,河北邢台市中級人民法院曾出台《關于審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收益分配糾紛案件若幹問題的意見》,第一次在審理意見中對集體成員資格進行了界定,具體劃分了二十多類人群,将争議人群列入原始取得與法律取得類型,還特别對争議極大的“農嫁女”人群進行認定。農村婚嫁女及其家人一律被納入保留成員資格之列,詳細闡明其權利,從根本上堵住争議人群成員權受損的漏洞。
這裡面很重要的原則是任何一個人都不應該兩頭空,與此同時,任何一個集體組織成員也不能兩頭得。這一原則不僅針對婚嫁婦女,對農村其他有争議的人群同樣适用。如果農村依法治理,“出嫁女”土地權益被剝奪的問題就能得到解決。
南方人物周刊:多數決這一村民自治形式适用于哪些決策,為什麼在保護婦女權益方面有時候是失靈的?
多數決适用于公共領域的決策,比如村幹部的民主選舉,要得到半數以上村民的同意,村幹部一定得代表老百姓的意願。又如,村莊公共事務決策要公開透明,村民可以參與決策過程,不能村幹部說了算。但另一方面,有些涉及個體權利的私人事務,如果用多數決來決策,很容易剝奪個體權利。比如,一些村的村規民約中規定:“純女戶家庭隻能有一個女兒留在本村享有成員資格與村民待遇。”如果你家有兒子,女兒就不可以留下。個體權利一旦被納入村民自治多數決,就會造成少數人利益受損。婦女利益受損就與多數決直接相關。所以,涉及婦女權益不能采用多數決。
南方人物周刊:另一個問題是,随着城鎮化發展,農村土地被征用的補償款,有的地方以戶為單位賠償,這也導緻了家庭内部的女性分不到錢。
這種征地補償款不由集體統一發放,而是按照戶的土地面積進行發放。征地款發給戶主後,由戶主自行決定發給子女。不過,絕大多數家庭的戶主再進行戶内分配時,往往是給兒子不給女兒,哪怕女兒結婚後的承包地依然在娘家,照樣得不到。
2012年8月,我采訪了東北某村莊的一位婦女,她告訴我自家有三姐妹,一個弟弟,土地承包是按照家庭六口人分的。她後來嫁到丈夫所在村,身為長女,還是幫父母蓋了房子。後來她家土地被征用後,得到一筆50萬元的賠償款,她父親把這筆錢全給了她弟弟,幾個女兒一分錢都沒分到。所以,家庭以戶為單位,往往也會剝奪婦女的土地權,隻是這種剝奪往往是隐形的,女兒們礙于親情不便公開抗争。

2018年4月14日,安徽合肥長豐縣陶樓鎮新豐社區廣場,志願者正在為村民發放電風扇、助聽器、書包、文具等物資 圖/中新社

修訂村規民約的實踐
南方人物周刊:修訂草案也提出“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應當組織婦女參與制定村規民約、居民公約,推動解決婦女關心的現實利益問題”。你曾參與河南周山村制定村規民約,根據村子具體情況制定村規民約是推動性别平等、改善婦女土地權益受損問題的辦法嗎?
是改善婦女土地權的有效辦法之一。推動周山村修訂村規民約一開始是有阻力的,傳統觀念根深蒂固,開展工作很難。2006年,周山村的土地流轉給大冶鎮政府管理,村民每年每人可分得“口糧款”800斤小麥(折合款)。為了分配“口糧款”,2007年,村兩委制定規則十三條,其中規定:“婦女婚後戶口未遷出者,離婚、喪偶後回村居住的婦女,不參與‘口糧款’分配。”村中每年分配“口糧款”時,都會有人到村委會告狀,吵得不可開交,更有甚者拿着木棍來到村委會準備打架。每到此時,村組幹部都處于“戰備”狀态,生怕鬧出人命。所以,村幹部也希望借修訂村規民約的契機化解這一矛盾。
從2008年至2015年,課題組協助周山村黨支部和村委會一共進行了三次村規民約的修訂,整個過程一切都靠民主協商,老人、婦女、村民代表和村組幹部都要參與其中。過去村裡沒幾個婦女參政議政,重要事務都由男性戶主和幹部決定。現在周山村修訂新的村規民約,有1/3的婦女代表參加,而且,婦女代表還得有性别平等思想。
南方人物周刊:如何判斷一個婦女是否有平等思想?
周山村婦女參與修訂村規民約時,一開始就采取特邀的方式,由村民代表表決通過邀請1/3的婦女代表參加起草。她們能站在婦女角度為婦女權益發聲。許多村莊都出現過媳婦反對女兒留在娘家村的現象。周山村起草草案時,接受過性别平等培訓的絕大多數婦女代表都是周山村的媳婦,她們能跳出從夫居的立場,領悟了男女平等的本意,提出想留在村裡的外嫁女也應當享有村民待遇。這得到了婦女代表和村幹部的支持,從而寫入具有平等理念的村規民約條款:男到女家、女到男家均可,都可以享受村民待遇,“婚出男女因離婚或喪偶,将戶口遷回本村者,可享受村民待遇。”性别平等思想就是對男女兩性權利的同時保障,而不是犧牲一個性别保障一個性别。
南方人物周刊:全國有不少地方借鑒周山村的經驗修訂村規民約。在這其中,比較突出的是安徽長豐的創新社區和南圩社區,我記得它們是最早對随母姓家庭給予獎勵的社區。
長豐是周山村之後推廣的三個試點縣之一,創新社區和南圩社區又是長豐縣的試點社區,當時計生部門做推動時,希望借此弱化生男偏好。生男偏好背後除了父居還涉及父姓,隻能随父姓意味着隻有男孩可以傳宗接代,女孩是不可以的。為了促進生育觀念的轉變,創新社區和南圩社區寫入新條款:“凡是新生兒随母姓,可以獎勵800元到1000元。”

“與性别不平等觀念脫鈎,是對所有人的解放”
南方人物周刊:最近我聽一個讨論修訂草案的講座,發現大家關心的問題更多和城市女性相關。相比而言,農村婦女的土地權益似乎是被忽視的,這一問題如何與城市女性相關聯?兩者之間真的毫無聯系嗎?
婦女群體是很多元的,她們的處境也不完全相同。農村婦女如果進城務工,可能會和城市婦女面臨相似的問題。但大部分農村婦女面對的問題是農村獨有的,比如宅基地的分配。這些問題城市婦女可能不太會關心。很多農村婦女很關心這次修訂草案的第四十二條,涉及農村婦女的成員資格與基本權利。但是,就深層次來看,農村與城市婦女是有聯系的。即便是城市婦女結婚,也常常要男方或男方家庭買房,依稀可以看到男娶女嫁的影子。隻是,在農村男娶女嫁更具有強制性,婦女的自我選擇更受限,父權制的烙印更重。我從2000年起一直緻力于農村婦女權益保護,正是基于城市婦女與農村婦女的深層聯系,為農村婦女争取權益,同時也是為我們自己、為每一個女性都能擺脫父權制的束縛有尊嚴地生活。
南方人物周刊:随着權利意識的加強,女性越發懂得如何捍衛自己的權利,另一方面,一些男性會認為“這是以單一性别視角征求法律援助,索取的是特權”。無論在鄉村或城市,這種割裂其實是非常明顯的。
有同感,特别這次修訂草案征求意見,我明顯感覺到男權與平權的差距之大,男權人士會認為《婦女權益保障法》走得太快了,很想拉回去。而追求性别平等的人士覺得還不夠,需要繼續往前走。這種撕裂與對立,說明性别平等的價值觀還遠遠不能被更多的人普遍接受,也說明在社會大衆當中進行性别平等教育多麼必要。
令人欣慰的是,修訂草案的第十一條規定:“國家将男女平等基本國策納入國民教育和培訓體系。”實際上,國務院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自2012年就開始在一些中小學開設試點課程。課堂上,老師會啟發孩子:怎麼看待媽媽做家務?家務勞動有價值嗎?如果有價值,爸爸媽媽能不能一起來做?女孩可不可以發怒?男孩能不能哭,可不可以表現柔情和脆弱?這項工作有利于改良文化土壤,很值得繼續推動。通過學習性别平等課程,反思我們習以為常的觀念,改變性别刻闆印象。長此以往,男權與平權的對立就可以化解,撕裂會走向融合。 
(感謝王江濤、施璇對本文的幫助)


,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