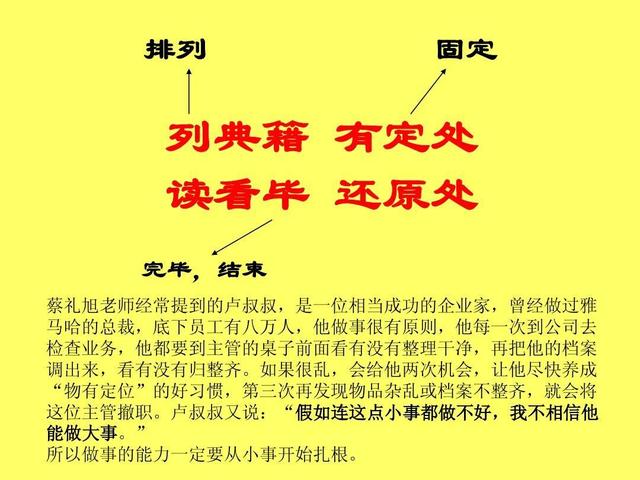“筆尖的光芒寫在黑夜的胸脯”
——周慶榮散文詩集《執燈而立》讀後記
文/齊鳳豔
《執燈而立》詩意蔥茏,思想繁茂,如果說每一章散文詩都是一株文字之優美姿儀與智慧之深邃神韻兼備的嘉禾良木,那麼整部書籍就是一部綴滿星星的天空。無論是在叢林漫步還是擡頭仰望,我都被一種熱烈的情意感召,被一種高尚的精神引領。周慶榮說,他要“用自己的作品,喚起蒙塵的理想和人性的溫度”。他的寫作是有使命感的寫作,這也是他重視散文詩思想性的原因,他針砭着、悲憫着、熱愛着、希望着,他一直在探尋日常生存與外部環境的關系,一直努力發出光亮彰顯生命意義,一直呼喚一顆顆發光的心。黃恩鵬指出,在周慶榮這裡,“執燈而立,不是口号,是星光落地時人心的安然和自在。”周慶榮希望每個人都有燈盞,都是燈盞,他希望每個人對思想的探尋對意義的追求和堅守使世界明亮,讓人間溫暖。周慶榮自己也這樣踐行着,《空間論》中下面的這句話是他的樣子吧:“動物中最高等級,一個人能用體内的骨頭保持站立起來的姿勢,一個人能用獨到的語言和意念從龐大的人群中走出來”。
(一)
在散文詩《讓我們一起執燈而立》中,周慶榮告訴我一盞燈面臨的危險:“被春天懶散的柳枝甩過來的細風,從深秋枯樹的落葉上一躍而起的壞脾氣,冰面上溜達而來的寒噤。”他也告訴我一盞燈存在的理由也是充分的:“比如黑雲壓城,比如伸手不見五指。更多的情形屬于日常的歎息,它們慢慢變成心底的陰霾。”這些現象都在日常生活中,所以“讓我們一起執燈而立”絕不是唱高調。他期盼的是,希望如萬草萌芽,俯拾皆是——這不隻是他在《靜守》中的精彩比喻。希望是光,人是要生活在希望中的。
自然在造人的時候,它隻創造了人的一半,另一半要由人自己通過創造性活動來完成。德國哲學家恩斯特·布洛赫在《希望的原理》一書中指出,人借助于自身的主動性與超越性為自身創造他的未來,希望是人性的根本,而希望的基礎則是人永遠不懈地自我超越。在《向藕緻敬中》周慶榮告訴我,藕是殘荷的希望和超越。這種超越現實、追求理想的精神是人的本性,生活在希望之中,就是活在可能性之中,從而形成存在的開放性。人如果不思突破其有限性,那就是死亡而不是人生。所以,執燈而立在另一層意義上講,是心存超越之希望和理想。周慶榮的《人間的地形隻是希望的田野》就是這樣滿懷超越之心和倔強不屈:
什麼才能讓生命的地形平等?
你說是死亡。
我想說的卻是希望。
當春雨如酒,冬天空蕩的杯子被斟滿,我們能否先不說結果,隻喝了這杯酒?
豪情來了,地形會升高萬丈。
你坐在萬丈裡,看春雨的作用。麥苗會長出骨節,油菜将挺直腰杆,不久,裝滿人間雜念的頭顱就會變成一片花海。
地形由人自己決定,這是對人的力量的肯定。周慶榮說:“生動的人間,即使苦難重生,如果有了信念,後面的生活才能永遠生生不息”(《佛閣:米拉日巴、詩與方法論》),“愛恨情仇和主動的奮鬥,它們都彌漫在日子裡”(《安靜是最可靠的氣勢》),“一切起伏的和淪陷的,包括寒冷的和溫暖的,最後的地形屬于希望”(《人間的地形隻是希望的田野》)。
對于寒冷,周慶榮是有凜冽的态度的。在《守護人——寫給可可西裡守護人索南達傑》中,他寫道:“不允許槍口的硝煙表達收獲獵物的喜悅。讓槍口對準偷獵者自己。”在《與鳄魚說》中,詩人說:“走在美好的河畔,我要做一個帶刀侍衛。假如鳄魚吞噬了我,我要剖開它的腹。我對鳄魚說:這是我的一次度假式的遊泳,而且,河畔隻能美好。”但是,守護人死于一次對沖突的制止,河邊有小生命被鳄魚吞噬。世界并不像預期的那樣美好,世态炎涼和人心的陰暗與明亮是世界的豐富性。《天涯》中,周慶榮是否在告訴我那些令人重複的惆怅和沮喪的人與事是考驗,而重複的堅定和希望是必須的。人心必須有不甘,世間萬物本無定局,它是可以改變的,人力雖然渺小,卻也是可以增長和積蓄的。這就是周慶榮倡導的“讓自己暖起來”的意義:“如果生活中生長出沮喪,我依然要用愛情的态度抱緊它”(《紅月亮》),“把手暖起來,太陽是戰勝時間的光源。然後,冰天雪地裡的同胞可以從容地握住另一個同胞的手。”
在周慶榮的語境裡,每個普通人都能夠成為提燈而立的人,每一個人都可以是一個小太陽,他相信有理想的人群的力量。對此,周慶榮有生動的比喻:“解構後的鵝絨那樣柔軟,一抱團就是堅定的信念”(《雨中觀蒲》)。而周慶榮《瑪尼堆和我》中的詩句則表達了這樣的含義:詩人的骨頭裡要一直保留着人類奮鬥和跋涉的勇氣,骨髓遇見空氣,永遠磷火般閃亮,要執燈而立,必須有勇氣和信念。周慶榮的《祝酒詞》中的如下充溢英雄情結詩句令我動容,頗受感染:
一醉是可以的,當萬物不休,我也不休。
懦弱是疾,歎息是疾,中途掉隊是疾。
有一天,當我不得不休,我想無疾而終。
就是說,人們看着我的背影,說:他有人的骨頭,他的勇氣讓歎息檢讨,他始終抵達了目的地。
這是祝酒辭,也是多年後我的墓志銘。
愛默生《詩人》有三處表達的意思是這樣的:一,詩人遲早都會将所有人吸引到他的身邊,因為所有人都倚靠真理,并且需要表達;二,任何事物如果不在詩人面前站立和行走,由詩人闡明它,它就不會行走、爬行、生長和生存;三,詩人的生命有限,但是他們的作品沒有止境,就像一面鏡子,從大街上照過去,随時都可以照出每一件造物的形象。批評家章聞哲評論道:周慶榮的詩作所呈現的“完美”的質,“堅持着公道正義,并且在這樣的理性的原則之上,還有希望之花的熱烈、堅韌與光明——因為期待,所以熱愛;因為堅持,所以深沉;抑或,因為有堅定的信念,所以有不折不撓的鬥争,所以有擔當,所以有仁義。”所以一段時間以來,我認真拜讀學習了周慶榮的很多散文詩,我感到周慶榮是那個有魅力的詩人,而優秀的詩歌也是燈盞,這是不是可以成為我所解讀的“執燈而立”的另一層含義?
(二)
“當你懷揣溫暖,哪裡能夠讓你冷?”(《異客》)這樣的詩句,總是那麼親切,能夠消融天地間所有冰霜。《水墨西塘》中詩人說:“以鄰為美的人,彼此互不設防,心有江南的漣漪,人性婉約。”然後我看到了這個心中裝滿熱愛的人的可愛的樣子。“慢跑幾步,沽來一壇花雕。”在西塘,在時空交錯中周慶榮摒棄漂泊感;他沽酒與古鎮人促席延故老,揮觞道平素,大有反客為主之勢。“用一個墨點渺遠去古鎮那頭的馬鳴庵,木魚寂寥,市井才能生動。”讀到這句,我想到了這部詩集中的另一首散文詩《淨峰寺》。在這首詩中,周慶榮寫道:“因為我不同意自己輕易地六根清淨,我依然固執地愛着人間……點燃三炷香,一炷坦陳我塵緣未了;一炷袅袅訴說渾濁背景下的忐忑;第三炷想告訴正在登山的人,我準備離開淨峰寺,下山,繼續當一名播種者……我播的種子,從此各有其名。它們分别是:善良、公平和幸福。”在《與螺髻山脈耳語》中,詩人則告訴我,他的生活“要删除下面的詞語:謊言、虛榮和膚淺的幸福。”
周慶榮的人生觀絕對不是隐逸的和出世的,在《叩問——觀戴衛寫生<老衲叩鐘>》中,面對一幅佛家題旨的畫作,他發出的也是一個入世者的叩問:
我是一個年長的勞動者。
我要每日三叩。
叩呈人間五味的真實,讓佛永遠是正确的知情者;
叩述人與人的差異,除了高尚和卑鄙之外,更多的人隻想尋常地活着;
第三叩,我想聽聽你的聲音。是不痛不癢的普遍的道理,還是對勞動者必将實現的回報的承諾。
我叩鐘啊!
在我坦承了一生的言與行,最後的鐘聲就是我的叩問。
勞動,總是包含價值實現、奮鬥目标、安居康泰、自由樂土等内容,是與幸福關系最密切的。周慶榮首先将幸福賦予給勞動者。而且在他的文本中這幸福的内涵是豐富的,具體的。
勞動的人們,坐在田埂上,一閉目,理想就在眼前豐滿。
平凡的人間,必有一部分内容屬于上升。
勞動者和大地的對話:
“我們讓美好落地,我們讓甜蜜真實,我們讓鮮花開放在稻香裡,我們讓喧鬧中的人們來到這裡,獲得天空的遼闊和生命的從容。”
勞動者在周慶榮這裡有一個完美的預設:他們勞動,他們有技術,他們獲得物質生活,他們還要有精神生活,即:“平凡的人間,必有一部分内容屬于上升。”這裡,周慶榮把人的發展與完善納入到了人的幸福中。讓個體的人發展完善,是社會的責任,是個體幸福感的主要來源,這也是一種社會範圍内的仁愛精神的根源之所在。沒有發展的事實證明,就沒有對國家、民族,乃至其他個體的愛情與友情,乃至責任感,因為,正是由于有希望,才可能願意付出,才可能認識到那一本體的鞏固,作為人民有所依的根基的重要性。對此,周慶榮在詩中的表達則更加生動:
“生活确實還要深入,更遠的路還要繼續走。我們的臉龐也真的挂滿汗珠,我們在大雲做一下歇息,讓田野的風拂去汗,仿佛一片雲擦拭天空。我們把這裡看成是一次和解,一次理療,更是一次自我鼓舞。”
這樣的詩句的生動來源于它與生活的貼近。在《散文詩和九言——獻給我剛出生的孫女九言》中,詩人寫道:“散文詩更仿佛生活本身,一些句子隻是生活原本的模樣,普通而自由,每個人的生命中一定會有光芒的時刻,它昭示着我們要相信詩意的人生。”
從這些詩作中,我感到周慶榮的理想主義,也更多的看到他的現實主義。他的批判與熱愛,關懷與擔當,都在一種毫不隐晦的語言形式裡表達着人本現實主義的思想。作品的現實主義精神還在于,他在書寫精神如何能動地為生存建立合法性,開辟足夠的伸展空間,以便生存能夠在緻遠,緻深,緻精微的方式中抵達宏闊與莊嚴。周慶榮的詩論中有這樣的語句:“思想的完成如果不食人間煙火,就是冰山上的雪蓮,它對大地上的谷子和麥子作用不大。”“現實主義地寫作,理想主義地讓自己有點兒精神!”現實主義,就不是陷于私人化泥潭,理想主義絕不驅逐崇高之魂,使詩歌流于對細瑣生活現象的浮光掠影的吟詠和把玩。《人間煙火才是萬佛之佛》中,周慶榮說:“人間煙火,應該永遠被注視。它是萬佛之佛,是一尊聖石的具體情感,是畫家筆下永恒的藝術魅力。”那麼,這人間煙火也是周慶榮散文詩寫作的及物對象,是周慶榮“認真地望天,卻說出自己對大地的熱愛”(《女娲補天》)。
(三)
在《執燈而立》的《代後記》部分,周慶榮主張散文詩走出多年來的唯美、抒情和密集修辭的誤區。這不是說,散文詩放棄美和抒情,而是要超拔出私人化泥潭,讓詩歌主題超越對細瑣生活現象的浮光掠影的吟詠和把玩,這與周慶榮散文主題中包含的大情懷是一緻的。但是周慶榮的散文詩是不拒絕優美的語言、精當的意象、豐富的聯想與恰切的比拟的。
《檔案裡的鐵匠》中,有“咚咚”的敲擊聲,有飛濺的火星,有燒紅的鐵砧,當他寫出“一塊燒紅的鐵等待被敲擊”的詩句時,鐵就有了一顆成長的心,周慶榮在毫無違和感地賦予事物以屬人的德性。“等待”,一個靜态的詞語裡,紅彤彤的願望在跳動。而這火熱的氛圍和力的贲張在周慶榮描寫勞動者“臂膀的肌肉如老樹軀幹上滄桑的瘤”時,語言産生了一種即視感,一個硬朗的青銅雕塑作品出現在我面前,而它的背景是火,或者它在火中。
《恰西草原》裡,周慶榮讓哈薩克騎士的馬鞭“鞭梢”甩出彩虹的聲音。《半枯的胡楊和晚陽》中,詩人寥寥數筆,勾畫了一幅極具象征意義的風景,衰竭的生命呈現出來的粗犷與堅韌震撼人心。更多的時候,比如《風筝往事》,詩中事物的隐喻與象征統攝全詩,申明主旨,比如冰、火、夜晚、黎明、春天、星星等意象。這是周慶榮“格物”寫作理念的具體實踐。格物的基礎是因為“事物内部的力量與我們身體中的意志暗合”(《如此一坐——觀戴衛畫<王維詩意圖>》),有時候“物我之間的善意互相作用,人性的溫度如溫暖的泉水從土地深處湧出”(《生活的頓号是一朵雲》);有時候在與物的周璇揣摩中,詩人感性形象地說出理趣、認識和思想,比如《後麥子時代》結尾詩句:“面粉是一種食糧,從麥穗上走下的麥粒,它們必須磨碎自己,必須重新彼此熱愛,然後必須混合”。《上等的磨刀石——黃姚古鎮石闆街記》中詩人則是要以石闆為磨刀石,他要把自己磨成刀、劍,走在石闆街上,詩人表達了對自我鍛煉和琢磨的渴望。
多年來,周慶榮是那個黎明前寫詩的人,他把“筆尖的光芒寫在黑夜的胸脯”(《對酒的答謝》)。每一個漫漫長夜都是他愛讀的書本。他在字裡行間讀出呼吸和呼吸者們永不停頓的努力,他讀遙遠的燈火如豆,讀海浪的咆哮代替了細雨霏霏的歎息,讀窗外矗立的樹幹俨然人群中的骨頭。夜色永遠不會熄滅他眼裡的光芒,他說:“不是黑暗包圍了我,而是我打入了黑暗的内部。”(《山谷的黑暗》)在《陰與陽》中,我看到了這句話語的另一種表達:
我心底的陽剛不會被任何溫柔所征服,因為即使我身處沙漠,我也一直要求自己溫柔似水地對待生活。
一切的陰,我都報之以陽。
包括我的夢,也隻能讓它蒸蒸日上。
堅持,或者确信,或者執着,是周慶榮的典型書寫姿态。他的詩文告訴我,他認真研墨,墨汁夠用就行,不浪費給卑鄙,也不用多餘的墨去抹黑别人。那年歲尾,當他再一次在白紙上寫下“除夕”,誰會想到他會把紙片點燃。曆史不虛無,未來需要火焰和燃燒的力量。我們期待周慶榮更多的精彩。向周慶榮緻敬。

齊鳳豔,筆名靜鈴音,遼甯康平人,遼甯省作家協會會員。作品散見于《文藝報》《揚子江詩刊》《散文詩》《星星·散文詩》《海燕》《詩潮》《人民海軍》《散文選刊》《芒種》等刊物。著有詩集《齊鳳豔詩選》,出版獨譯合譯詩集10部。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