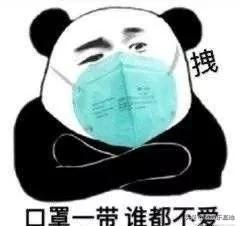中山公園預制型塑膠跑道?作者:遲子建我對哈爾濱最早的認知,是從父親的回憶中,今天小編就來說說關于中山公園預制型塑膠跑道?下面更多詳細答案一起來看看吧!

作者:遲子建
我對哈爾濱最早的認知,是從父親的回憶中。
父親童年不幸,我奶奶去世早,爺爺便把父親從帽兒山,送到哈爾濱的四弟家,而他四弟是在兆麟公園看門的,多子多女,生活拮據。父親在哈爾濱讀中學時寄宿,他常在酒醉時講他去食堂買飯,不止一次遭遇因家長沒有給他續上夥食費,而被停夥的情景。貧窮和饑餓的滋味,被父親過早地嘗到了。父親說他功課不錯,小提琴拉得也好,但因家裡沒錢供他繼續求學,中學畢業後,他沒跟任何人商量,獨自報名來參加大興安嶺的開發建設。爺爺的四弟得知這個消息時,父親已在火車站了。父親這一去,直到1986年因病辭世,近三十年沒回過哈爾濱。而他留給我的哈爾濱故事,多半浸透着眼淚。
父親去世後,1990年我從大興安嶺師範學校,調轉到哈爾濱工作。每次去兆麟公園,我都會憂傷滿懷,想着這曾是父親留下足迹的地方啊,誰能讓他的腳印複活呢。
初來哈爾濱,我的寫作與這座城市少有關聯,雖是它的居民,但更像個過客,還是傾情寫我心心念念的故鄉。直到上世紀末我打造《僞滿洲國》,哈爾濱作為這個曆史舞台的主場景之一,我無法回避,所以開始讀城史,在作品中嘗試建構它。但它始終沒有以強悍的主體風貌,在我作品中獨立呈現過。十年過去了,二十年過去了,我在哈爾濱生活日久,了解愈深,自然而然将筆伸向這座城,于是有了《黃雞白酒》《起舞》《白雪烏鴉》《晚安玫瑰》等作品。
熟悉我的讀者朋友知道,我的長篇小說節奏,通常是四到五年一部。其實寫完《群山之巅》,這部關于哈爾濱的長篇,就列入我的創作計劃中。無論是素材積累的厚度,還是在情感濃度上,我與哈爾濱已難解難分,很想對它進行一次酣暢淋漓的文學表達。完成《候鳥的勇敢》《炖馬靴》等中短篇小說後,2019年4月,我開始了《煙火漫卷》的寫作。上部與下部的标題,也是從一開始就确定了的——《誰來署名的早晨》與《誰來落幕的夜晚》。寫完上部第二章,我随中國作協代表團訪歐,雖然旅途中沒有續寫,但筆下的人物和故事,一路跟着我漂洋過海,始終在腦海沉浮升騰,曆經了另一番風雨的考驗。
我們首站去的是我2000年到訪過的挪威,因為卑爾根給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當年歸國後我還寫了個短篇《格裡格海的細雨黃昏》。而此次到卑爾根,最令我吃驚的是,這座城市少有變化,幾乎每個标志性建築物和街道,還都是我記憶中的模樣,甚至是城中心廣場的拼花地磚,一如從前。而在中國,如果你相隔近二十年再去一座城市,熟悉感會蕩然無存,它既說明了中國的飛速發展,也說明我們缺乏城市靈魂。而有老靈魂的城市,一磚一瓦、一木一石都是有情的。在卑爾根海岸,我眼前浮現的是“榆櫻院”的影子,這座小說中的院落,在現實的哈爾濱道外區不止一處,它們是中華巴洛克風格的老建築,曆經百年,其貌蒼蒼,深藏在現代高樓下,看上去破敗不堪,但每扇窗子和每道回廊,都有故事。它們不像中央大街黃金地段的各式老建築,被政府全力保護和利用起來。這種半土半洋的建築,身處百年前哈爾濱大鼠疫發生地,與這個區的新聞電影院一樣,是引車賣漿者的樂園,夜夜上演地方戲,演繹着平民的悲喜劇。從這些遺留的曆史建築上,能看到它固守傳統,又不甘于落伍的鮮明痕迹。這種藝術的掙紮,是城市的掙紮,也是生之掙紮吧。
從卑爾根我看到了“榆櫻院”這類建築褶皺深處的光華,到了塞爾維亞,我則仿佛相遇了《煙火漫卷》中那些傷痛的人——傷痛又何時分過語言和膚色呢!在塞爾維亞的幾日少見晴天,與塞爾維亞作家的兩場交流活動,也就在陰雨中進行。其中幾位前南老作家,令我肅然起敬。他們樸素得像農夫,好像每個人都剛參加完葬禮,臉上彌漫着一股說不出的哀傷。對,是哀傷不是憂傷。憂傷是黎明前的短暫黑暗,哀傷則是夕陽西下後漫長的黑暗。他們對文學的虔敬,對民族命運的憂慮,使得他們的發言惜字如金,但說出的每句話,又都帶着可貴的文學溫度,那是血淚。這是我參加的各類國際文學論壇中,唯一沒有誰用調侃和玩世不恭語氣說話、唯一沒有笑聲發出的座談。窗裡的座談氛圍與窗外的冷雨,形成一體。苦難和尊嚴,是文學的富礦和好品質,一點不假,安德裡奇的《德裡納河上的橋》誕生在這片土地,不足為奇。塞爾維亞作家腦海中抹不去對戰争廢墟的記憶,而我們也抹不掉對這片土地一堆廢墟的記憶。盡管穿城而過的多瑙河在霧雨中,不言不語地向前,但傷痛的記憶依然回流,刻在我們每個人的心上。
寫累了,我會停頓一兩天,乘公交車或是地鐵,在城區之間穿行。我起大早去觀察醫院門診挂号處排隊的人們,到淩晨的哈達果蔬批發市場去看交易情況,去夜市吃小吃,到花市看花,去舊貨市場了解哪些老器物受歡迎,到天主堂看教徒怎樣做禮拜。當然,我還去新聞電影院看二人轉,到老會堂音樂廳欣賞演出,尋味道外風味小吃。凡是我作品涉及到的地方,哪怕隻是一筆帶過,都要去觸摸一下它的門,或是感受一下它的聲音或氣息。最觸動我的,是在醫大二院地鐵站看到的情景。從那裡上來的乘客,多是看病的或是看護病患者的,他們有的提着裝有醫學影像片子的白色塑料袋,有的拎着飯盒,大都面色灰黃,無精打采。有的上了地鐵找到座位,立刻就歪頭打盹。在一個與病相關的站點,感覺是站在命運的交叉口,多少生命就此被病魔吞噬,又有多少生命經過救治重獲新生。這個站點的每一盞燈,都像神燈。能夠照耀病患者的燈,必是慈悲的。
2019年歲末,長篇初稿終于如願完成了。記得寫完最後一行字時,是午後三點多。擡眼望向窗外,天色灰蒙蒙的。我穿上羽絨服,去了小說中寫到的群力外灘公園。春夏秋季時,來這裡跑步和散步的人很多。那時隻要天氣好,我會在黃昏時去塑膠跑道,慢跑兩千米。但冬季以後,天寒地凍,灘地風大,我隻得在小區院子散步了。十二月的哈爾濱,太陽落得很早。何況天陰着,落日是沒得看了。公園不見行人,一派荒涼。候鳥遷徙了,但留鳥仍在,尋常的麻雀在光秃秃的樹間飛起落下。它們小小個頭,卻不懼風吹雪打,該有着怎樣強大的心髒啊。
我沿着外灘公園猩紅的塑膠跑道,朝陽明灘大橋方向走去。
這條由一家商業銀行鋪設的公益跑道,全長近四公裡。最初鋪設完工後,短短兩三年時間,跑道多處破損,前年不得不鏟掉重鋪。因為塑膠材料有刺鼻的氣味,所以施工那段日子,來此散步的人銳減。為了防止人們踏入未幹透的跑道,施工方用馬紮鐵和繩子将跑道區域攔起來。可是六月中旬的一個傍晚,我去散步時,在塑膠跑道發現一隻死去的燕子。燕子的嗅覺難道與人類不一樣,把刺鼻的氣味當成了芳香劑?它落入塑膠泥潭,翅膀攤開,還是飛翔的姿态,好像要在大地給自己做個美麗标本。而與它相距不遠,則是一隻凝然不動的大老鼠——沒想到灘地的老鼠如此肥碩。這家夥看來不甘心死去,劇烈掙紮過,将身下那塊塑膠,攪起大大的旋渦,像是用毛筆畫出的一個逗号,雖說它的結局是句号。而我一路走過,還看見跑道上落着煙頭、塑料袋、一次性口罩、糖紙、房屋小廣告等,當然更多是樹葉。本不是落葉時節,但那兩日風大,綠的葉子被風劫走,命差的的就落在塑膠跑道上,徹底毀了容顔。
無論死去的是燕子還是老鼠,無論它們是天上的精靈還是地上的竊賊,我為每個無辜逝去的生靈痛惜。
我們在保護人不踏入跑道時,沒有想到保護大自然中與我們同生共息的生靈,這一直是人類最大的悲哀。
如今的塑膠跑道早已修複,我迎着冷風走到記憶中燕子和老鼠葬身之地時,哪還看得到一點疤痕?它早以全新的面貌,更韌性的肌理,承載着人們的腳步。去冬雪大,跑道邊緣處有被風刮過來的雪,像是給火焰般的跑道鑲嵌的一道白流蘇。完成一部長篇,多想在冷風中看到一輪金紅的落日啊,可天空把它的果實早早收走了,留給我的是陰郁的雲。
我的長篇通常修改兩遍,年後從故鄉回到哈爾濱,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哈爾濱與大多數省會城市一樣,采取了限制出行措施。我與同事一邊和《黑龍江日報》共同策劃組織“抗疫”專号文章,一邊修改長篇。每日黃昏,站在陽台暖融融的微光中,望着空蕩蕩的街市,有一種活在虛構中的感覺。與此同時,大量讀書,網上觀影。波拉尼奧的《2666》是這期間我讀到的最複雜的一部書,小說中的每個人似乎都是現代社會“病毒”的潛在攜帶者,充滿了不安、焦慮與恐懼,波拉尼奧對人性的書寫深入骨髓。我唯一不喜歡的地方,是他把罪惡的爆發點集中在墨西哥,就像中國古典小說寫到情愛悲劇,往往離不開“後花園”一樣。如果人類存在着犯罪的淵薮,那它一定是從心靈世界開始的。
二月改過一稿,放了一個月,四月再改二稿,這部長篇如今要離開我,走向讀者了。在小說家的世界中,總是發生着一場又一場的告别,那是與筆下人物無聲的告别。在告别之際,我要衷心感謝《煙火漫卷》中的每個人物,每個生靈,是他們伴我度過又一個嚴冬。
在埋藏着父輩眼淚的城市,我發現的是一顆露珠。
小說總要結束,但現實從未有尾聲。哈爾濱這座自開埠起就體現出鮮明包容性的城市,無論是城裡人還是城外人,他們的碰撞與融合,他們在彼此尋找中所呈現的生命經緯,是文學的織錦,會吸引我與他們再續緣分。
(本文為《煙火漫卷》後記節選)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