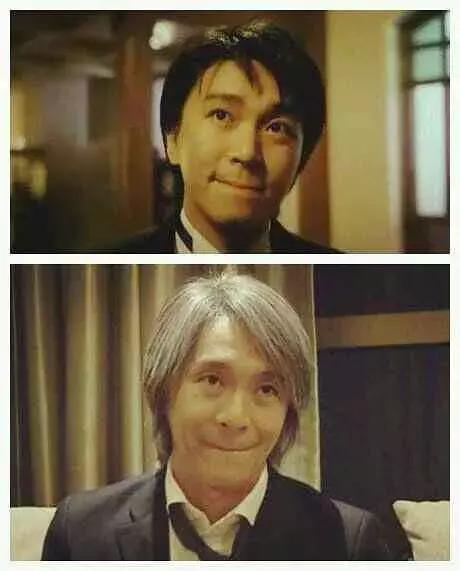說起《狂人日記》,你會想到什麼?
作為一個金句頻出的經典,什麼“趙家的狗”“從來如此,便對麼?”
從魯迅那個時代延續到現在,至今被人們所津津樂道。

我們現在的時代,距離《狂人日記》的發表,已經過了将近一個世紀的時間了。《狂人日記》在文學意義上的地位自然是不必我來贅述,作為中國的第一篇白話小說,中國文學進入現代的标志,他的頭銜太響亮;同時,創造性的現實主義與象征主義結合的藝術手法、日記體的格式、文白兼備的語言、細緻的心理描寫,凡此種種,魯迅先生都擺脫了那個時代白話文的青澀。
第一部白話文小說,就成熟的如此可怕,可怕到過了一個世紀的我們讀《狂人日記》都不覺得生澀,好像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作品似的。
但是我們這次,暫且都不關注這些。我們要知道的是,優秀小說之所以是優秀小說,采用了什麼技巧,其實是不很重要的事情。曆經了近百年的時光仍然光輝不滅,能做到的隻有,永恒的思想價值。
在讨論什麼思想之前,我們不妨來探讨探讨,在《狂人日記》裡,怎麼才算是一個“狂人”?.

開頭魯迅先生就很有意思的點出來,這是一個“迫害狂”的日記,還順便提及了那個“迫害狂”如今的境遇,“赴某地候補矣”,也就是說,“狂病”被治好了。我們不難發現,《狂人日記》中,“狂病”被治好的狀态是“候補”,通俗點來說,也就是準備當官去了。“狂人”的“病”已被治愈,“赴某地候補”,仔細一思量,真是令人不寒而栗。
反過來再想一想,“狂人”的第一個症狀,不就是像賈寶玉一樣不醉心于功名利祿嗎?

在《狂人日記》裡,狂人不止一次對“吃人”,産生了恐懼。他把為他把脈的,他的大哥,都想象成吃人者。封建道德倫理是什麼?兄友弟恭;封建裡怎麼看醫生?醫者父母心。
狂人不這麼想,他說他們都是吃人者,吃自己的肉!并且在日記裡,寫了以下這段話:
我翻開曆史一查,這曆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地每頁上都寫着“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着,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着兩個字是“吃人”。
看來要成為“狂人”,你還得不信那些封建說教,能從字中看出字來。
如果隻是這兩點,我們現在人好像确實有點優勢,但是魯迅先生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寫出了第三點,第四點。
狂人發現了“吃人”這一可怕的事實之後,他馬上想到了自己早逝的妹妹,覺得自己“吃了她的肉”,這種反省與思考,使他的人生層次,再次提升了。
接着便是憎惡自己的靈魂,自己也是“吃人的人”,然後他發出了“救救孩子”的号召。自己已然是一個“吃過人的人”了,不能讓下一輩也做“吃人者”。
當我們把狂人的幾個特質組合起來,不醉心功名,不迷信封建說教,人難得的悲憫與反省再加上對下一輩的責任感,我想,魯迅先生筆下的“狂人”,好像比那個時代的正常人更像一個人。
二:趙家的狗和古久先生的陳年流水簿子
《狂人日記》裡,提到了兩個頗有意思的意象。
趙家的狗和陳年的流水簿子。
餘華對“趙家的狗”那句話大加贊賞,說魯迅一句話就寫出了精神病人的樣子,也是,正常人,誰能注意到多看自己一眼的趙家的狗呢?
趙家的狗,這個意象,有個形容詞,“趙家的”。趙家是哪家?是趙貴翁的家。趙貴翁是誰?文中并沒有明說。
但是從我質問大哥為什麼不給租戶減租,可以大體推斷出,趙貴翁其實身份地位和我大哥,是一類人,不然又怎麼能與我大哥交流呢?
古久先生的流水簿子,是一種帶有魯迅意味的象征,代表着封建的曆史。《狂人日記》中,狂人踹了一腳,就等于狠狠打了一次封建的臉,作為古久家的不認識但休戚相關的代表人,趙貴翁自然是對于狂人,很是憤怒,但是尊貴的老爺自然是尊貴的,于是乎,狠狠瞪“狂人”的,自然隻有趙家的狗了。老爺不方便做的事,奴才當然要體察上意了,這就是狗的思維。
先生在《狂人日記》中刻畫了一個病态社會,讓我想起《走向共和》中的一句台詞,“大清國人人有病”。而在這種人人有病的環境下,誰要是沒病,誰就成了他者口中的“狂人”,“狂人”想要解救“趙家的狗”,打倒趙貴翁和無處不在的古久先生,但是可悲的是,“趙家的狗”對“狂人”警惕,對趙家熱愛。
正如《權力的遊戲》中奴隸的解放者丹妮莉絲所言,“枷鎖戴久了,也會有人愛上它”一樣,奴隸們不想解放自己,他們甯願在得過且過和烈士們的鮮血饅頭中苟且的活着。狂人們在這種境遇下,也就隻剩兩條路了,要麼“候補”,算作“治愈者”,要麼像夏瑜一樣,在牆内孤獨的死去,而牆外,總有華老栓來買他的人血饅頭。
三:“狂人”想說什麼?
“狂人”,想說什麼?
一言以蔽之,正是那句金句“從來如此,便對麼?”
“狂人”是一個迫害妄想症患者,在他的世界裡,一切都被合理的異化了,他覺得趙家的狗知道這場陰謀,疑心小孩子也被“吃人者”帶壞,懷疑大夫給他把脈是為了把他養肥了在吃,最後開始陷入了自我懷疑——他,竟是吃人者的兄弟!
如果我們從正常人的視角看,村裡的人隻不過是正常生活,大夫隻不過是想要為他醫治,他的大哥也盡到了大哥的責任,全心為他着想,他卻敏感地曲解每個人的行為、話語,并為此驚懼。
可狂人新穎的思考卻也不無道理:
“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我曉得他們的方法,直接殺了,是不肯的,而且也不敢,怕有禍崇。所以他們大家聯絡,布滿了羅網,逼我自戕”
“這時候,我又懂得一件他們的巧妙了。他們豈但不肯改,而且早已布置;預備下一個瘋子的名目罩上我。将來吃了,不但太平無事,怕還會有人見情。佃戶說的大家吃了一個惡人,正是這方法,這是他們的老譜!”
從上面我摘抄的一系列狂人的心理活動中,很明顯可以看出,魯迅先生話中有話,他需要借“狂人”的嘴,來傳遞他的思想。
我們中國人講究的所有的道德在“狂人”這裡已經完全的揭示了他的荒謬性,魯迅先生的偉大之處,就是揭示了一個人如何在都是“正常人的社會中走向死亡”。
像祥林嫂,孔乙己,還有這個“狂人”,我們不能說“狂人”的周邊人做的不對,因為他們那個時代,表達愛的方式,就是如此;我們也不能說孔乙己的消失,祥林嫂的死亡,他的周圍的人都是不正常的,魯四老爺很正常,丁舉人也很正常,正常到那個時代的人,都對他們的舉動,不會發出一點聲音。而悲劇的是,一群時代的正常人間,總是夾雜着幾個“狂人”的命。
錯的不是他們,錯的是整個時代。這是莫大的悲哀。
如今的時代,也常常見到有人感歎,說魯迅是常讀常新的,好像他寫的那些東西,在當今這時代,依然一針見血,雖然百年已逝。雖然那個封建年代已經被我們掃進了墳墓,可舊時代裡長期養成的國民性,并不會一下子就無影無蹤。那種種壓迫、強權和愚昧并沒有消亡,它們好似戴着面具的惡鬼,藏匿在每個人當中,一遇上機會便要“吃人”。而小說中那一個個極具象征意義的形象,“趙貴翁”、“趙家的狗”、“大哥”,以及“狂人”本身……很不幸的是,他們還活着,隻是戴了面具而已。
值得警惕的是,從古至今,這個社會的進步其實遠不如我們所以為的那樣大,總有人厚顔無恥的借公理正義的美名,打着正人君子的旗号,戴着儒雅的面具,以蓬勃的民意為武器,以春秋筆法含沙射影,使無刀無筆的弱者連質疑的勇氣都沒有,就被裹挾着走上一條莫名的道路。
幸運的是,魯迅先生早已經借“狂人之口”說出那句:
“從來如此,便對麼?”
文/枕貓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