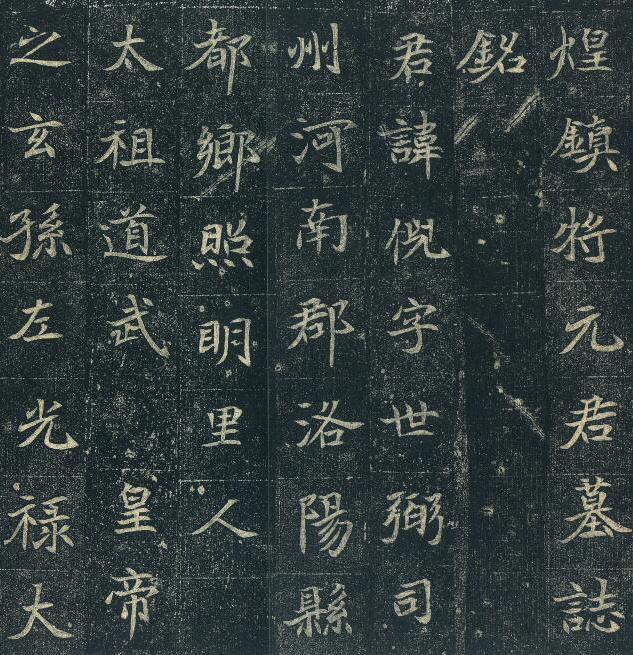既熟悉,相認又有些遲疑。
街道比我童年跑着玩時顯得寬;街上之人的衣着,也比我們小時穿得更周整。
沒有一輛汽車,自行車竟也少;遠處馱着麻袋的闆車在這座城裡行了很多年。
街面的人不慌不忙的走着,沒有革命運動的激昂或混亂之中的焦慮。
那樣的坦然、自得。
該是秋天吧,陽光清朗而妩媚,道旁樹還精神着。
路邊的孩子自由自在的玩着。
遠處幾座二三層樓,我已想不起來它們是什麼。
所有沿路的房子似乎完全沒有門面房的概念,一眼望去,未見一家商店。
日子就安靜得有些寂寞。
恍惚中,一聲似遠還近的“磨剪子來”的吆喝把我喚醒。
那聲音遠而幽,你看不見人時,聲響就從某一條側街或小巷飄過來,蚌埠腔調的平直。
那是老蚌埠的市聲。
一聲就把老日子給複原了。
老城市的老街老巷都有“市聲”。
這個“市”是市集、市井的意思。
“市聲”主要流行于遊街串巷的行商和集市攤棚中,尤以小本經營的貨郎和攤販為甚。
或肩挑推車,沿街叫賣,或就地擺攤吆喝聲聲。
我們記憶裡躲着藏着的,就是這些回蕩在街巷裡的吆喝,有扯開嗓門,努力的大喊,也有敲着個物件發聲。
有需要的人家聞聲紛紛走過來。

磨剪子戗菜刀是一門古老的行當。
多年以前,“磨剪子戗菜刀”的手藝人時常出現在市井人家的庸常生活中,京劇《紅燈記》把這形象塑造成一個特定場景中的聲音,那拖着長音的吆喝聲刻在腦子裡,經典得無法忘懷。
剪子的刃口要求是陡峭的,所以要用磨;菜刀的刃口要薄而光滑,故而要用工具鏟平削薄。
戗在這裡是镗鏟的意思,用一種鋼制的類似于木工的推子,把菜刀表面鏟平。
以前的菜刀是手工打制,表面坑坑窪窪;用刀久了,刃口斜面不平,要鏟平或磨光。
“磨剪子來戗菜刀”的吆喝非常有特點,“磨”和“戗”字上拖音,“磨剪子來”高調,到“菜刀”聲音落下來,為重複再喊蓄勢。
聽着它就有古時吟唱七言、五言的味道。
那時可以與之抗衡的就是“ba盆ba鍋”,我沒查到“ba”的寫法,用“耙”或“疤”卻又沒有這個義項。
過去人家窮,鍋漏了,盆裂個口子,得“打補丁”。
會這門手藝的師傅背個大工具包,喊起來“ba盆ba鍋”特别有味道,他是将““ba盆”分開長調,到“ba鍋”降調連音,喊起來精神,音調就能壓過“磨剪子喽”,讓後者顯得慵懶。
最難忘的是老蚌埠洋茅廁往東的澡堂子。
洗澡上來,汗未擦幹,就聽捏着嗓音喊出的蠻子腔“香幹”。那人精瘦、矮小,挎個籃子,白紗布罩着鹵好的香幹。
他的喊法也别緻,“香幹”二字前輕後重,突然煞音。
那香幹太好吃,切成細絲,裹成香腸狀,一片片的。
我是舍不得整片放嘴裡,拉着細絲,一條一條的細嚼慢咽。
滿嘴清香。

“磨剪子喽”的吆喝無關我們屁孩的事情,最讓我們着迷的是小铴鑼聲,當當當的急響,——賣糖稀的來了。
那糖稀是紅芋熬的,甜得透心透肺;加上挑擔的會停在那裡,捏小玩意,孫猴子、小鳥、小狗,幾下就在小木棍上立現,實在是可愛。
把孩娃招惹得火急火燎。
我們會跑回家纏大人,要幾分錢;有的喜滋滋跑回來,一點一點在唇上舔,叫其它小朋友慕羨。
還有的要不來錢,便鬧;一會兒你就聽大人拍打幾下,小娃哇哇的哭。
賣冰棒的來,背個正方的木頭箱子,裡面放團小棉被保溫,弄個馬蹄餅那麼大的響木,栓個繩子在手裡搖着。
那聲音密集、銳利,直抵人心。
我們一般早将零花錢準備好,去買。
最便宜的是水果冰棒,三分一棒;赤豆的四分,牛奶的要五分。
那時開始玩花樣,弄個雙色冰棒,一半白,一半紫紅,看着鮮豔,要七分;味道卻一般。
我小時最喜歡赤豆棒冰,又涼又甜,還有豆子在嘴裡化。
最頭疼的是聽到巷子裡的搖鈴聲,銅制的大鈴铛,拉垃圾的專用。
它聲音大,老遠在街上出現,巷子裡的人家都能聽見。
搖鈴響起時,恰在我們院子裡小夥伴玩遊戲最起勁,打皮卡,彈溜蛋,磕冰棒筷,全神貫注正要定輸赢。
它一響,就聽各家各戶的媽媽爸爸的吆喝:小四、老三、毛丫、小五、老妮,倒垃圾了!
你不去,叫聲絕不停歇。
我們隻好放下手裡的玩物,悻悻的散開。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