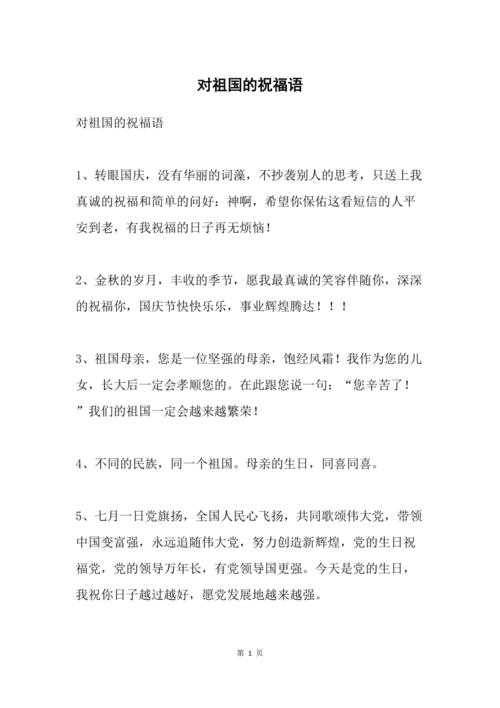少年時代在農村,我是背牛草背篼長大的,是個不折不扣的“看牛匠”!“看牛匠”每天除了放牛、牽牛吃水,更多時間就是割牛草。記得好像是五歲多點,母親就找人用慈竹篾條幫我編了一個牛眼膽背篼,就是很小比喻像牛眼睛那麼大點,實際比牛腦殼還大,我背起正合适。那可不是幫我做的玩具,每天都要背起它、拿起一把小鐮刀,跟到姐姐些遍山割牛草。剛開始邊玩邊割半天割不滿,姐姐們就從她們的大稀眼背篼裡抓幾把給我裝好,裝滿一牛眼膽背篼嗨啧嗨啧背回去,老娘娘就會獎勵我一顆貓屎糖!

七、八歲以後,牛草背篼也就逐漸從小稀眼背篼換成了和姐姐們一樣的大稀眼背篼。割草也就從玩變成正兒八經幹活路!那時喂的牛是用來耕田的水牛,都屬于生産隊,哪家有能割牛草的娃兒就去認養一頭,生産隊負責一天兩三分記工分,大牛記3分,小牛記2分。一年下來也能掙個七、八百分工分,也算是為家裡做了很大的貢獻。
每天放學回家,我的任務就是至少得割滿滿一背牛草,也就夠小牛吃一天了。牛兒長成大牛一頓就要吃一背,一天三頓就是三背,就得發動幾姊妹一起割才夠。下午一兩點鐘放學回家,吃了午飯就背起背篼出門割草。夏秋兩季好割草,河邊竹林頭、田邊地坎、山林邊上到處都是絲茅草、馬胡草、馬鞭梢、馬兒花,一哈兒就是一大背。遇到冬程天就惱火了,天寒地凍、草木不生,背起牛草背篼跑遍大半個生産隊,都難得割滿一背。那季節,我們幾姊妹也有辦法,先是勻到安排割自留山上幾坡平時留起來未割、長得整齊茂密的“護草”(專門留起來過冬的牛草),自己家的“護草”割完了,偶爾也曾經打過别人家“護草”的主意,被别人攆得牛草背篼都追落了!還有就是到河邊上竹林頭扳硬頭黃竹葉子喂牛,實在不行了還可以用豬圈樓樓兒上一樓的幹谷草給牛充饑,反正不能讓它餓到。一到臘月二十幾頭,我們幾姊妹就要加班加點每天多割幾背篼草來存起來,過年開頭那幾天好丢下工程(不做活路)走人戶随便耍都有草喂牛,我們稱之為過年草!
那是,家家戶戶娃兒些大多數都在喂牛,割草也就十分困難,隊裡小夥伴平時都在為牛兒的口糧發愁。于是一種割草賭博的遊戲應運而生。我們老家娃兒些喊這種遊戲叫打叉兒,也就是通過打叉兒賭草。在參與賭草的娃兒些都割了大半背草的時候,找一個地勢相對平坦點的壩壩,豎起三根竹棍子搭成一個三角架叉叉,在離叉叉四五米的地上刮出一道橫線,參與賭草的小夥伴每人抓出一把草放到旁邊作為賭注,然後劃錘包剪(就是現在的剪刀石頭布)決定順序,依次投擲鐮刀擊打叉叉,誰先打到叉叉就算赢,大家抓出的牛草就歸誰。我們男生一般赢多輸少,姐姐們割了半天都是在幫我們打工。我們一哈兒就赢了滿滿一背判起尖尖,歡天喜地下河洗澡摸魚去了。姐姐們和鄰居家的女娃兒些隻好垂頭喪氣埋怨自己運氣太差,背起空背篼繼續找新的地方割草去了。其實她們哪裡曉得,我們男娃兒些平時經常拿彈槍(彈弓)打雀子、錠(抛)石頭打青果老木柑,早就練就了一身十分了得的投擲技術,女娃兒些玩打叉兒哪是我們的對手!

割牛草最怕割到手,鐮刀每天使用前都要在磨刀石、水缸邊子上磨得飛快,遇到幾個人搶割一片長得好的牛草,稍不注意就要割到手。有次在龜歇凼門口的沖口大田坎上,我和張二娃他們兩姊妹搶割一片茂盛的油草,我割得又急又快,一不小心鐮刀谝pian到左手中指上,一時間中指第一個關節皮筋割開一條大口子,鮮血直流。我媽呀一聲大哭起來,捏住傷口跑去找大人。幸好母親他們就在近處出工,拉起我就往燈杆灣跑,沿路滴了一路的血!因為燈杆灣牟二孃家最近,又曉得備有消炎粉。到了那裡急忙抖了半包在傷口上,要了一塊布角子(打衣服剩下的邊角餘料)包好纏緊就了事,害得我十多天無法割草。由于韌帶割斷沒有縫針,以緻這根中指一直打不伸,後來讀師範要自願選修音樂或美術,本來想學音樂,結果手指往風琴琴鍵上一放,音樂老師馬上說你無法彈琴學美術吧!

喂牛是一個系統工程。每天天一亮就要牽牛吃水,就是把牛牽到河邊喝水、窩屎窩屎。夏天就直接把牛栓在牛滾凼頭,或者栓到河溝裡,傍晚再牽回牛欄屋。打掃牛欄也很煩,要把牛屎鏟好挑出來晾曬堆到,第二年開春用來并紅苕種(種紅苕苗子)。這還不要緊,那時我最怕的是換牛鼻索(用于穿過牛鼻孔牽牛的竹篾條編制的索子)。一般都是在牛鼻索用久了磨斷了,牛兒脫離約束打脫了才換一根新的。這情況得膽大心細,用牛草逗牛兒停下來,趁它不注意一把摳住它的鼻孔,把牛鼻索一頭穿過去再打一個結栓好才要得。如果是在牛欄外面田頭路上打脫,穿牛鼻索就更加困難了!必須要一個與這牛兒親近的人拿着牛鼻索慢慢噴攏去豁到才能完成。遇到要打人的牯牛又高又大,我們娃兒些是不敢靠近的!據說就有農人被惹毛發瘋的大水牛用鋒利的牛角活活挑死過。
從小到大在農村甚至離開農村參加工作之後,隻要回家一天到晚都要和牛打交道,自然就對家裡的水牛産生了特殊的感情。有次生産隊要賣掉我們家認養的一頭半大牛兒,那天隊長帶着牛牙子(做牛買賣生意的中間人,促成交易成功買牛人就會支付傭金給牛牙子)和買牛的來到我們家,起初我還不曉得他們是來幹啥子,還幫到大人端茶遞水擡闆凳。母親帶他們進牛欄看過牛兒出來,牛牙子把隊長和買牛人一手牽一個拉到一邊,撈起身上的圍腰帕蓋住兩人的手,開始神神秘秘、搖頭擺腦不說話,牛牙子的圍腰帕下面像在耍魔術一般不停地抖動。我們幾姊妹圍在旁邊一臉懵逼不曉得他們在搞啥子鬼名堂!事後母親才告訴我們,他們這是在講價錢,喊價還價全部用手指頭在圍腰帕下面互相比劃,免得旁邊的人殺價搶生意。我聽了感覺搞笑,我們又不買牛,鬼才搶你的生意,大敞明亮直接講價不就完了嗎?!後來長大了才曉得這是牛市上的行規。等隊長和買牛人都用力點了點頭,牛牙子這才大笑道:“成了!付錢付錢!”買牛人馬上摸出荷包開始付錢,我們才煥然大悟原來是要買走我們喂的牛!我哪舍得這麼乖的牛兒被人牽走?!頓時難受得大哭起來,又跳又鬧不準他們牽走。母親悄悄勸我:拿鐮刀割牛鼻索!我聽了趕緊沖進屋在刀别子上取下一把鐮刀,跑過去就準備割斷買主已經牽出敞壩的牛鼻索,沒有想到買主把牛鼻索交給牛牙子,笑着走過來拍拍我的肩膀:“小夥子喂牛喂得設力(辛苦的意思)!來!該禮節禮節!”說着居然遞過來一張新嶄嶄的一元票子!我吃驚地用詢問的目光望向母親,母親微笑着點頭說:“拿到嘛,買主弄大的禮節呃!”心裡再舍不得牛兒都不會給這麼大一筆“巨款”過不去撒(要知道老爸三十晚些發給我的壓歲錢都才隻有兩角錢啊),隻得抖抖地借過錢眼睜睜看着一群人有說有笑牽着我們的牛兒爬上了對門的山路……後來才曉得,買牛人要給“看牛匠”牛鼻索錢也是牛市行規!
其實我知道,在小時候那個農耕時代,耕牛就是農人的命根子!如果沒有耕牛,莊稼特别是水稻種植就無法順利開展,人們千百年來賴以生存的白米飯将無處可尋!因此,舊時農村敬牛如敬神,耕牛累死老死也不忍食用,在早都要慎重其事厚葬的。就是過去生活困難時期,耕牛老得不能犁田了,也是忍痛悄悄賣到遠處,眼不見則心安,所以許多老輩人是終身不吃牛肉的!在我老家農村對牛的膜拜甚至演化為一種祭拜儀式,小時候許多地方都還遺存着牛王廟遺址或地名,我們老娘娘在世的時候,說每年十月初一是牛王菩薩生,還要刀頭敬酒備起到牛欄頭祭拜一番,那天全體耕牛都要歇一天不幹活,也要喂最好的牛草。
我曉得的對牛最有尊崇意味的是農村過年一直保留着一種與耕牛相關的民俗表演,那就是牛牛燈!那時,每年正月初十一過,每個公社都有一兩拔牛牛燈在鄉壩頭挨門挨戶耍!牛牛燈隊伍才攏對門坡上,歡快的鑼鼓聲就老遠響起來了。到了敞壩頭,領隊的燈頭提着馬燈開唱:“牛牛燈耍得圓,牽起牛兒來拜年……”四言八句順口溜祝福語一套是一套!母親趕忙遞上至少一個月月紅一元二角錢紅包禮信,表演完把大家耍高興了一般還要“沖水”(發第二次紅包)。随後耍燈主角正式亮相:一人扮演“看牛匠”,身上背着裝了一把牛草的稀眼背篼,一手一根牛鞭杆,一手牽起一條由兩人身披草席或被單裝成的耕牛,伴着銅鑼、镲钹、壇鼓合奏的特殊音樂,歡騰跳躍表演牛犁田、吃草、打滾、刨虱子、洗水凼、放牛娃騎牛等動作,惹得我們全家和沿路攆來圍觀的鄰居們哈哈大笑。一時間,歡快的鑼鼓聲、喜慶的鞭炮聲伴随農人開懷的暢笑聲傳遍山村的山巒河谷……
後來,田土下放,耕牛更是每家每戶少不了,農村養牛迎來高峰期,也催生了耕牛繁殖、飼養、醫療等系列産業的興旺發達。我們家三姐夫就看準耕牛市場開發了一個牛産業起始端項目:養了一頭有大又壯的公牛,專門等待養母牛的農戶牽牛上門配種!那時城鄉正在風行娛樂城,三姐夫的朋友們便戲稱他開辦了一個“牛樂城”,幾年下來确實找了不少錢。再後來,農村城鎮化進程加快,農村種田人大都離鄉背井打工掙錢去了,田土大量荒廢,加之機耕普及,耕牛就失去了存在價值,我從事過的“看牛匠”這個職業也就永遠退出曆史舞台,載入中國農耕文化的史冊!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