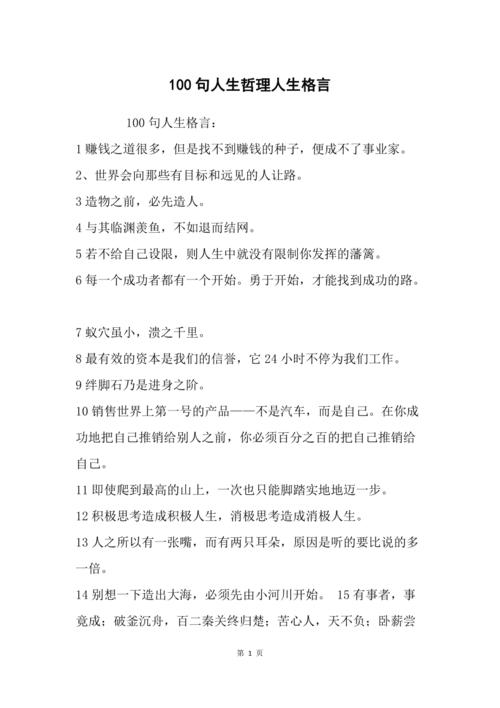過了正月,青青麥田,點點都是挑草的人。坐着小闆凳,彎着腰,在自家地裡埋頭挑草。陽光明媚,春日遲遲,原野遼闊而靜寂,聽得見麥地清涼的呼吸。
挑草是愉快的事,也是辛苦的勞役。整個二三月,女人們天天忙着挑草。挑完一茬,又長出一茬。直到麥苗吐穗,還得再去拔草,草總是比苗長得更快,更旺盛。今年拔幹淨了,明年又會長出來。
草,是除不完的。為了一口糧食,人不得不常年和草做對。
唐代詩人白居易寫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是事實,也是隐喻。隐喻什麼呢?
我們來讀幾首詠春草的詩詞,看看在詩歌的國度,現實與隐喻如何統一,不可見的現實如何被語言發現并喚醒。
撰文丨三書
01
離離原上草
/ /
《賦得古原草送别》
(唐)白居易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别情。
/ /
先談談詩題。“賦得”指借前人的詩句或成語,在習作、聚會或科舉考試時,命題作詩的一種方式。《賦得古原草送别》,就是白居易少年時準備應試的習帖詩。按照當時科考的規則,凡是限定的詩題,題目前必須加上“賦得”二字,作法類似詠物詩。這首詩的真正題目是“古原草送别”。
白居易應舉初至京城,以此詩谒見時任著作郎的顧況。顧況看罷姓名,端詳了他一會兒,說:“米價方貴,居亦弗易”,遂即披卷,閱至一半,乃嗟賞稱歎,能寫出這樣的詩句,生活也就容易了。顧況于是為其延譽,白居易自此聲名大振。
命題作詩或作文,很難出佳作,這首雖是賦得體,但造語真率,意境天成,一經詠出,即為絕唱。“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開頭兩句,似脫口而出,妙手偶得。原上,可以是樂遊原,也可以泛指原野。一歲一枯榮,兩個“一”字,疊出自然節奏,形成詠歎的效果,及生生不已的情味。這是春草,如果颠倒詞序,變成“一歲一榮枯”,那就是秋草了。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今人引用這兩句詩,多取其隐喻義。隐喻什麼,因人而異,例如《唐詩三百首》的編者蘅塘退士旁批此詩曰:“詩以喻小人也。消除不盡,得時即生,幹犯正路,文飾鄙陋,卻最易感人。”後世多取此喻。樂天作詩,是否真有此意,不得而知。吾等解詩,亦可見仁見智,或以喻世道循環,治亂往複,或以喻天心貞元,生生不息,皆無不可。
野火與春風,意象振奮,讀之倍覺精神。唐人也有類似詩句,比如劉長卿的“春入燒痕青”,孟浩然的“林花掃更落,徑草踏還生”,詩意相類,氣象皆不如樂天的廣大寬馀。
上半詠古原草,下半詠送别,關合全篇。“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兩句遣詞工緻,遠芳遞春草之香,晴翠狀春草之色,動詞“侵”、“接”,尤善體物傳神。古道、荒城,又将春草綿綿鋪展到遠方,不僅空間上的遠方,還有時間上的過去和未來。
“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别情”,最後點明送别之意,此乃詠物詩慣用的寫法。古人詠草,多寫别情,幾乎都用《楚辭·招隐士》之意,“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不過後來的“王孫”,不必特指貴遊子弟,可以泛指宦遊的朋友。
以上是此詩的完整版。現今有些選本不知何故,僅截取前四句,詩題也簡化為“草”。“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倒也是一首天然的絕句。

《湖天春色圖》
02
闌幹十二獨憑春
/ /
《少年遊》
(北宋)歐陽修
闌幹十二獨憑春,晴碧遠連雲。
千裡萬裡,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
謝家池上,江淹浦畔,吟魄與離魂。
那堪疏雨滴黃昏,更特地、憶王孫。
/ /
闌幹十二獨憑春,這些漢字放在一起,自有一種古典美。我們為什麼要讀古詩詞?今人的生活方式與情感體驗,與古人已太多迥異,這些詩詞并不能幫助我們更好地探索世界或認識自己。對于我,讀古詩詞,不是為了認知,也不是為了獲得什麼啟示,而僅僅是為了美,漢語原本的美,古人靈魂栖居的美。不可能回到古代,也不必回到古代,但我們可以通過文本,去體驗語言中的詩意栖居,而這,或許能給我們的生活,帶來某種清新的啟迪。
“少年遊”,始見于晏殊的詞句“長似少年時”,因取以為詞牌名。歐陽修此詞,與白居易的詩,皆詠春草賦離情,氣質美感卻完全不同。詞别是一家,誠然。
漢語是表意文字,我們讀古詩詞,即能很好地體會這一點。“闌幹十二獨憑春”,這個句子沒有主語,憑闌幹,詞序卻是闌幹在先,而且說的是“憑春”。如果翻譯成現代漢語,比如“春天時,她獨自倚着曲折的闌幹(遠眺)”,詩意已喪失大半,而且“憑春”的春,在詩句中不隻是個時間狀語。可見一斑,詩的确是用詞語寫出來的,而不在于表達了什麼意思。用什麼詞,詞的位置,詞與詞的關系、距離以及顧盼,會帶給我們不同的美感,甚至不同的詩。
“晴碧遠連雲”,措辭也同樣美幻,晴空下的碧草,以“晴碧”二字寫出,“遠連雲”,既實又虛,不是有人說過上帝是個畫家嗎?草色芊綿,宛如他在大地的調色闆上,碧色一抹到天際。
我最愛接下來的兩句,“千裡萬裡,二月三月”,字句看似平淡,卻真是尋味不盡。越樸拙的字句,越出之不易。寫春草的句子,還有比這更好的嗎?沒有一個“草”字,全篇都沒有,草卻滿春天、遍天涯。
“行色苦愁人”,春草彌漫之愁,今人大概不會有,但也會傷行色。古人送别多在春天,故有此心情。我們送别多在機場、車站,背景的春草,換作空間的喧嚣,行色同樣愁人。
過拍連用兩個典故。“謝家池上”指謝靈運,他曾苦吟出名句:“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江淹浦畔”出自南朝江淹的《别賦》:“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後世以南浦代送别之處。此二句,一吟魄,一離魂。
“那堪疏雨滴黃昏,更特地、憶王孫”,末二句可看作首二句的續寫,亦可作為獨立意象,與前面的諸多意象并詠春草。憶王孫,在疏雨滴黃昏之後,結句清勁,筆力橫亘。

《江村草閣圖》
03
萋萋無數,南北東西路
/ /
《點绛唇》
(北宋)林逋
金谷年年,亂生春色誰為主?
餘花落處,滿地和煙雨。
又是離歌,一阕長亭暮。
王孫去,萋萋無數,南北東西路。
/ /
唐代杜牧的《金谷園》,我們都能背誦:“繁華事散逐香塵,流水無情草自春。日暮東風怨啼鳥,落花猶似墜樓人。”這首詩是杜牧途經西晉富豪石崇的金谷園遺址時,傷春感昔的憑吊之作。若問他憑吊的是什麼,石崇,綠珠,世事無常,人世滄桑?或許兼有。大自然并不在意人世的悲歡離合,流水無情,草木自春,也幸好是這樣。
和靖詞的開始,用金谷園典故,詞意比杜牧有所拓展,“金谷年年,亂生春色誰為主?”從西晉到北宋,無數朝代隕滅,近千年過去,金谷年年,春天照樣來,春草按時生。“亂”字頗主觀,是詞人的視角,“誰為主?”是他的發問。春為誰來,草為誰生?顯然不是為石崇,也許是為綠珠,為後來人。
“餘花落處,滿地和煙雨”,不是寫落花,寫的是草。荒園煙雨,落花依草,草亦凄涼苦楚。與歐詞一樣,這首詞也是通篇不着一個“草”字。宋代沈義父在《樂府指迷》中有過精辟論述,他說:“詠物詞,最忌說出題字。”此論幾成評判詠物詞優劣的首要标準。
林逋生性恬淡,不慕榮利,早年漫遊江淮,四十歲後隐居孤山,梅妻鶴子,常駕小舟遍遊西湖諸寺,與高僧詩友相往還。此詞借金谷園詠春草,“亂生春色誰為主”,也是悟道之語。後來宋代詞人張先在《過和靖隐居》詩中,悼林逋曰:“湖山隐後家空在,煙雨詞亡草自青。”煙雨詞,就是指這首春草詞。
下片寫别情。今人或不覺得離愁和春草有何關系,在古人這卻是很自然的事。春草方生,長亭相送,酒罷歌馀,天色将暮,王孫一去,南北東西路。“萋萋無數”,即離愁的具象化,離愁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芳草離情,從《楚辭》起,經過千餘年的體驗與書寫,早就成為一種民族心理,看到春草便觸動離愁。
近代王國維先生在《人間詞話》中,引述曆代評價稱,和靖《點绛唇》、聖俞《蘇幕遮》、永叔《少年遊》三阕為詠春草絕調,而馮延巳的“細雨濕流光”五個字,已攝春草之魂。
春草是什麼?對于我們,春草就是春草。對于古人,春草除了是春草,還是離愁,是思念,也是流光。
作者丨三書
編輯丨張進 重明
校對丨郭利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