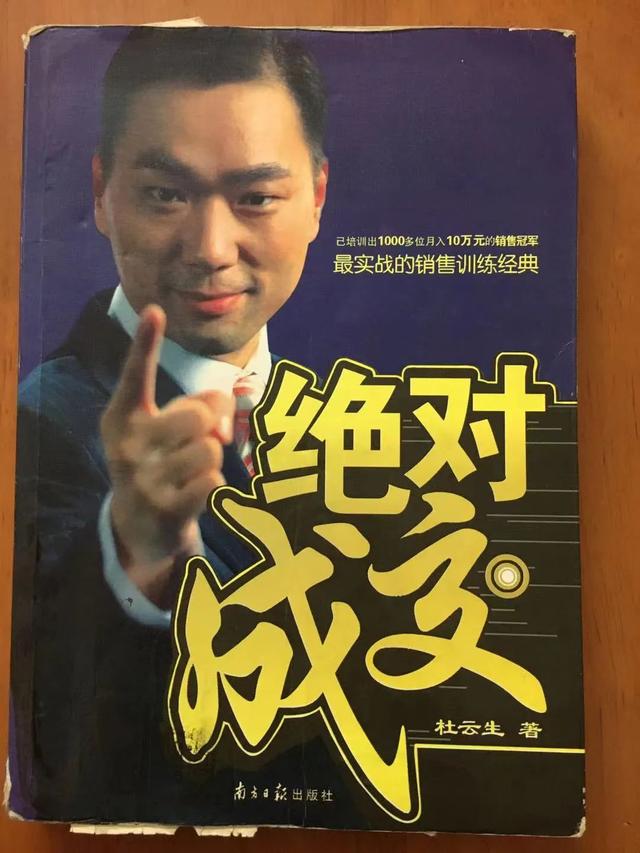資料圖
摘要:你會怎樣承受失去獨子的痛苦,而且十七年後,他的遺體才得以火化?當你的伴侶也逝去後,你又如何獨自面對這一切?如果你遭遇胡月琴的經曆,你或許也會相信,人生就是一束永遠穿梭在黑暗中的時間。
文|周航 編輯|王珊
新房子
這間不到五十平米的兩居室已經不成樣子,鐵質窗戶塞滿棉條擋風,衛生間瓷磚掉了兩塊,其餘靠膠帶固定。胡月琴真擔心自己有一天要是倒下,保姆都不願意來這樣的房子照料。
胡月琴是獨居在這不成樣房子裡的女人,你也可以說,是這個房間裡最後的戰士。她67歲了,笑起來會露出上排牙齒,但她很少笑。為了保持健康,每天清晨7點出門,散一小時步,正好符合健康專家說的,“日行六千步,勝過人參補”。
深秋的上海透着涼意,她戴了頂棒球帽,以免腦血管受寒。一路上,法國梧桐樹不停飄落橘子般顔色的皺葉,踩上去聲響清脆。用不了一個月,所有葉子都會掉完,到時候她會換上棉帽,捱過又一個冬天。
她不能倒下,否則沒人料理兒子的後事。自從四年前丈夫去世,她就成了孤獨的一個。散步都找不到同伴,朋友們都老了,要麼筋骨欠佳,下樓都難,身體好的也沒時間,都在家帶第三代。
隻有她還在忙過去的事。
她的獨子李奇樂,遺體一直冷凍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冰櫃,頭朝外,身子朝内,永遠留在了20歲。胡月琴感謝殡儀館,保管兒子17年多,但恨醫院,相信是對方“醫死”兒子,而且一直不提供死亡證明,讓她沒法火化、安葬他。
她要戰鬥到底。這段時間,她計劃聘請律師打官司,向醫院讨要冷凍費,哪怕為此用盡積蓄,甚至賣房也在所不惜。“人活着不就為了一口氣嗎?”她說。
位于上海東北角的這套房子是她最值錢的财産,也是僅有的栖身之地。擔心自己随時可能會倒下,今年夏天,她找來裝修隊将房子整饬一新。
很多東西一直留到現在,這回終于扔了。兒子玩具裝了兩個馬甲袋,包括兩三歲時買的一組六個變形金剛,當時花了120塊,頂好幾個月工資。小人書也有兩袋,不少是舅舅舅媽送給侄子的禮物。他上學騎的山地車,她自己扛下了四層樓。還有一大堆關于胰腺的醫書,兒子死後,丈夫買來研究,經常看到淩晨一兩點。
兒子的出生證,疫苗證,學生證,好幾張獎狀,舍不得扔,父子倆經常穿的衣服,也都留了下來。最後一共8個大紙箱,存進倉儲公司。
難過在所難免,但也談不上多難過,就像隔着月球感受陽光那樣,十七年時間已經沖淡了很多情感。
裝修後,這間屋子簡潔、幹淨,甚至有點太幹淨了,家具一片純白,看起來像沒住人一樣。她不開火,客廳和廚房沒裝隔斷,油煙機從沒打開過。所有東西都收拾得齊整,裝水果的塑料袋都攤平後疊成小塊,當垃圾袋用。袋子越積越多,一個人住實在沒多少垃圾,經常幾天才扔一袋。家裡沒有熱水瓶,一個人喝,保溫杯就足夠了。
“侬現在佬雷瑟個(很行的)。”老同事上門看到新屋,誇她能幹。她笑着回答,都是被逼的,“事體到侬頭上,侬阿雷瑟個(你也行的)。”
家具家電都是她自己去挑的,她還會網購呢,經驗豐富,比如一個專門擰罐頭的塑料器具,還有客廳裡的純木高腳凳。
她不會做飯,丈夫去世後,全靠一口電飯鍋解決三餐,早上煮湯、中午炖肉、晚上煮粥,天天如此。
很多老物件還在用。兒子喝奶粉的長柄勺,現在用來舀米。客廳裡一把母親用過的老式躺椅,布網壞了,她換成竹片繼續用,每天散步回來,便不再外出,坐在上面看書,從圖書館借的網絡言情小說,年輕女孩喜歡的那種甜寵文。這個時候,她可以藏起那顆破碎的心,短暫地忘記當年的事。
17年過去,當年的一切已經成為了故事。這個故事她回憶過無數次,做過詳細記錄,也對很多人講過,公安的,法院的,還有街道來調解的。如果需要,她可以對你條理清楚地講上幾個小時。

胡月琴在看電視,她每天都會看本地新聞。周航/攝
奇奇
故事總是從李奇樂肚子痛開始說起。那是2003年4月3日,星期天,他們帶兒子去了新華醫院。診斷結果是急性胰腺炎。兩天後,開了第一刀。接着是第2次、第3次、第4次手術。
那段時間,胡月琴和丈夫各拎一把躺椅,住進過道,日夜守着重症監護室。門上有扇小窗,但遮住了,看不見裡面。怎麼能睡着,心髒像有雙手緊緊攥着一樣痛,大腦像有一整支球隊在打架,實在困了,就迷迷糊糊躺一會兒。
李奇樂,寓意“少有的快樂”。他繼承了胡月琴飽滿的額頭,父親狹長的臉型,眼睛像兩人綜合體,眉宇間頗有幾分英氣。和父母一樣,個子不高,一直坐第一排。
這是他們的愛子,一生中最寶貴的成就。直到今天,胡月琴的微信名叫“珠媽”,原來是“豬媽”,兒子和丈夫都屬豬,大家都說不雅才改了這個名。
印象中隻打過一次,六七歲時,他扒着她托人從外地買的24寸女士自行車,在小區裡騎,搞丢了車鎖鑰匙,丈夫很生氣,象征性地拍了他後腦勺,陪着一路去尋,也沒找回來。
奇奇,家裡人都這麼稱呼他。奇奇喜歡小動物,養過蠶寶寶、巴西龜,有一次還捧回隻小貓,不敢告訴爸爸,偷偷和她說,“很可憐的”。也和她一樣喜歡看書,生日禮物就是讓他自己去買書,有一系列福爾摩斯,還有衛斯理的小說,胡月琴也看過,還記得裡面的人物流淌着藍色的血。
李奇樂和誰都能熟絡起來。有時看到門口曬太陽的老人,直接就坐在一塊聊上了。有的鄰居搬走很久以後,在馬路上看到,胡月琴還沒開口,他就先打了招呼,“阿姨好”。他知道媽媽愛看言情小說,還找同學借瓊瑤的書拿給她看。身邊的人都說,兒子這麼活絡,以後一定有出息。
胡月琴想一直留兒子在身邊。李奇樂大學念的是法律。每天吃好早飯,他就騎上那輛山地車,去小區對面的同濟校園上課。周末有空,一家三口會騎車一塊去逛公園,他們總是一起出行,兒子騎在前面,夫妻倆跟在後面。
突然之間,這像混凝土砌塊牆一樣樸素而堅實的生活就崩塌了,起因僅僅是“肚子疼”。

李奇樂的學生證。
醫療單子一張張送到手裡。他們取出全部兩萬積蓄,賣掉郊區一個小房子,幾年前6萬多買的,換了十萬塊,很快就用完了。丈夫的哥哥姐姐拿來幾萬塊錢,學校、同事和鄰居捐助一部分,其餘都是胡月琴借的。她也借不到那麼多,印刷廠的領導幫忙從外面借。
53天後,一切結束了。5月25日下午2點多,醫生說,孩子快不行了,進去見最後一面吧。她和丈夫進了病房,孩子光着身,插滿管子,她緊緊握着他的手,眼淚默默留了下來。
走出病房,剛過去兩分鐘,醫生拿來心電圖,一條直線,正式宣告了李奇樂的死亡。他們再次走進病房,給兒子擦身,看到背後、臀部,全是壓瘡,一邊擦一邊流淚,穿好衣服,推進停屍房。
回到家,打電話通知完親戚,夫妻倆就癱倒在床上。沒力氣動了。幾個哥哥嫂嫂主動承擔起後續,胡月琴說,他們去醫院拿死亡證明,但被拒絕了,對方要求結清醫療費才能給,幾次去都是這個結果,當時他們已經花去40餘萬,實在拿不出更多錢。
隻能先保存好遺體。李奇樂去世第二天,便被送到市區的寶興殡儀館,聽家裡人說,那裡會用福爾馬林浸泡遺體,不如寶山殡儀館冷凍條件好,他們就辦了轉存。
第三天中午,夫妻倆到寶興殡儀館,一起護送孩子過去。在外面,胡月琴還沒哭,但上了車,拉開屍袋,就忍不住掉淚了。她看到兒子的面容開始變得軟綿,像是要融化。不能多看,拉好袋子保溫,身子朝内,頭朝外,推進寶山殡儀館12号冷凍櫃。
那是她最後一次見到孩子。

胡月琴的客廳桌子,上面壓着有關兒子治療時的回憶。周航/攝
徒勞的旅行
胡月琴很安靜,從不嚎啕大哭,隻是默默流淚。失去孩子那年她50歲,丈夫56歲,眼淚在當時就流光了。如今最悲傷的時刻,回憶孩子的點滴時,她隻是濕潤了眼眶,仰在躺椅上,瞳孔蓦得放大,出神地望向空中。
一直以來,他們都在試圖追究醫療事故的責任,相信是醫生拿兒子做了試驗。刑警找上了門,說證據不足,勸他們改走民事訴訟,他們——主要是她倔強的丈夫一口拒絕。
兒子死去幾個月後,胡月琴才從法院的傳票上知道欠費的具體數字,124925.37元。他們是被告,醫院起訴了他們欠費。她相信這次起訴是一場報複,報複他們試圖認定醫療過錯。
沒人能接受孩子突然的離世。丈夫買來一本本關于胰腺的醫書和法律的書,每天在那裡看。原本定期會有家庭聚餐,胡月琴也不去了,實在見不得溫馨的家庭場景。以前每年學校有幾場重要考試,領導會安排她監考,賺筆勞務費用,也拒絕了,看到那些年輕的學生會讓她想起愛子。外面的熱鬧與他們無關,每年過年,關好窗戶,夫妻倆就躺在床上看春晚度過。
但她還要繼續在同濟印刷廠做會計工作。早在1990年,丈夫就因支氣管炎辦了病退,1994年起就沒有收入,從此家裡隻有她掙錢。同事都看到了她的憔悴,白頭發從裡到外冒了出來,瘦削得不成樣子。在醫院的53天,她從110斤瘦到了92斤。兒子出事時,她50歲,剛要退休,又返聘回崗,同時兼外面兩份會計工作,用了幾年時間還清外債,之後便和丈夫一樣,全心投入給兒子“讨一個公道”。
兒子剛走的一兩年,清明,重陽,夫妻倆會去殡儀館悼念,進冷藏室,見不到孩子,但能看到小黑闆上12号還寫着兒子的名字。後來冷藏室因為管理原因不讓進後,也就沒去了。
每年5月25日都是一個難關。夫妻倆會提起,兒子已經走了多少年。剛開始的幾年,一提就争吵,丈夫怪她同意開刀,她則埋冤丈夫堅持要刑事立案,一直拿不到死亡證明,送不走孩子。再之後也就不争吵了,隻是商量着怎麼上訴。
以前,胡月琴就和丈夫吵不起來,周邊住的都是熟人,不好意思吵。丈夫脾氣不好,生氣了就擡高聲音,她最多就是賭氣不說話,那時還有兒子兩邊拉扯,讓他們重新講到一塊。丈夫身體出狀況後,兒子又不在了,她就變得更沉默,總會讓着對方。
唯一手段是寫信告狀,公安部,教育部(醫院系大學附屬),甚至最高法,都寄去了訴狀。和家裡其他事一樣,這件事也由丈夫拿主意,她充當助手,用筆記下他的口述,轉至電腦,打印。最早兩毛錢一張,逐漸漲到現在五毛錢一張。
訴狀基本都被駁回了。5年前,丈夫提出最後一搏,到紐約找聯合國,找律師。胡月琴少見地提出了異議,覺得太不靠譜了,但丈夫急了,“兒子的事你就不管了是麼,總歸要試試看”,她聽了也覺得有道理,試了也就沒有遺憾,對得起兒子了。
這麼多年,很多鄰居同事會勸他們放下,一切随着時間會好起來的。但她怎麼聽得進去,勸别人她也會,“但事情真的到自己頭上,沒人放得下的。”而且時間隻是讓人變得麻木,隻要想起兒子,心依舊就會鑽心的痛。隻有最親近的哥哥嫂嫂們不會說這樣的話,他們隻會說保重身體,才能更好“讨公道”。
于是,這對年過花甲的老人踏上了漫長的旅途,那是他們第一次坐飛機,全靠着一張寫滿“華人區”、“旅館”、“廁所”、“飯館”這些關鍵字和對應英文的A4紙,在皇後區華人街找到了落腳點。合租的都是打工者,有人問起,他們隻是說自己來旅遊,這悲傷的故事實在難以向不相關的人說出口。
這注定是場徒勞的行程。一年後,胡月琴獨自飛回了上海,淩晨三點的浦東機場,燈光很亮,她背着兩個包,前後各一個,兩手各拉一個行李箱,走出通道,發現侄女在等她。侄女問,姑父呢。她說姑父已經走了,骨灰盒就在包裡。
回國不久前,在幾戶人家合租的房間裡,丈夫做完飯,說自己有些累了,沒吃就在床上歇了,然後就沒了動靜。他一直有高血壓、心髒病,就這樣安靜地離開了人世。在華人街殡儀館,他的遺體連帶棺椁,一同被火焰吞噬、燃盡。
說着說着,胡月琴就哭了,侄女也哭。第二天一早,二嫂來了,她早就看出不對勁,以前問她消息,總是說“我們很好”,後來成了“我很好”,但又不敢問。
直到今天,丈夫的骨灰盒依舊放在家裡,沒有安葬。兩個人生前有約定,無論誰先走,都要帶孩子一塊走(合葬)。她包上紅絨布,放在從前兒子的房間的櫃子上。上面還擺放了丈夫和兒子的單人照,還有兩張一家三口的合照。其中一張還是電腦合成的,2003年初侄子婚禮上,他們與新郎新娘分别合的影。

新華醫院曾作出的回複。
奇迹
丈夫的離世讓胡月琴一下子沒了主意,一年後,丈夫曾經做法律顧問的哥哥也走了,兒子的事一直是三個人在跑,現在隻剩她,連個商量的人也沒有。
她不再執着追求醫療事故的責任。她也老了,體檢報告裡問題一頁紙都列不完,牙齒下排兩邊都裝了牙套,左邊五顆,右邊三顆。牙齒就是從兒子生病那時開始疼的。她不再那麼信任現代醫學,降壓藥都不怎麼吃,每天隻吃半粒降脂的他汀類藥片,怕斑塊堵塞血管,突然倒下,丈夫就因為這個走的。
她想趁着自己還走得動,盡快送走兒子。她不斷申訴,讨要死亡證明,事情轉到了醫院,2017年邀請她去面談,但是沒有結果。
知道當年事情的人要麼調走,要麼退休了,病例資料也都沒了,隻能保存5年。直到2019年初,憑借上海市衛健委一封回執,再次去醫院,才成功拿到死亡證明,第一聯的複印件。二三聯已經丢失了,按照規定,第一聯原件必須保存在醫院。
當天下午,她就去了公安局,想給兒子銷戶,換殡葬證明,但複印件不能用。她又講了一遍自己的故事。對方聽完,讓她先回去,5天後打來電話,至此,兒子去世第十六年,她終于拿到殡葬證明。
然而,十六年的冷凍費又成了難題。胡月琴相信這筆錢應由醫院來承擔,為此不惜要請律師打官司。11月6日中午,她見到了斯偉江,這位因代理李莊案、林森浩投毒案聞名的律師經常從事法律援助。
會面一開始,斯偉江就提出,先安葬孩子,再專心打官司,胡月琴答應了,這讓斯偉江也松了口氣,他還怕她會倔強到底。胡月琴沒說,要是丈夫還在,他很可能不同意這個方案。
會見超過了胡月琴的預期,斯偉江不僅和她簽了合同,還無償代理。在律師離開去拿合同的間隙,她嘴角不自覺地抽動,心跳加快,呼吸也急促起來,吞下好幾口空氣。“心中一塊石頭落下了,就覺得終于有依靠了。”她說。
總算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了。第二天清晨散步,她去逛了趟花鳥市場,三塊錢買了袋山泥土,從小玩到大的老鄰居給新家送了幾盆吊蘭和蘆荟,原本快養死了,但後來她每天早晚噴水,又活了過來,其中一株吊蘭還長出了墜絲。這些植物也是家裡最有生氣的地方。

胡月琴在逛花鳥市場。周航/攝 胡月琴在逛花鳥市場。周航/攝
這兩年,胡月琴的退休工資已經漲到了七千多,每個月還有八百多的失獨補貼。她一直很節儉,衣服仍舊是上班時穿的,綴着碎花的素雅款,黑色滌綸褲子也穿了幾十年。去超市,要遇到優惠活動才買速凍餃子。攢下的錢,她要安葬兒子和丈夫,以及為自己生病做打算。
今年10月,她去了一趟殡儀館,問冷凍的具體費用。當時她還想見孩子,但被拒絕了。寶山殡儀館的張燕聽說後打來電話勸她,孩子的面還是先别見了,17年了,容貌已經不成樣子。
館内知道這件事前因後果的也隻剩張燕了。她從當年的小張成了現在的老張。張燕還記得,當年是一個男人苦苦哀求,就差下跪,她才打申請,同意接收了遺體。剛開始的幾年,這個男人會經常來看望,她一直以為那是孩子的父親。但胡月琴說,那其實是自己的弟弟,他住的離殡儀館近。她也是聽張燕說起後,才知道弟弟經常會去看自己的小侄子。
現在,張燕的工作就是處理這些長期滞留的遺體。她最熟悉的數字是10950元,這是一年的保管費,幾十年都沒漲過。他們大多因為醫療糾紛或是遺産糾紛擱置了後事,她每半年梳理一次,給家屬打電話。她的名單上有100個人,最久的從1999年就保留到現在,但和很多人一樣,家屬電話已經打不通了,她也不知道應該拿這些遺體怎麼辦。
張燕對李奇樂印象特别深,他那麼年輕,又有一個容易讓人記住的名字,而且這麼多年後,家屬還能聯系上,簡直就是一個奇迹。
會見過去四天後,斯偉江把愛心人士捐助的20萬打到了胡月琴賬戶上,胡月琴去辦手續,在政策範圍内,殡儀館為她免去了十萬。這筆錢是自己能承受的,于是她把20萬又退還給了斯偉江。
減免前,她還特地問斯偉江,這會不會影響之後向醫院起訴,得到否定的答案才申請。她依舊堅持要向醫院讨要冷凍費,以及一個道歉,為何可以因為欠費就不提供死亡證明。

2019年,胡月琴終于拿到死亡證明複印件,換取了殡葬證明。
度過時間
11月14日上午,星期六,離世十七年六個月後,李奇樂的葬禮在寶山殡儀館最大的告别廳舉行。十多個家人都到齊了,包括她年逾八十的大哥大嫂,晚輩攙扶着過來,還有丈夫的姐姐和嫂嫂也拄拐到了。
兒子的臉被風衣領子遮了起來。胡月琴個子小,隔着花圈看不到。之後兩個兄弟和兩個侄子給棺材上釘,也攔住了她,勸她别看了,她也沒有堅持。
合上棺材,胡月琴再也抑制不住,扶着靈柩放聲哭了起來,不再是以前那樣默默哭,而是嚎啕大哭。
無論如何,總算把兒子送走了。她捧回了骨灰,将它和丈夫骨灰放在一起。她還沒想好怎麼安葬,沒有後人,就算買了墓地以後也無人打掃。也許會選擇海葬。兒子的照片,她想在生前處理好它們,但不知道應該燒了還是撕碎扔掉。就像算賬時不能搞錯一個數字,她總是願意把事情考慮得盡量周到。
打完官司後的事,她還沒想過。也許會像河水,聽憑自然,順流而下。
固定的作息又恢複了,每天早上7點準時出門散步。回來繼續看書,還是她年輕時愛看的言情小說。她知道書裡面都是瞎編的,純粹消磨時光。她經曆的現實就沒有一見鐘情,都是日子久了,成了親情。她有時候會想,是不是結婚生子也不是必要的,那樣她或許可以一直留住幸福的時光。
那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作為家裡唯一的女兒,她曾經受盡寵愛。結婚後,她分到自己的小房子,後來又搬到鴛鴦樓,二十多年前又搬到現在的兩居室,始終沒離開過同濟新村。這方天地就足夠了,她曾經想過,等李奇樂成家了,就把這讓給他做婚房,自己和丈夫搬到郊區去住。17年過去,這間屋子已經從當年的20萬漲到了500萬,但對她來說也沒有任何意義了。
堅持起訴,錢也是最次要的。她早就過了這個階段。曾經她也在單位積極表現,努力升職,自從兒子走後,她就發現這一切都不重要。見到幾個晚輩,她總提醒,最重要照顧好身子。
她至今還欠着醫院那筆醫藥費,當年因為區人大常委會的發函暫停執行,哪怕這次官司會重新激活這筆錢,她也要堅持追責對方曾以拖欠醫藥費不給死亡證明。
“橋歸橋,路歸路,該我付的錢我會認。”她說。
前幾天奔波兒子的事,她一直沒睡着覺。送走兒子那天,她終于又睡着了,迷迷糊糊得睡上兩小時。自從兒子走後,她的睡眠就成了這樣子,這幾年她總是聽着聽書軟件睡覺,有時候醒來發現聽過了,再調回原來的位置。
第二天醒來,吃完早餐,散步。接着是午飯。傍晚喝完粥,5點半準時拉上窗簾,看本地電視新聞。9點電視劇播完,拉開窗簾,映着窗外的路燈睡覺。
夜深以後,除了馬路上偶然駛過的汽車聲,隻有秒針的走字聲。這塊方形鐘表從1996年用到現在,取下來時外框碎了,一度拿到了垃圾角,臨扔前反悔了,她看到它還在走字,又拿回卧室,放在電視機櫃上,斜靠着牆。咔哒咔哒,一秒一響。
(文中張燕為化名)
版權聲明:本文所有内容著作權歸屬于搜狐享有,未經搜狐書面許可,不得轉載、摘編或以其他形式使用,另有聲明除外。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