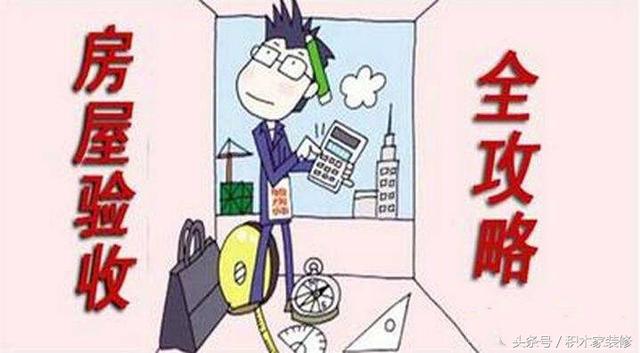圖片來源:影像中國
我在高速公路上開車,有時看見某個熟悉的路牌,就打轉向燈順勢拐過去,因為它指向鄱陽。
離開鄱陽縣城二十多年,我無數次重演以上“即興之舉”。
爸爸和妹妹住在城裡,幾個親友住在縣城四周。于我而言,他們是情感吸鐵石,但他們又不是我去鄱陽的全部理由。
每次妹妹問:晚飯想吃點什麼?我都回答:炒粉皮子。然後車剛進城,粉皮子就等在路上,妹妹端着它,從車窗遞進來,然後一車人都興奮起來。
藜蒿炒臘肉、鲇魚糊、春不老煮黃芽頭、柘港豆腐、水菜煲……鄱陽的吃食,細數起來真是讓人口舌生津。還有獨特的糕點蔥酥餅,一咬就掉碎屑,面粉、豬油、蔥、糖、鹽雜糅在一起的口感,很獨特,尤其是剛出爐時,軟軟熱熱的,我一口氣能吃四塊。早晨吃稀飯時,我偶爾還會懷念油條包麻糍。這種把油條的酥脆和麻糍的軟糯融為一體的早點,體現了鄱陽人對美食文化的獨特領悟。
舌頭上的記憶就是這樣頑固。不管離開鄱陽多久,我最喜歡的食物還是這些。
作為鄱陽湖邊的古城,鄱陽的氣味也是特殊的。
首先是水的氣味。寬廣的昌江流經鄱陽城奔向鄱陽湖,在城裡留下韭菜湖、青山湖、土湖、東湖、球場湖五片湖。可以說,鄱陽是一座浮在水上的城。湖水在晴天蒸發出的腥甜味、雨天浮泛的鐵鏽味,彌漫在當地人的每一寸生活空間。每次去鄱陽,傍晚時分,我總要到城西的圩堤和高門碼頭散步。一邊走着,一邊尋找小幹魚被陽光暴曬又被雨水浸泡後的獨特氣味。有時一個人在河邊站着,當河水既腥又甜的氣味濕漉漉地湧來時,全身都感覺到了暢快。
這時,如果沿河路夜宵攤上,傳來幾聲用方言喊的招攬顧客的吆喝聲,我便會跟着那聲音走回從前。
縣城講方言,因為多是本地人。我雖然也留戀縣城的美景,卻不想被方言所代表的小城生活所固定,二十多歲時總是向往着遠方。
我先後在縣城的中學和報社工作,業餘寫散文、小說和詩歌。我總愛騎着山地車在一些人少的場所遊逛。芝山、西門圩堤、高門碼頭……我的足迹在這些地點之間來回穿梭,不斷在心裡構思一條遠行的路。
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的一個冬天,某個大雪飛揚的日子,我終于登上一艘隻有兩三位客人的客輪,離開了鄱陽縣城。
隻是沒有想到,回歸會發生得那麼迅速。2000年夏天女兒出生,在我的父母家住了約一年。那段時間,我幾乎每個周五都要坐五六個小時的大巴或夜班船回鄱陽,周日晚上又原路返回。那些奔波卻又溫馨的日子,迄今回憶起來都很幸福。
大概就是從那時開始,我深刻地體會到自己和鄱陽這座城之間複雜的情感交織。以至于後來每次在南昌街頭聽到有人說鄱陽方言時,我都會眼中一熱,忍不住多看人家幾眼。在外地旅行,遇到講鄱陽方言的一家人,總會不知不覺跟着他們多走一段路,雖然從不上前搭腔,心裡卻有種小小的滿足感。
媽媽去世後,我有次去鄱陽,在東門口大街見到一位頭發花白的大媽彎腰買菜。她身材微胖,和媽媽差不多,穿的羽絨服也是媽媽喜歡的款式。我湊過去聽她和小販砍價,當熟悉的方言傳到耳朵裡時,眼淚頓時熱辣辣地湧起。
現在,随着高速公路的修建和高鐵的開通,鄱陽城裡說普通話的人越來越多。縣城居民增至近三十萬,其中十萬是流動人口,城區面積、店鋪數量也比二十年前翻了幾倍,就連被水葫蘆和綠藻掩蓋多年的内湖也開始蘇醒。挖掘機們正日夜加班,準備把五個内湖串聯打通,讓它們變成活水流向鄱陽湖。
隻是,不管鄱陽這座城的外表怎麼演變,我總能以味覺、嗅覺、聽覺為觸手抓住它的本質。而對于我來說,不管離開鄱陽多久,不管走到哪裡,吃得最爽口的還是那些食物,聞得最親切的還是那些氣味,聽得最溫暖的還是那些聲音。
最近一次去鄱陽,住在父親獨居的中學老宿舍樓裡。屋子裡充塞着老家具、舊衣物、書籍等。妹妹嘗試着偷偷把那些舊物清理掉,讓房間更潔淨舒爽些。父親發現後連忙制止:“我就是想看着它們過日子,不行嗎?”在父親心中,那些物件雖然老舊,卻有着特别的情感價值。
有天深夜,我在一隻舊皮箱裡翻到在鄱陽工作時發表作品的樣報樣刊,接着睡覺時居然夢見了那時縣城街頭的梧桐樹,以及父母在廚房一邊聽收音機一邊交談的情景……
第二天一早,我被斑鸠叫醒。在晨光裡,我忽然有種幻覺,似乎自己從未離開過鄱陽。
《 人民日報 》( 2020年06月24日 20 版)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