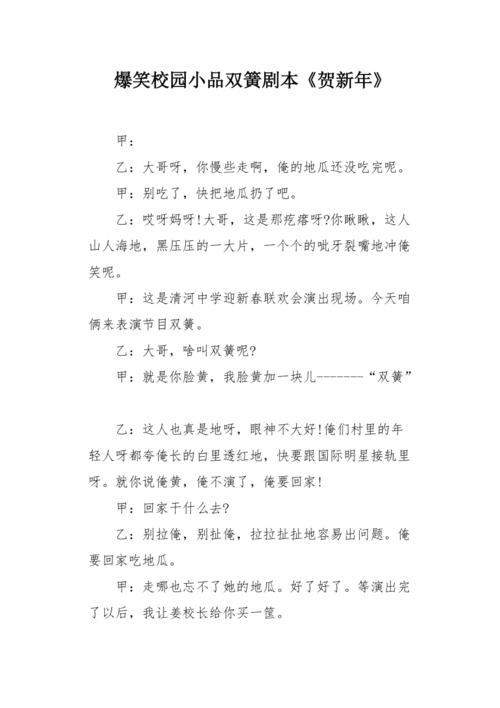戲劇演出應該是什麼樣的?台上聲台行表、全情投入,台下鴉雀無聲、正襟危坐,大概是多數人印象中的情形。而觀衆“質問”演員、将演員問得“張口結舌、變了臉色”,這種場面大約會令人想到演出事故,但對于一些沉浸式戲劇來說,這正是新鮮的玩法、不同的體驗。

從經典之作《無人入眠》到新秀《瘋狂理發店》《阿波羅尼亞》等,各類沉浸式戲劇你方唱罷我登場。近年來,沉浸式戲劇在國内演出市場上大量湧現,受到許多觀衆尤其是年輕人的歡迎,其發展态勢堪用如火如荼來形容。随着不同藝術門類、文娛方式的對話交流,越來越多帶有戲劇元素的演藝項目加入沉浸的行列,豐富甚至挑戰着傳統的戲劇觀念和演藝格局,也再次喚起人們對戲劇性、文學性的思考,成為令人矚目的行業現象和文化景觀。
從觀看到參與,方興未艾
沉浸式戲劇以新穎的演出形式、新鮮的觀看體驗成為市場的新晉寵兒,實際上,沉浸式戲劇并不很年輕,其曆史已有數十年之久。資料顯示,1975年,設計師尤金·李把一座劇場改建成遊藝場,場内不僅有演出,還設有遊戲機、小吃攤位、照相館等,觀衆可以自由漫步,自行決定觀看哪個演出,或者吃些小吃、喝點啤酒——這就是美國演藝項目《冷酷大教堂》,其藝術影響力延續至今。
多年來,為了給觀衆提供新鮮感、沉浸感,國内創作者想出了許多辦法突破原有的演出模式,刷新戲劇的觀演方式。以《奮不顧身的愛情》為代表,一些小劇場話劇雖然仍在傳統的鏡框式舞台上演出,但演員會配合劇情發展而在某些時刻來到觀衆席中表演,拉近劇情與觀衆的距離;以賴聲川執導的話劇《如夢之夢》為代表的一批作品使用環繞式舞台或者将表演區域延伸到觀衆席中,沉浸感進一步增強;各大旅遊景區的文旅演藝劇經常把舞台設置在真實的山水園林之間,戲劇環境與更廣闊複雜的自然、人文環境相融合;被譽為沉浸式戲劇天花闆的《無人入眠》在其演出場地設置了幾十個房間、同時上演着不同的劇情,觀衆可以自行選擇房間來觀看,還有機會與演員互動。這些演出形式各不相同,但都籠統地冠以“沉浸”之名。
盡管沉浸式戲劇有着較為豐厚的曆史積澱和創作實績,然而究竟什麼是沉浸式戲劇,從業者、理論界往往莫衷一是。哥倫比亞大學戲劇學者阿諾德·阿隆森提出的一個比較簡單、通用的定義,基本能夠囊括各種看法之間的共識,即“沉浸式戲劇是一個參與性的演出事件,包括一個包羅萬象的吸納性環境,調動了所有的感覺”。以此觀之,目前一部分被稱為沉浸式戲劇的作品、演藝項目實際上并不十分沉浸,而更像是特殊場域展演,或處于特殊場域展演與沉浸式戲劇的中間地帶。
有的在徘徊,有的很激進,不乏創作者步子邁得很大,在作品中盡可能調動多重感官并且大量“留白”,呼喚觀衆參與。自2017年起從英國引進、經本土化改編後落地上海的《玩味探險家》《玩味放映廳》等“玩味”系列劇集定位為賞味環境劇,将戲劇與飲食結合起來,觀衆不僅可以觀劇、即興互動,還能同時大快朵頤,不少觀衆表示很好玩、很好吃。不過,這究竟是戲劇還是真人互動遊戲?許多觀衆在沉浸過後收獲了輕松愉悅,未必會考慮這個問題。作為觀衆,也的确沒有回答這一問題的義務。
此劇場已非彼劇場
那些呼喚觀衆深度參與的戲劇作品,究竟是戲劇還是真人互動遊戲?
《玩味探險家》總制作人謝已在采訪中表示,沉浸式戲劇“最本質的要求”就是要做一個足夠新鮮、吸引人的東西,一種觀衆在網上無法體驗的東西,于是給觀衆一個走出家門、來到現場的理由。
這種觀點是在線上與線下、戲劇與其他相互競争的語境中看待沉浸式戲劇的。的确,沉浸式戲劇的走紅與新興媒體的影響、文化消費方式的變革升級、激烈的市場競争等密切相關。在注意力經濟的背景下,許多曾經相隔甚遠的文娛品種,一下子成了彼此的競品,相互之間的切磋、借鑒、共融自然而然地發生。正如上海戲劇學院教授韓生所說,交叉融合、邊界模糊是當今藝術的共同特點,其背後是整體文化生态的沿革,源自當今社會生活方式已經發生的深刻轉型。當代觀衆能夠輕松便捷地通過多種媒介形式獲取不同的文化娛樂享受,新媒體、新技術也催生了全新的消費場景、消費體驗,高速移動互聯網、智能穿戴設備等的普及,還将進一步加速這一進程。垂直分衆的供給、豐富多元的選擇大幅提升了人們在文化消費中的自主性、能動性,觀衆對戲劇的審美期待、戲劇人的創作方式也在這個過程中悄然改變。
廣西藝術學院影視與傳媒學院戲劇影視文學系教師韋哲宇分析,尋求消費市場的戲劇創作者一方面引入各類景觀,通過演出場域的技術、裝置等為觀衆呈現銀幕、屏幕所難以提供的精緻影像和奇觀;另一方面,當代戲劇也在創作和演出中鼓勵遊戲,讓觀衆盡可能獲得即興、自由、創造性等在其他渠道較少享受到的差異化消費體驗。不難發現,上述兩種訴求在沉浸式戲劇創作演出中交相輝映,戲劇成為“幻覺機器”,讓觀衆暫時進入虛構時空、抽離自身的社會屬性,在一場戲的時間裡成為某位他者,這既是體驗,也是表演。表演的沖動堪稱人類自古以來便具有的精神文化需求甚或一種天性,在不同社會、時代條件下被以不同的方式滿足,眼下沉浸式戲劇的火爆,正是一種天性解放,恰逢其時。
某事物的蓬勃發展除了外部環境的刺激,也必定有内生動力的推動。沉浸式戲劇是戲劇人對日益挑剔的演出市場做出的積極回應,也是戲劇自身在特定條件下不斷求新求變的階段性形态,或者樂觀地說:階段性成果。

如果說内容的差異成就作品的個性,那麼,觀演關系的變革則可能創造新的戲劇樣式。從“黑匣子”裡的先鋒實驗,到山水田園間的實景演出,創作者不斷嘗試新的演藝空間、演出模式,努力推動戲劇藝術創新發展。在此過程中,《絕對信号》《同船過渡》《如夢之夢》《隻有河南·戲劇幻城》等作品,都留下了它們的名字。中國舞台美術學會會長曹林認為,當今時代,戲劇演出是多向性的,各種不同形式的戲劇活動競相出現,戲劇的場域無處不在。所謂劇場藝術之“劇場”也并非傳統意義上用來承載戲劇表演的物理空間,而是更接近“磁場”的意思,它是藝術行為、藝術作品相互作用的共享空間,與生活中的現實場域相平行。
在國内外理論思考與藝術實踐的洗禮下,戲劇的觀念、形态發生着變化。以内外雙重視角觀照沉浸式戲劇,其發展繁榮的理路似乎變得更為清晰。然而,那個觀衆沒有義務回答的問題,專業人士卻不得不回答:那些呼喚觀衆深度參與的戲劇作品,究竟是戲劇還是真人互動遊戲?這個問題也許觸及某些重大的課題或變革。劇評人安妮認為,《無人入眠》這類作品讓人們盡可能地沉浸在戲劇營造的世界,盡管觀衆可以參與,但無論觀衆做什麼,幾乎都不會對戲劇世界造成影響,而對于有些作品來說,觀衆的個人選擇、個人叙事疊加在戲劇世界之上,很可能影響或改變故事的走向。倘若如同部分理論家所說,觀看行為定義了當代戲劇的本質屬性,那麼,當觀衆之于戲劇的關系從觀看變成了參與乃至左右,戲劇還是原來的那個戲劇嗎?
拆除劇場外那幾磴台階
所謂戲劇性、文學性,究竟是什麼?戲劇與文學究竟能帶給觀衆什麼?
如果說阿爾托所倡導的那種觀衆坐在中央,被場景、持續不斷的音響包圍,以全身心投入、集體狂歡為特點的殘酷戲劇被廣泛認為是戲劇,那麼沉浸式戲劇自然也屬于戲劇範疇,這在邏輯上應當沒有太大疑問。不過現實中,觀衆思考問題的出發點往往并非邏輯,而是體驗。網絡平台上,許多網友将沉浸式戲劇與劇本殺甚至密室逃脫相提并論。杭州小夥王旭斌就是個沉浸式戲劇的愛好者,同時是劇本殺“骨灰級”玩家。“雖然玩劇本殺時人手一份劇本,但不到最後一刻還是很難猜出事件的真相、故事的結局,這種邊看、邊猜、邊體驗的感覺,和沉浸式戲劇差不多。”王旭斌說,“我知道,專業人士可能認為它倆不是一回事,但對我來說,除了沉浸式戲劇的票更貴、綜合體驗更好一點,它倆幾乎就是一回事。”
這種混同是一個戲劇地位被挑戰的危險信号嗎?如果能夠接受交叉融合、邊界模糊是當今藝術共同趨勢的觀點,那麼對于沉浸式戲劇的“劇本殺化”抑或其他什麼“化”,就不必太過激動地口誅筆伐,這一變化也許還會帶來一些好處。
正如編劇、策劃人史航所說,戲劇是有門檻的,劇場外那幾磴台階使得人們不會一不小心就走進來,至少需要買張票。沉浸式戲劇以及帶有戲劇元素的各種文化娛樂形式融合着戲劇性、文學性的内核,以風格類型各異但同樣新鮮誘人的姿态,拆除了劇場外的那幾磴台階,于是越來越多人進來了。盡管還是要買張票,但觀衆、玩家至少能夠感知,戲劇、文學距離自己并不遙遠。讓更廣泛的群體有機會走近戲劇、走近文學,這顯然不是壞事。
那麼,所謂戲劇性、文學性,究竟是什麼?戲劇與文學究竟能帶給觀衆什麼?學術界關于文學性的讨論曠日持久,這确乎是值得不斷探讨但很難給出精準答案的問題。在第九屆烏鎮戲劇節的小鎮對話“文學與劇場”中,知名作家、編劇劉恒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劉恒認為,僅僅文字上的錯彩镂金或遊刃有餘,價值總是有限的,文學與劇場是精神的會餐。“我自己總結,文學與劇場的真正本質是一種對抗。”劉恒說,文學與時間對抗,容易遺忘的人類靠文學來固定對這個世界的看法,經典的作品成為創造者生命不朽的象征;文學與愚蠢對抗,人類用文學來促使自己清醒,用文學來增強自己的智力;文學與理性對抗,過分相信自己的理性可能産生偏見、導緻災難,文學保留着人類珍貴的感性;文學與複雜的現實對抗,告訴人們怎樣更符合人類文明的發展、符合人性的基本需求。“最根本的是,文學與命運、與不确定性對抗,它在精神上撫慰我們,我們進劇場看劇的時候,尋找的正是這個東西。”劉恒說。

文學與戲劇形而上的價值理想,總要以具體、生動、可實操的方式體現在一部部作品之中。探讨愛、死亡、人性、命運、時代等重大母題的戲劇作品,古今中外都不乏佳作,從《哈姆雷特》到《雷雨》,從《等待戈多》到《茶館》,不一而足。對于部分沉浸式戲劇以及更具融合性、實驗性的文娛形态來說,處理重大命題的創作沖動猶在。戲劇團體“爪馬戲劇”打造的《玩家 the life》融合了戲劇表演、桌遊、線下社交等元素,定位為“沉浸式互動演繹”。在《玩家 the life》中,每一位觀衆都被設定為登錄虛拟遊戲的玩家,玩家使用的遊戲币則是時間、智慧、健康、顔值等人生中頗為珍貴的财富。不同的價值、财富應當怎樣權衡取舍?的确是傷腦筋的問題,《玩家 the life》希望通過這樣的方式喚起對時間、生命等重大命題的思考。這種思考帶有藝術、遊戲的特征,無法解決人生中遇到的現實問題,然而思考過與始終懵懂終歸不同,增加生命的厚度、深度與豐富性,本身就是一種非凡的意義,也是人類之所以需要文學、需要戲劇的一個重要原因。
過山車與莎士比亞本不矛盾
戲劇或言藝術之于觀衆,是一種單純技術性、服務性的滿足,還是肩負啟迪、滋養、引領的使命?打造具有莎士比亞氣質的過山車,會不會更吸引人呢?
任何事物尤其是新生事物,都難免在獲得追捧的同時遭受質疑,前者證明了該事物存在的價值,後者指出了該事物進化的方向。毀譽參半是常态,喜歡沉浸式戲劇和類似文娛項目的人能夠從中感受沉浸帶來的美好,而不喜歡它的人則反而感受到緊張、疏離甚至空洞。
的确,并不是所有的沉浸式戲劇或相關文娛項目都有捍衛文學性、戲劇性等價值内核的自覺。在求新求異的沖動、激烈的市場競争、新技術的蠢蠢欲動以及變現的急迫心情等共同作用之下,不少沉浸項目形式大于内容、體驗大于内涵、噱頭大于實質。原本,文學性、戲劇性借助新的形式而飛入尋常百姓家,而後者逐漸成熟之後,則可能成為科幻電影中背棄了人類的人工智能,張揚起極度商業化的、消費主義的自我意識,在純感官的道路上狂奔,文學性、戲劇性已經被抛諸腦後。
當然了,不少傳統的、相對嚴肅的戲劇,也不見得有多麼強烈的價值自覺,新生事物在發展過程中經曆野蠻生長或者自願做出選擇,都是很自然的現象,不至于為之椎心泣血。隻不過,從來沒有一部内涵阙如的作品成為經典或者爆款,這是時間和市場宣告的事實。那麼,“過山車一定比莎士比亞更吸引人”的看法,是一廂情願的假設,還是經過了市場檢驗的真理,抑或是自作聰明的偏見乃至思想缺席的借口?戲劇或言藝術之于觀衆,是一種單純技術性、服務性的滿足,還是肩負啟迪、滋養、引領的使命?打造具有莎士比亞氣質的過山車,會不會更吸引人呢?有些東西本就并非勢同水火、非此即彼,沒理由自矜高傲,也不必太過屈尊降貴。
暫時擱置思想價值問題,僅就形式而言,沉浸式戲劇也受到部分觀衆的質疑。讀中文系的小謝将元雜劇作為研究對象,同時也經常光顧劇場。小謝表示,他更喜歡傳統鏡框式舞台的戲劇樣式,“第四堵牆”的存在為他構築起心理屏障,能夠給予他安全感。“在這種情況下,我反而更能沉浸到劇情、人物與戲劇氛圍之中。一幫演員圍着我演戲的沉浸式戲劇我也看過,常常感到緊張無措,我不知道下一秒他們要幹什麼,會不會突然把我拉起來演一段兒,這種擔心讓我惴惴不安,很難投入劇情。”小謝說,“如果沉浸式戲劇開演之前能把劇本發給我,可能會緩解我的緊張,但那樣的話,我更分不清自己是看戲的還是演戲的,是該買票還是賣票了。”當然,換個角度觀照,看戲的和演戲的也許根本不需要區分,至于票,肯定要買,否則沉浸的費用從哪來?
中國傳媒大學副教授劉洋認為,目前,沉浸式戲劇的“沉浸”主要體現在空間場所、環境體驗層面,而不一定是心理、情感、文化層面。然而,一部作品與觀衆的真正距離恰恰主要體現在心理、情感和文化上,物理空間的消弭未必帶來心理距離的拉近,有時甚至适得其反。這種微妙的審美心理不僅關乎沉浸式戲劇創作的得失,而是有着更具普遍性的意義。
從操作難度上考量,空間場所上的沉浸并不太難,在沉浸中安排吃喝玩樂也不太難,資金到位後,藝術問題主要成了施工問題。然而,敢想、敢做畢竟不等于才華與生命力。藝術作品要真正實現與觀衆的精神對話,光靠“推牆破框”恐怕不夠,光靠新鮮刺激恐怕也不夠。那麼怎樣才夠呢?事情發展到這裡,似乎就又回到了文學性、戲劇性這個經典命題之上。
以長線的、曆史的眼光看,戲劇不斷啟發、滋養其他藝術形式、文娛方式,這是戲劇生命力旺盛的表現,其自身也在這一過程中覓得更多的知音、惠及更廣的群體。然而,當生活中處處是“戲劇”,可能也同時意味着,世界上已經沒有了戲劇。因此當務之急或許是:生活中不妨處處是“戲劇”,但戲劇,應該始終在場。
來源: 中國文化報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