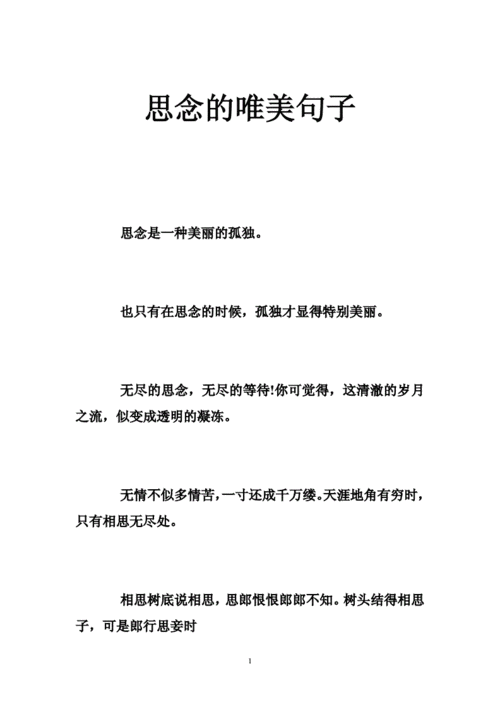那天是6月18日,嶽父來接兒子過去住幾天。吃晚飯時,我陪着喝了點酒,就由妻子開車送嶽父和兒子回嶽父在城南的家。
半個小時後,我有點兒心神不甯,以為是不勝酒力的關系,開着電視迷迷糊糊地躺在沙發上,仿佛看到妻子回來了,過來摸我的額頭嗔怪我沒酒量還逞能。
夢似真似假地一直做着。不知過了多久,刺耳的電話鈴聲把我驚醒,頭像裂開一般疼痛起來。那邊問:“請問你是秦小敏的家屬嗎?”
我不記得是怎樣到醫院的,我掙紮着,硬是邁不動走向他們的腳步。兒子還在手術室裡,妻子和嶽父卻已經白布蒙面。我握了握嶽父冰冷的手,又抱了抱妻子毫無溫度的身體,好一陣兒都回不過神兒來接受眼前的事實。很想大哭,或者大叫。可是我什麼話都說不出來,我隻是蒙了,兩腿軟得跪在地上起不來。我不知道,我是怎麼度過那兩天的,他們叫我吃飯,我就吃,叫我喝水,我也喝。
我并不知道他們說些什麼,我的腦子裡一片空白。隻是偶爾聽見妻子好似在叫我“老公”,然後是兒子快樂的叫聲—“爸爸”。那聲音時遠時近,時清晰時模糊,在匆匆趕來安慰探望的親友的吵鬧聲中,斷斷續續,不曾消失。
我心痛難忍,那是一種不單來自于心理上的痛,還有生理上的窒息一般的絞痛。我大口地吸氣,試圖讓自己平靜下來,傷心欲絕的嶽母需要我,兒子也需要我。
他的求情
不大的一個會議室裡吵吵嚷嚷,我們來了好幾次,是公安局通知來與肇事者家人見面。肇事者是獨生子,父母在市外的一個小縣城裡。這次車禍四死五傷,報紙電視全都播了,他們不可能不知道。可一連許多天,都聯系不上人,打了好幾次電話,要麼不接,要麼說來,等了好幾次,都沒見人。
所以當那個男人進來時,我連日來的疲憊、悲痛與憤怒都已經到達了崩潰的頂點,我沖了過去,沖他臉上就是幾個大耳光。他低着頭,被我打得一個踉跄,差點兒沒倒在地上。
其他人也沖上來破口大罵,另一個死了丈夫的女人,更是又抓又打,歇斯底裡。
打過了人的手,有點兒辣絲絲的痛。這是一周多來,第一次感覺除了心髒以外,身體上還有其他地方有痛感。我看向剛才差點被我打暈在地的那個男人,才發現,他是個頭發花白一臉憔悴的清瘦老漢,年紀大約60歲上下,嘴唇哆嗦着,任由那個悲痛憤怒的喪夫女人推搡着,像隻破敗無力的麻袋。
在場的公安人員過去拉開那個痛哭的女人:“周明理,你兒子撞死撞傷了這麼多人,叫你來你就應該及時來,不能來也說個理由,逃避絕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他枯瘦的手顫抖着伸進外套口袋,掏出一包煙來,想遞給誰,可大家都在冷冷地看着他。他捏着那包煙,就那麼僵硬了半晌,忽然“撲通”一下,就朝我跪下了:“大兄弟,我對不住你,我對不住大夥。我這些天,向親戚借錢去了。我知道用錢也買不回命,可我求求你們,留我家偉子一條命吧!”
他的話,讓我剛才好不容易才平息下去的悲痛和怒火,騰地一下又燒起來了,我想指着他的鼻子大罵他教子無方為老不尊,他以為用錢什麼都可以買到嗎?我的妻子,我的嶽父,他們做錯了什麼?要這樣白白送命!
我怒火中燒地看着他,這個年紀與我父親相差無幾卻跪在我面前的花甲老人,他的眼睛裡,閃動着的光芒,有迫切、有焦慮、有懇求、有無奈、有痛楚,有許許多多我說不清楚的情緒。這種似曾相識的情緒,令我想起了面臨噩耗的自己,我慢慢松開緊緊握住的拳頭,點了一支煙,以控制自己的怒火。
“大兄弟,大嬸子,我教子無方。我35歲那年才生了偉子,就這麼一個孩兒。偉子他不是那種做盡壞事的孩兒,你們就給他一次機會吧。我給你們磕頭了。”
他說着,就磕起頭來。在場的人年紀都比他小,他一個又一個響頭地磕着,大家一下子都蒙了。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