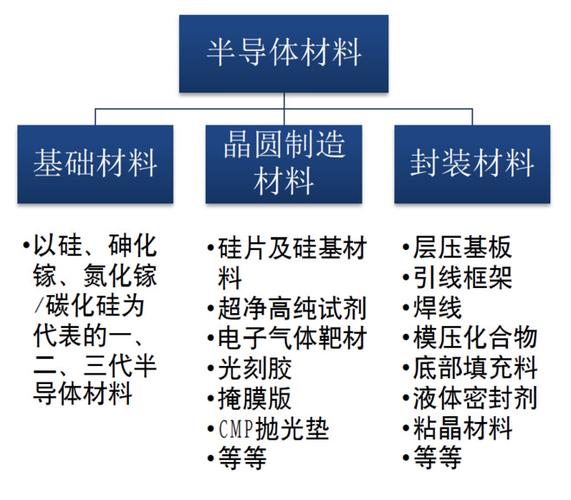在古代文壇上,沒有哪一對兄弟像蘇轼和蘇轍,同樣驚才豔豔,又一生相互扶持,情深似海。
曹丕和曹植這對兄弟,曹植才高八鬥,一篇《洛神賦》驚豔了世人一千多年。
曹丕同樣不凡,他的《燕歌行》現存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詩,開千古之妙境;還有他的理論著作《典論·論文》,開創了文學批評的風氣,是中國文學批評之祖。
然而這對兄弟為了王位和女人争得你死我活,同室操戈,令人唏噓。

唐朝的王維和王缙,是出了名的兄弟情深。
王維安史之亂時曾當過僞臣,後來差點被清算,當時他的弟弟王缙是刑部侍郎,前途一片光明,但為了給哥哥王維求情,甘願削職為其贖罪。
而王維晚年的時候,又上書皇帝請求削盡己官,以換得弟弟重回京師。
王維的詩才是衆所周知的,王缙雖然後世也評價“文筆泉薮,善草隸書”,但他在文學上的成就實在難以和王維相提并論。
但是蘇轼和蘇轍這對兄弟不一樣,蘇轼以詩詞聞名後世,而蘇轍則是以散文著稱,兩人同為“唐宋八大家”。
而他們的之間的兄弟之情更是令後人感動。

都說蘇轼豁達從容,除了本性使然,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的弟弟蘇轍為他承擔了生活的瑣碎與不堪。
在蘇轼因“烏台詩案”入獄,蘇轍不僅上書請求以自身官職替兄贖罪,到處為兄長奔波,還承擔起照顧蘇轼家小的任務。
蘇轼出獄後被貶黃州,蘇轍也被貶到了江西,他帶着兩家幾十口人一起上路,到了江西安頓好家人後,又護送蘇轼家小趕往黃州。
後來蘇轼被貶惠州,沒錢上路,又是蘇轍千方百計為他籌措了一筆錢。
當然,蘇轼對蘇轍的感情也是十分深厚的,兩人聚少離多,蘇轼常寫詩詞懷念弟弟,據不完全統計,蘇轼留下的詩詞中提及“子由”的便有将近200首。
今天我們就從首寫于中秋的《水調歌頭》,來感受蘇轼和蘇轍的手足情深。


這首《水調歌頭》實在太經典,無論是說到蘇轼,還是中秋,亦或是這個詞牌名,都不得不提這首詞。
寫這首詞的時候,蘇轼還未經曆“烏台詩案”,當時他在密州(山東諸城)擔任知州。
而蘇轍呢?他在齊州(山東濟南)任掌書記一職。
如今看來同處一省,距離很近,但古代交通不便,何況兩人都有職務在身,想要見上一面實在是難。
昔日同進同出的兩兄弟,如今一别就是六七年,蘇轼心中對弟弟的挂念可想而知。
1076年的中秋他在月下獨酌,喝得酩酊大醉,醒來後揮筆寫下了這首詞,抒發了他對弟弟的無限思念之情。
“但願人長久,千裡共婵娟”,詞作最後一句突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阻隔,淋漓盡緻地表達了他對弟弟,還有普通下所有人的美好祝願。
後世對這首詞的評價非常高,“中秋詞,自東坡《水調歌頭》一出,餘詞俱廢”,我深以為然。


這首水調歌頭是蘇轍在1077年所寫。
那一年蘇轼調任徐州,離京赴任途中,遇到蘇轍,兄弟相攜至徐州。
當時蘇轍在徐州呆了一百多天,兄弟兩人對床而眠,詩話平生,留下了“對床夜話”的佳話。
那年的中秋,他們是一起過的,泛舟賞月,對酒吟詩,好不暢快。
然而天下無不散之筵席,中秋過後,蘇轍要離開徐州到他鄉赴任,于是便寫下了這首詞。
上半阕開頭一句“離别一何久,七度過中秋”寫透了這幾年兄弟聚少離多的無奈之情。
接下來的幾句描寫了兩人歡聚的情景,歡樂中帶着悲涼之意,因為他們又要分别了。
下半阕抒發的是離别思鄉之情,還隐隐包含了前途渺茫,人生無奈之意。
兩人重逢又别離,其中的不舍可想而知。


這首《水調歌頭》是一首和詞,當時蘇轼讀了蘇轍的詞後,覺得太過悲涼,便寫了這首詞以安慰對方。
蘇轍的《水調歌頭》以“但恐同王粲,相對永登樓”結尾,表達了他對前途的擔憂,他怕兄弟兩人就像東漢的王粲一樣漂泊異鄉,不得施展才華,又無法回歸故裡,隻能登高以望家鄉。
而蘇轼的這首詞上半阕引用了謝安的典故,隐隐流露出想要隐退之意。
而下半阕中,他開始設想兄弟二人辭官隐退,返回家鄉的情景,“我醉歌時君和,醉倒須君扶我”。
其實,兄弟二人在早年的時候便有“夜雨對床”、“為閑居之樂”的約定,而蘇轼這裡重提舊約,自是為了安慰弟弟,兄弟情深由此可見。
然而可惜的是,蘇轼設想的“退而相從之樂”的場景,這一生都沒有實現。

這三首寫于中秋的《水調歌頭》說盡蘇轼和蘇轍的兄弟情深,千年來感動了無數人。
也許蘇轍的《水調歌頭》水平和境界遠不及蘇轼,但是詞中所流露出的兄弟之情卻無高低、優劣之分。
不知你怎麼看蘇轼和蘇轍的兄弟情?
注:圖片來源于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作者删除。
喜歡這篇文章的朋友,就點個關注哦。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