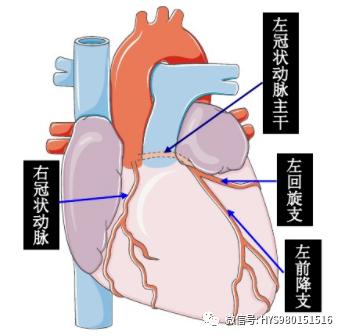“咣當——”一聲刺耳的挪椅子聲敲醒了鄭雲的睡眠。
淩晨五點,窗外還是朦胧的昏暗。“砰砰砰——咔”,腳步聲和開窗聲接踵而至,聲音透過樓層隔闆清晰地傳入耳中,鄭雲隻能從床上坐起,直到五點半,鄭雲起身下樓到車裡繼續休息。
鄭雲今年50歲,居住在昆山的一個小區。離異後,鄭雲習慣了一個人居住。“周末在家裡一個人聽聽音樂,刷刷微博看看電視,生活上也沒有什麼不舒服的地方。”
隻是在噪音每日打卡般一天不落地出現後,這樣的生活好似斷了片,原本舒适的家如今成為了鄭雲最抗拒的地方。她成為了公司裡最早到也是最晚離開的那個人。下班後,她選擇躲進一切能躲藏的地方:酒吧、公園、咖啡店。開車回家途中,擔心疲勞駕駛的她,把車停在回家路上的廠房旁,蜷縮在駕駛座上小憩,驚醒後,鄭雲常常不知道自己身處何方。
像鄭雲這樣被噪音所擾的人不在少數。2019年,來自蘇州的傅嶽建立了微信公衆号“反噪音聯盟”,如今已有一萬五千人關注。而五個微信群如今也有一千五百多人。
這些成員大多生活在城市,平日裡的鄰裡噪音成了成員們共同的“敵人”。
加入反噪音聯盟後,從孤軍奮戰到抱團取暖。大家解決噪音問題的方式也漸漸變得多元。而在建立“反噪音聯盟”一年後,傅嶽将聯盟的名稱改成了“安靜之家”。傅嶽希望大家能夠理性維權,反對以暴制暴,并從自身的改變做起,早日擁有屬于自己的“安靜之家”。

噪音問題出現後,即便是周末,鄭雲隻能選擇待在咖啡店裡等待夜深歸家。新京報記者 周思雅 攝
困在噪音裡
在長期租房的城市青年李林靜(化名)眼裡,她對自己的第一個家充滿了期待。
2017年3月,27歲的李林靜和男友在沈陽市區買下一套100平方米的新房,大大小小的設計、裝修事宜李林靜都親自參與,前後花了一年時間将新房裝修成自己心儀的“工業風格”。
2018年六月搬入新家後,透過隔闆,李林靜能清楚地聽到早晨5點多,樓上老人在客廳砸核桃的聲音,而樓上小孩的跑跳撞擊地闆的聲音也如影随形,“像一個沖擊波,你能感覺到不停的嗡嗡聲,樓闆一直在震。就像你在一個鼓裡邊,他們在上面一直敲你。”
多次溝通無果後,李林靜和男友一度與樓上鄰居起了肢體沖突,而在沖突過後,噪音依舊。
李林靜也曾求助過物業,而物業表示,他們沒有權利明令禁止樓上停止活動。
“那段時間我覺得之前一年裝修期間的那種期待和快樂,看起來像個笑話。”李林靜說。
另一邊, 35歲的傅嶽在蘇州一家外貿公司從事銷售工作。2019年,樓上鄰居的噪音劃破了傅嶽原本平靜的生活。
傅嶽戴着一副黑框眼鏡,說話細聲溫和。為了方便女兒上小學,傅嶽買下蘇州市姑蘇區一套一百平方米的學區房,從蘇州鄉下搬進了這套商品房裡,開車上班的時間也從兩個小時縮減到了半個小時。樓上過去住着一對生活規律的老人,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傅嶽的生活除了柴米油鹽,幾乎沒有波瀾。
直到2019年初,房子搬進了新的鄰居:一家六口,兩個大人、兩個小孩和兩位老人。
傅嶽說,樓上新搬入的鄰居作息和自己完全相反:晚上十一點本是自己入睡的時間,但卻是樓上夫婦剛下班到家的時間。當自己睡意正朦胧時,樓上卻出現了拖拉桌椅、小孩跑跳、收拾房間、搗鼓東西的聲音。好不容易熬到入睡,早上六點多樓上老人買菜的拖車滾輪“咕噜咕噜”,緊接着小孩奔跑—— “咚咚咚”,平日裡八個小時左右的睡眠,傅嶽隻能睡到三四個小時。
傅嶽記得,自己時隔一個月才鼓起勇氣第一次和鄰居溝通。小心敲開對方家門後,傅嶽得到了一句“知道了”的簡單回複後,門随即被關上。傅嶽回到家卻發現,噪音絲毫未減。
溝通次數多了,傅嶽再去敲門便不見開門,“他們在屋子裡說‘知道了你走吧,不要再來了’。”
傅嶽說,在長時間缺少睡眠的情況下,自己的精神狀态出了問題,時常出現晃神,也變得越來越沒有耐心。最沖動的一次,他沖進廚房,拔出一把菜刀,希望上樓和對方拼個“你死我活”。
“冷靜下來後,就覺得自己挺可笑的。”傅嶽回憶,他也曾産生過購買震樓器來反擊對方的想法,但這種想法隻是轉念而逝:這種方式隻會讓雙方關系惡化,“噪音問題仍然無法真正解決”。
此後,傅嶽搬回了鄉下居住,原本半小時的上班路程拉長到了兩個小時。即便如此,傅嶽覺得,相比忍受噪音侵擾和睡眠不足的問題,兩個小時的車程已經不值一提。

傅嶽在“安靜之家”公衆号裡講解噪音知識。受訪者供圖
安靜之家

2019年底,由于女兒到了上小學的年紀,傅嶽隻能選擇搬回市區的房子,直面噪音問題。他先是花了上萬元在家裡安裝了隔音吊頂,又特地買了隔音墊送到鄰居家門口,稱是家裡用剩下多餘的,盡管鄰居拒絕了隔音墊,但傅嶽覺得對方的态度在好轉。
借着和物業一起巡樓的機會,傅嶽進到樓上鄰居家,發現鄰居在桌椅闆凳底下安裝了隔音墊,晚上十一點過後的噪音也逐漸消失。
2019年底,傅嶽開始在網上發布噪音科普的文章。傅嶽覺得,自己經曆了解決噪音的過程,可以在工作之餘将這些深受噪音困擾的人們聚集起來,共同讨論解決噪音的方法,他将自己公衆号的名稱改為了“中國反噪音聯盟”,希望更多人找到解決鄰裡噪音的辦法。
李林靜在一個偶然機會下進入了反噪音聯盟。她發現雖然群裡關于噪音的抱怨聲不斷,但關于噪音的解決辦法也開始變得多元。
按照群友們推薦的攻略,李林靜也嘗試了不同的方法。安裝隔音吊頂的方法并不适用于她的家,她解釋,自家樓上的噪音級别很重,若要完全隔掉噪音,需要非常厚的吊頂,“做好以後這個屋也沒法住人了。”李林靜決定和樓上鄰居再度溝通,說服鄰居花了一千元購買了減震墊,“但是效果并不好,而且墊子鋪了一兩年後,已經壓實了,現在是起不到任何效果的。”李林靜也嘗試給鄰居送過軟底拖鞋,效果仍舊不明顯。

安靜之家群聊内,群友在讨論降噪耳塞和耳機的降噪效果。網絡截圖
李林靜又嘗試和鄰居的6歲孩子成為朋友,趁着孩子在小區樓下玩耍時帶上玩具和孩子打成一片。這被李林靜稱作是最有效的方式:“他們的孩子和我們混熟以後,就會說‘樓下的叔叔阿姨,以後我們會輕點蹦’。”
居住在上海浦東新區的周敏(化名)也嘗試群友推薦的各種方式解決噪音問題。長期的噪音困擾下,周敏已經形成了一種心理:噪音沒有出現的時候,周敏開始等待噪音的到來。“有聲音的時候會非常煩躁、痛苦和恐懼,沒有聲音的時候,我卻在花所有時間等那個聲音到來,整個24小時都被噪音占據。”
周敏先是購買了最厚的耳罩,晚上躺在床上戴着耳罩睡覺,卻沒辦法翻身。後來又嘗試噪音脫敏治療,從網上下載了高跟鞋摩擦地面的各種聲音,每天躺在床上播放這些聲音嘗試脫敏,僅僅過了4天,周敏就再也無法忍受。
最後,周敏花了4萬塊錢,把自己房間的天花闆和牆敲開,在裡面填上了最厚的隔音棉、石膏闆和隔音層,過去頭頂上清晰的咚咚聲如今在多重阻隔下變成低悶的響聲。在周敏看來,噪音問題已經大大解決了。
鄭雲則在群友的鼓勵下選擇了鼓起勇氣反擊。
自認為性格軟弱的鄭雲,曾在與樓上鄰居調解噪音問題時送過雞、粽子,也送過各式各樣的零食,她希望能用友好溝通的方式解決噪音問題。但鄰居的我行我素,讓這一切成了徒勞。
鄭雲通過以最大音量播放電視節目的方式表達憤怒。“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也有人嘗試以暴力反擊噪音。傅嶽記得,2020年年初,一個25歲左右的男生因為反複和樓上租戶溝通無果,在群裡表達了自己要拿鐵棍上樓報複對方的想法。有不少群友在群裡勸解他,“哪怕深夜去敲門提醒,也不要以暴力的方式解決問題。”男生當時聽不進勸解,一度退群,冷靜下來以後又主動加入群聊。
傅嶽通過和男生私聊後,了解到男生在遭遇噪音問題時恰逢生活上也有諸多煩惱,情緒已經處于崩潰的臨界點,于是産生了極端的想法。在傅嶽給男生提供了幾條解決辦法後,男生通過和樓上房東溝通的方式,最終把噪音問題控制在了可接受範圍内。
2020年底,傅嶽将聯盟的名稱改成了“安靜之家”。他希望加入聯盟的人能夠理性維權,反對以暴制暴。“遇到有人想用暴力解決問題時,群裡都會有人勸解:犯不着去打架鬥毆,最後自己的生活反而被毀了,還要承擔刑事責任。”
安靜之家的群公告裡,列着幾項傅嶽制定的群聊公約:“可以吐槽抱怨,但是不要發布詛咒、侮辱視頻”、“不得宣傳暴力手段。”

2019年底開始,傅嶽在家裡的客廳和房間都搭建起了隔音吊頂。新京報記者 周思雅 攝
期待有法可依

記者查詢發現,近幾年關于噪音擾民的讨論越來越多。微博上一個名叫“樓上請停止你的噪音”的超話上如今有15萬粉絲,閱讀量達4192萬,該超話下的微博内容在抱怨鄰裡噪音問題時大多充滿着負面情緒。據媒體報道,2019年4月,青海一名男子因無法忍受樓上鄰居家的“噪音”,持刀沖入住戶家中,砍傷了四人,造成兩人重傷。2019年11月16日晚,鄭州一男子因鄰裡噪音糾紛殺害樓上三名女孩。
在裁判文書網檢索“鄰裡噪音”,結果顯示,從2015年至2021年由鄰裡噪音引發的案件共有31起,其中15起涉刑事案由,15起涉民事案由,1起為行政案由。31起案件中,6起涉及人身傷害賠償,2起涉及拘役,2起涉及防衛過當。而據生态環境部公布的數據顯示,據不完全統計,2020年,全國生态環境、公安、住房和城鄉建設等部門合計受理的環境噪聲投訴舉報事件約為201.8萬件,其中,社會生活噪聲投訴舉報最多,約108.3萬件,占53.7%。此外,2020年,“全國生态環境信訪投訴舉報管理平台”共接到公衆舉報44.1萬餘件,其中噪聲擾民問題占全部舉報的41.2%,僅次于大氣污染,位列第2。
據我國《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第六章第四十六條規定,使用家用電器、樂器或者進行其他家庭室内娛樂活動時,應當控制音量或者采取其他有效措施,避免對周圍居民造成環境噪聲污染。此外,據《民用建築隔聲設計規範》規定,對于住宅卧室、起居室允許的噪音級别為:卧室白天小于等于40分貝,夜晚小于等于30分貝;起居室全天小于等于40分貝。超過此标準即為建築隔音不達标。
傅嶽說,物權法中有對鄰裡關系需要和睦的一個定義,《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中也隻有應當避免對周圍居民造成環境噪聲污染的說法,但上述法規都沒有針對鄰裡噪聲如何判罰的定義。
傅嶽說,正是因為目前無法可依,在現實情況中,居委會、派出所等機構也常對噪音糾紛束手無策。而在訴訟層面,常常存在噪音取證困難的問題,無法直接證明噪音來源,大多數人不會選擇通過訴訟的方式解決問題。“在走到複雜的法律訴訟這一步之前,人們往往選擇搬家。”
蘇州一小區物業管理人員劉曉紅告訴記者,面對業主的噪音投訴,物業人員會通過上門調解的方式進行勸解,但僅限于口頭調解。除此之外,隻能依靠業主尋求如報警等方式處理。
傅嶽說,正因如此,他們對正在提請修改的《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充滿了期待。
據媒體報道,8月18日上午,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就噪聲污染防治法草案進行分組審議,人大委員們認為,随着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民群衆對“甯靜”生活環境的需要日益增長,但噪聲污染多發、多樣,日趨嚴重,噪聲污染防治法的修改回應了人民群衆的新要求新期待。
中國政法大學環境資源法研究所副所長胡靜參加了2021年《噪聲污染防治法(草案)》專家研讨會。他表示,研讨會對于近幾年投訴較多的鄰裡噪音問題有過專項讨論,而讨論的核心主要集中于鄰裡噪音在法律訴訟過程中的取證問題。
胡靜表示,新的噪聲污染防治法出台以後,可能會賦予物業、居委會等基層機構解決鄰裡噪音糾紛的權利和職責。“如果這個層面解決不了,可以尋求派出所民警進一步解決。
“在問題超出一般的糾紛後,公安機關不能因為沒有達到刑事案件的程度,就采取忽視的态度。鄰裡噪音問題裡有很多自然的隐患,公安機關應該及時出手制止。”
全國人大官網數據顯示,2021年,共有33項法律草案完成面向社會公衆征求意見,其中《噪聲污染防治法(草案)》意見條數排名第三,意見條數達到3068條。

現代城市裡密集的樓房,噪音成了城市生活的“副産品”。新京報記者 周思雅 攝
“在一切還沒有成熟前,隻能改變自己”

45歲的楚天(化名)遭受樓上鋼琴聲困擾長達15年。在他看來,鄰裡噪音也成為了現代社會城市運作的‘副産品’。而一些人在工作上付出了所有的精力,已經處于壓力的臨界值,在噪音的影響下,最後一根稻草也被壓垮了。“社會中間層普遍已經在工作中把自己推到邊界,達到效能的最大化,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很難接受計劃外的負面刺激。”
在楚天看來,噪音問題在短時間内無法被改變,由于每個人承受壓力的水平不等,如果從物理和心理層面都無法解決問題,唯一一個理性的出路就是選擇離開。“社會對于噪音的認知程度參差不齊,很多人沒有親身體會到這種噪音帶來的精神壓力,也就無法達到共情的程度。噪音這個問題不是所謂的‘小題大做’,隻是幾率問題。遇到之後,哪怕一個人沒有高壓的工作或是生活的其他壓力,他也可能會承受不起噪音帶來的傷害。”
這兩年,傅嶽持續在江蘇政協網站上提交關于噪音立法的提案,提案一度登上網站熱度的前三名。傅嶽說,雖然目前影響力還不大,但他會每年堅持做下去。
“我們想要一個安靜的家,但是為什麼看似這麼簡單一個要求,會變得這麼難?”傅嶽認為,“安靜”隻是一個樸素的生活追求,但是如今人們連這個追求都越來越難。噪聲污染防治法的修改還在草案階段,當前受噪音困擾的人們隻能依靠各種渠道忍受、反擊,“在一切還沒有成熟前,我們隻能改變自己。”傅嶽說。
2020年底,在樓上租戶搬走後,周敏的樓上新住進了一家三口。這一次,周敏選擇主動上門溝通,加了鄰居微信,平時在樓道裡遇到也會主動打聲招呼。
楚天則暗自下定決心,以後若要購買新房,一定要選擇頂層的房子。
李林靜和男友則計劃在一兩年内将房子出售,再購買一套二手房,“購買新房就像是買盲盒,你不知道會抽中怎樣的鄰居。二手房至少能在做決定之前知道樓上樓下住的是誰。”李林靜說,未來自己也會在裝修問題上更注意降噪處理,“家是一個放松的地方,不希望再過得這樣提心吊膽。”
11月19日這天,鄭雲依舊在早上五點醒來。這天早上和以往有些不同——鄭雲隻數到了七次噪音,聲音也比以往都要輕微。“一定是昨天用最高音量播放電視節目反擊他們的作用。”
下午五點,在咖啡館喝完一杯咖啡後,鄭雲打算提前回家。鄭雲說,自己已經半年沒心思逛超市,這兩天噪音輕了,“心情好多了,今晚回家前去買些好吃的。”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