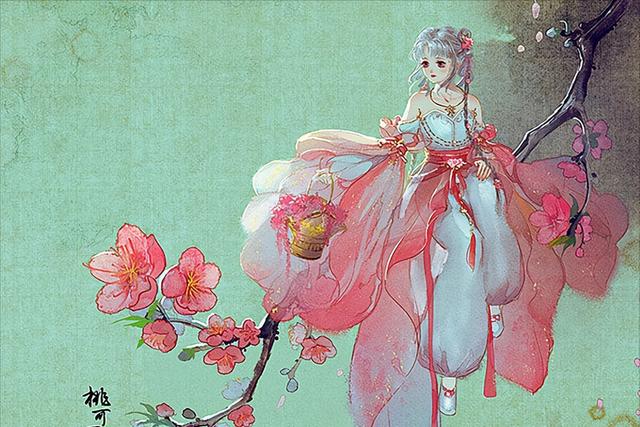一
蘇格拉底的“無知”是人類思想史上的一個經典議題。在柏拉圖的《蘇格拉底的申辯》(以下簡稱《申辯》)中,蘇格拉底以一種明确的口吻宣稱,他之所以被德爾菲的神欽點為“最智慧的人”,是因為他——相比那些自诩掌握了智慧,實則并不具有智慧的人——知道自己“不是智慧的” (Apol.21b)、“配不上智慧” (Apol.23b)等等。與此同時,在柏拉圖的另一些對話錄(尤其是所謂的早期對話錄)中,一方面,蘇格拉底在探讨許多具體問題時,多次表示自己陷入了“疑難” (Aporia),和他的對話夥伴一樣,也不知道真正的答案;另一方面,蘇格拉底在《會飲》、《斐德羅》等對話錄中多次宣稱,隻有神才握有智慧,而人是不可能掌握智慧的,隻能追求智慧。這些情況似乎也印證了蘇格拉底的那個自我評價。
雖然蘇格拉底從未把“無知” (agnoia,anepistemosyne,amathia)概念用在自己頭上,但一直以來,人們就把上述言論概括為蘇格拉底的“無知”,并且通過單純的字面意思來理解和贊揚蘇格拉底的“謙虛”美德。這仿佛表明,隻要我們像蘇格拉底一樣承認自己的“無知”,也可以跻身于“最智慧的人”之行列。然而在人們對此的一片贊美聲中,他們顯然沒有注意到這一明确的事實,即在古希臘人津津樂道的諸多美德中,什麼都提到了,但唯獨沒有提到“謙虛”。
近代以來,人們從對于那種“謙虛”的贊美出發,引伸出另外一些認識判斷,這些判斷尤其是和柏拉圖聯系在一起的。其中主要有如下兩種代表意見:(1)以沃納·菲特 (Warner Fite)、本傑明·法靈頓 (Benjamin Farrington)、卡爾·波普 (Karl Popper)、喬治·薩頓 (George Sarton)為代表的一些當代英美學者把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對立起來,指責柏拉圖“嚴重背叛”了自己的老師蘇格拉底,①因為柏拉圖在很多地方看起來并沒有那麼“謙虛”,不是坦然承認各種開放的可能性,而是野心勃勃地建立了一套把形而上學、自然科學、認識論、倫理學和政治學包攬無遺的體系。(2)近代的德國浪漫派(尤其是弗利德裡希·施萊格爾)把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等同起來,主張柏拉圖哲學的核心精神同樣也是以“無知”為旨歸,因此在柏拉圖那裡,同樣不存在對于終極問題的答案,不存在絕對意義上的真理,至多隻有對于智慧和真理的“無限趨近”。
我們看到,這兩種意見在對待柏拉圖的态度上正好相反。然而,它們在另一個問題上達成了一緻,即蘇格拉底(乃至柏拉圖)的“無知”的确是最高智慧的表現,是所有後世哲學家的榜樣。但在我們看來,他們對于“無知”的推崇仍然僅局限于字面上的意思,即對于真理“不具有知識”,而在這種情況下,“知道自己無知”隻不過是一種謙虛心态的表現而已,在内容上并不比“無知”包含更多的東西。我們承認,始終保持謙虛的心态無論對普通人還是對哲學家都具有重要的意義。然而在涉及客觀事實和真理時,過分強調“無知”毋甯說是一種虛僞的表現。畢竟我們都知道,總是把“知道自己無知”挂在嘴邊的人,和哲學中的“不可知論者”,和那些反對知識而推崇信仰的宗教信徒,幾乎隻有一步之遙。
筆者在三年前出版的《柏拉圖的本原學說》一書中,主要駁斥了上述第二種意見。(參見先剛,2014年,第191-222頁)筆者在那裡的主要觀點是,蘇格拉底和柏拉圖之所以強調自己的“無知”,辭讓“智慧”,其實是為了和那些智術師自诩的所謂的“智慧”劃清界限;反過來,從柏拉圖的口傳學說和那些包含着大量理論建樹的對話錄的實際表現來看,柏拉圖無疑認為自己掌握的“真知” (phronesis,episteme,gnosis)才是真正的“智慧”。就此而言,至少柏拉圖不像德國浪漫派曲解的那樣,隻願意追求真理和智慧,卻不能、甚至不願意掌握真理和智慧,毋甯說事實恰恰相反。
二
然而在《柏拉圖的本原學說》中,筆者對于這裡所說的第一種意見并未深入讨論。因此這是本篇論文的主要議題,即筆者希望進一步澄清蘇格拉底-柏拉圖的“無知”的哲學意蘊,同時希望表明,在知識問題上,所謂的蘇格拉底式“謙虛”和柏拉圖式“僭越”之間的對立壓根就是莫須有的。就後一個問題而言,那個捏造出來的對立從一開始就忽略了如下一些情況:(1)那個“謙虛的”蘇格拉底形象根本就是出自柏拉圖的手筆,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其實是柏拉圖本人學說的一種表現。②既然如此,柏拉圖怎可能自己“背叛”自己,自己“僭越”自己呢?(2)在柏拉圖的另一些對話錄中,蘇格拉底并不“謙虛”,而是以一種正面積極的方式提出了一套涉及方方面面的完整學說——針對這種現象,人們把其中的“蘇格拉底”自動切換為一個“僭越式的柏拉圖”或“獨斷的柏拉圖”,認為這些是柏拉圖本人的觀點,不應算在蘇格拉底的頭上。③問題在于,這裡的“蘇格拉底”和前面那個“蘇格拉底”憑什麼可以區分開來呢?(3)無論是蘇格拉底還是柏拉圖,明明比任何人都更強調“知識”的極端重要性,甚至提出“美德就是知識” (Men.87d)這樣的命題。他們反複拒斥“無知”,甚至明确将其斥之為“最大的惡”(Tim.88a-b)、“萬惡的根源” (Epist.VII 336b)、“最醜陋的東西” (Alki.I 296a),而這些言論怎麼能夠和對于“無知”的推崇結合在一起呢?
這些疑問促使我們全面而深入地考察蘇格拉底“無知”的真正意義。這裡的關鍵問題是,無論怎樣,人們不應按字面意思來随意接納蘇格拉底“無知”的概念,而應在這個概念出現時的語境中來考察其真正的含義。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首先從《申辯》出發,考察蘇格拉底大談“無知”的具體語境。這裡首先需要注意的是,當蘇格拉底得知神谕宣稱他為“最智慧的人”時,他并未否定這個神谕的真實性 (“神是無論如何不會撒謊的”,Aopl. 21b),而是不明白這個斷言的理由(“很長一段時間我都不理解,那個神谕是什麼意思”,ibid.)。因此他試圖通過與一些所謂的“智慧之人”的交流來探尋那個理由。具體說來,有如下三個步驟:(1)首先通過和政客的交流,蘇格拉底發現,他們最大的特點是“自認為自己是很智慧的,但實際上根本不是如此。” (Apol. 21c)“這些最有名望的人在我看來幾乎是一些最可憐的人。” (Apol. 22a)這類人是對于智慧完全“一無所知”的人。(2)随後在和詩人的交流中,蘇格拉底發現,他們雖然也說了很多真理,然而他們自身卻不理解這些真理;他們和預言家、神谕頒布者一樣,能說出很多美好的東西,卻不理解自己說的那些東西。(cf.Apol. 22b-c)這類人已經“具有”了某種程度的智慧,但并未真正“掌握”它們。(3)接下來是和工匠的交流,這些人确有一技之長,知道很多東西(這裡指他們在其專業領域中不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因此在這些領域中确實是“智慧的”,比詩人又勝一籌)。問題在于,工匠雖然在各自的專業領域中是智慧的,卻認為自己在“其他最重要的事物”上也是智慧的,其實他們對此仍舊一無所知,因此“他們的這個愚蠢就抹煞了他們的那個智慧”。(Apol. 21c-22e)通過這些檢驗,蘇格拉底發現德爾菲之神所言不虛,最重要的是,他明白了這一神谕的理由,即他和那些自認為有智慧,實際卻知之甚少或一無所知的人相比,至少是知道自己并不具有智慧,知道自己是無知的。
到此為止,我們和那些推崇“無知”的人看上去并無分歧。但筆者想提出兩個問題:第一,究竟關于什麼東西,政客、詩人和工匠是無知的?第二,蘇格拉底依據什麼斷定他們是無知的?很顯然,當一個人宣稱别人對于某件事是“無知”的時候,如果這是一個符合事實的判斷,那麼前者必定已經掌握了後者不具有的相關知識。因此這裡的關鍵主要不在于蘇格拉底比那些人“謙虛”,更重要的是,他确實具有他們所不具有的知識,惟其如此,他才能揭示出對方的“無知”。反之,假若蘇格拉底本身就是一個對于相關對象一無所知的人,即使他可以謙虛地承認自己“無知”,但他有什麼權利宣稱别人在這個問題上同樣也是“無知的”呢?或者說,如果我們承認蘇格拉底對于那些人的批判是切中要害的,那麼我們必須也承認,蘇格拉底并不是真的“無知”,毋甯說,就他們進行過談論的那些對象而言,蘇格拉底實際上一定是具有知識的——至于他的這些知識是否配得上“智慧”的榮譽,這是另外一個議題。無論如何,我們切不可忘記神谕授予蘇格拉底的“最智慧的人”這一頭銜的正面意義,因為如若不然,神谕為什麼不直截了當地宣布蘇格拉底是“最謙虛的人”呢?
那麼,蘇格拉底具有的是什麼知識呢?我們可以推測,當蘇格拉底和政客讨論“公正”,和詩人讨論“神性”,和工匠讨論“技藝”時,必然已具有了相關對象的正确知識。關鍵在于,他必須不僅具有相關知識,還需揭示那些人的“無知”,指出他們的錯處,進而指出他們知識的局限性或界限。這就是說,在進行相關讨論時,蘇格拉底一方面以自己的“知識”為對象,另一方面以對方的“無知”為對象,他的知識是一種同時把“知識”和“無知”包攬在自身之内的知識。推而言之,如果蘇格拉底認識到自己的“無知”,那麼他必定已經具有一種更高層面上的知識,惟其如此,他的那句斷言,“知道自己不是智慧的”,才會具有一種哲學上的價值,而不是僅僅反映出一種廉價的“謙虛”心态(這是我們反複強調予以拒斥的東西)。認識到這一點之後,我們立即就會注意到,在蘇格拉底-柏拉圖那裡,這種同時以“知識”和“無知”為對象的知識,不是别的,正是“明智”。
三
在對“明智” (sophrosyne)概念進行更深入的分析之前,筆者準備提及一個值得注意的情況,即在這裡被解釋為一種“知識”的“sophrosyne”,在柏拉圖的某些著作(比如《理想國》和《高爾吉亞》)中,通常被翻譯為“節制”,而“節制”的含義就是“自己控制自己”或“控制欲望”。(vgl.Rep. 430d;Gorg. 491d,492a-b)不僅如此,後來的亞裡士多德主要也是在“節制”的意義上讨論 “sophrosyne”。(Eth.Nic. 1117b23-1119 b18)首先,我們把“sophrosyne”理解并翻譯為“明智”,這是有充分的柏拉圖文本根據的(接下來将詳談)。那麼現在的問題是,“明智”和“節制”究竟是什麼關系?簡單地說同一概念具有兩層含義,這無疑是一種隔靴搔癢的做法。在筆者看來,其實很顯然,如果一個人沒有獲得關于自己的知識(即“明智”),沒有做到“自己認識自己”,那麼“自己控制自己”也無從談起。就此而言,所謂的“節制”隻不過是“明智”衆多表現之一而已。更何況亞裡士多德也已經指出,他所說的“節制”和通常所說的“知識” (phronesis)具有一種内在的“ sophrosyne 這個詞的意思就是保持 phronesis,sophrosyne 所保持的是 phronesis 的觀點。” ( Eth.Nic. 1140 b11)也就是說,“明智”已經把“節制”統攝在自身内,任何關于“節制”的讨論都已經預設其在本質上是一種知識,這兩個概念并無矛盾之處。
回到正題。在筆者看來,“明智”的發現為我們切實地理解把握蘇格拉底“無知”的真正意義提供了一條關鍵的線索。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從《申辯》轉向柏拉圖的另外一些對話錄,轉向其中關于“明智”的讨論。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阿爾基比亞德》中,在把“靈魂”界定為每一個人真正的“自己”之後,蘇格拉底提出了對于這個“自己”的認識亦即“自我認識”的重要性。蘇格拉底首先指出,醫生、運動員、農夫、工匠等有一技之長的人并不能憑借他們各種掌握的技藝來認識自己——注意這裡和《申辯》中對于工匠的批評的聯系——,然後給“明智”提出了一個定義;“明智就是認識自己(sophrosyne esti to heauton gignoskein)。” (Alki.I 131b)這個定義并非随意提出,因為蘇格拉底在随後的地方再次強調:“我們都承認,認識自己就是明智。” (Alki.I 133c)如果我們把這個定義和德爾菲神廟的另一個著名的神谕“認識你自己 (gnoti se auton)”聯系起來,再和那個宣稱蘇格拉底為“最智慧的人”的神谕聯系起來,很容易就會看出,這其實是宣稱蘇格拉底是“最明智的人”。這就說明,“知道自己無知”必定應當從“明智”出發來理解。
當然,《大阿爾基比亞德》僅僅強調了“自我認識”或“明智”的重要性,指出:“如果我們缺乏自我認識,不是明智的,就不可能知道,什麼東西對我們是好的,什麼東西對我們是壞的。” (Alki.I 133c)蘇格拉底在那裡進而宣稱,如果一個人缺乏自我認識,他也不可能真正認識自己所做的事情;如果一個人不理解自己所做的事情,同理他也不可能理解别人所做的事情,而這樣的人,絕不可能成為一名“政治家”。(Alki.I 133d-e)——如果我們把這些言辭和《申辯》中對于政客的批判聯系在一起,就會發現,政客們之所以是無知的,歸根到底在于缺乏一種“明智”。
在柏拉圖所有的對話錄裡,讨論“明智”最多的無疑是《夏米德》,其副标題就是“論明智”。和其他早期對話錄一樣,它也是選取一種美德作為讨論對象。同樣,在對話過程中,那些初步提出的規定逐一被抛棄,最終形成一個相對明确的答案。蘇格拉底在這部對話錄中主要有兩個對話夥伴:夏米德及其舅舅克裡提亞。他在前半階段和夏米德的讨論主要起到一種鋪墊作用,在這個階段,夏米德的那些觀點,比如“明智就是瞻前顧後” (Charm.159b)、“明智是一種羞恥感” (Charm.160e)、“明智就是每個人做他自己的事情” (Charm.161b)等等,被依次驗證為是無效的。轉折點出現在另一個對話夥伴克裡提亞的介入,他接着夏米德的最後一個定義,以一種更明确的方式提出“明智就是做好的事情(即把事情做好)”。(Charm.163e)而蘇格拉底對此的質問是,工匠和藝術家都能做好其本職工作,因此是在“做好的事情”,既然如此,他們是否有資格被稱為“明智的”呢?(這裡仍請大家注意和《申辯》中對于詩人和工匠的批評的聯系!)當然,克裡提亞對于這個問題的答複是肯定的,但更重要的是,他在這裡進而提出,“明智”就是德爾菲神廟裡提出的“認識你自己”。(Charm.164d)這個定義和《大阿爾基比亞德》中的說法完全一緻。在這裡,克裡提亞不僅提出“認識你自己”和“你要明智”是相同的意思,更認為德爾菲神廟的其他神谕,比如“勿過度”和“誰作擔保,誰就遭殃”,也是在強調“明智”的重要性。(cf.Charm.164e-165a)
由此可見,在“明智”問題上,《夏米德》是《大阿爾基比亞德》的深化和發展,同時二者都是間接地在闡發《申辯》中蘇格拉底的“最智慧”和“知道自己無知”的真正含義。按理說,這個如此重要的觀點應該由蘇格拉底本人提出,而不是讓克裡提亞提出,因為按柏拉圖對話錄通常的探讨方式,由對方提出的觀點都會遭到反駁或糾正。④果不其然,蘇格拉底立即發出了提問:如果“明智”是一種知識,它的對象是什麼呢?(看起來蘇格拉底并不認為“自己”或“自我”是嚴格意義上的認識對象)醫術以健康為對象,建築術以房屋為對象,紡織術以衣服為對象,這些知識都會帶來用處,産生成果 (ergon),既然如此,作為“自我認識”的“明智”能夠帶來什麼美好的成果呢?(cf.Charm. 165d-e)克裡提亞辯護道,“明智”這種知識就其本性而言和所有别的知識都不一樣,也就是說,“所有别的知識都是以一個‘他者’為對象,但唯有‘明智’是既以其他知識為對象,也以它自己為對象。” (Charm.166c,166e)沿着這一思路,蘇格拉底主動出擊,将克裡提亞帶入另一個觀點,即“明智”不僅以知識為對象,甚至以“無知” (anepistemosynes )為對象,也就是說:“唯有一個明智的人既能夠認識自己,也能夠探究他真正知道的東西和他不知道的東西;同樣,唯有他能夠對其他人作出評價,指出一個人在知道某個東西并且認為自己知道某個東西的時候,确實知道這個東西,或者一個人在以為自己知道某個東西的時候,其實不知道這個東西。” (Charm.166e-167a)這裡已經明确告訴我們,無論是“知道别人無知”,還是“知道自己無知”,都是一個“明智的人”的專利,而這顯然是《申辯》中的蘇格拉底在考察自己和别人的智慧時的表現!至于他所批評的那三類人,與其說是“無知的”,不如更确切地說是“缺乏明智的”。
通過自己主動介入和替對方作答,蘇格拉底在這裡實際接管了問題的導向,而在柏拉圖的對話錄中,通常說來,這是涉及到重要議題的标志之一。前面已經表明,“明智”是一種三重性的知識:(1)對自己的知識,(2)對别的知識的知識,(3)對無知的知識。(cf.Charm.167b-c)正如我們看到的,這種知識是如此獨特,确實不同于所有别的普通知識。尤其是在“自我認識”這個問題上,存在着許多困難。比如,按蘇格拉底列舉的例子,任何“看”或“聽”,作為一種知識,都是以一個他者為對象,反過來,對于“看”的“看”或對于“聽”的“聽”怎麼可能呢?推而言之,諸如欲望、愛、畏懼、想象也是如此,欲望以一個東西(比如美食)為對象,不可能以欲望自身為對象,否則,還會有對于“欲望的欲望”的欲望,如此以至無窮。
如果我們熟悉近代以來的哲學思維方式,就不難發現,這是所謂的“反思的無窮倒退”,而這裡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自我意識”或“自我”問題:“我”以“我”為對象,但“我”還可以以前面的那個“我”為對象,如此以至無窮,“我”始終不能建立起來。當然,近代哲學有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那就是拒絕自我意識的“反思模式”,轉而把“自我”理解為一種主客同一的理智直觀,理解為一種“純粹的”(亦即超越意識的或無意識的)意識。實際上,近代哲學面臨的“自我意識”問題和這裡所說的“自我認識”問題并無二緻,唯一的差别在于,蘇格拉底-柏拉圖尚未像後世那樣強調“自我”的極端的根本地位。也就是說,蘇格拉底-柏拉圖自己實際上将這個無比棘手的問題抛給了克裡提亞,而很自然地,克裡提亞對此啞口無言。為了給克裡提亞一個台階,蘇格拉底說道:“好吧,假若你是正确的,我們目前姑且承認,可能真的存在着這樣一種‘對于知識的知識’ (episteme epistemes),至于事情是否真的如此,我們不妨改天再來研究。” (Charm.169d)在柏拉圖的對話錄中,這是一種常見的“中斷讨論”的現象。對于這種現象,圖賓根學派的諸位學者認為,柏拉圖并不是不知道問題的解決辦法,也不是不能對此展開深入讨論,隻不過鑒于問題本身的難度以及對話夥伴的理解力,他甯願在其他場合(尤其是學園内部)親自講授這些學說,而不是在當前的這部對話錄中勉為其難地加以闡述。當然,就這個可能導緻“無窮倒退”的特定問題而言,無論是在關于柏拉圖口傳學說的記載裡,還是在柏拉圖的其他對話錄裡,我們都沒有找到、也不可能找到一個類似于近代哲學的解決辦法。但這并不意味着蘇格拉底-柏拉圖沒有其他解決辦法,而正如我們将會看到的,柏拉圖把這個意義上的“明智”導向了一種總體性的辯證知識。
由此蘇格拉底過渡到一個重要的問題:“一個具有自我認識的人,是否必然也知道,他知道什麼東西,以及他不知道什麼東西?” (Charm.169e)對于這個問題,克裡提亞輕易地給出了一個肯定的答複。但蘇格拉底提醒他注意,醫生具有關于健康的知識,是通過醫術,不是通過他的自我認識,音樂家具有關于諧音的知識,是通過樂理,不是通過他的自我認識,同樣,政治家具有關于公正的知識,是通過政治技藝,也不是通過他的自我認識。看起來,首先,自我認識或“明智”并沒有幫助人們獲得具體的知識。其次,他在評判人們“知道什麼和不知道什麼”的時候,自己也不知道那個“什麼東西”,而是僅僅知道“這件事情”:人們知道一些東西,或者人們不知道一些東西。(cf.Charm.170d)在這種情況下,自我認識或“明智”仿佛隻是一種空洞的知識,甚至不能和醫術之類的知識相提并論,因為醫生至少是同時知道“健康”和“不健康”,能夠區分誰是這方面有知識的人,誰是這方面無知的人,而這對一個“明智的人”來說卻是不可能的。(cf.Charm.171c)
這個困難導緻“明智”遭到質疑,即它對我們而言究竟有什麼用處?一個明智的人知道,自己知道什麼,不知道什麼,知道自己的“知識”,也知道自己的“無知”,除此之外,他還能評價别人的“知識”或“無知”。然而落實到具體事務上,比如在家庭事務和國家事務上,這種意義上的“明智”并不能如醫術、航海術、制衣術等等那樣給我們帶來任何具體的幫助。這些疑慮給我們造成了一個印象,仿佛蘇格拉底要把“明智”作為某種“完全無用的東西”加以抛棄。但這裡我們不能忽視一個關鍵因素,那就是,蘇格拉底真正要拒斥的,是那種流于形式的或空洞的“明智”,這種“明智”僅僅知道自己或他人的“知識”和“無知”,而對于具體的知識對象,即那個“什麼東西”,卻不具有知識。其實通過這一反思,蘇格拉底無疑已經告訴我們,單純的“知道自己無知”(即人們通常所謂的“謙虛”),根本就是一種無用的東西,或僅僅是一種具有初級用處的東西。⑤但相比之下,真正重要的還是應當掌握對于具體對象的知識,惟其如此,“明智”(即對自己和别人的“知識”或“無知”作出評判)才是一種有根有據的、令人信服的東西。也就是說,蘇格拉底之所以推崇“自我認識”或“明智”,絕不是希望人們簡單承認自己的“無知”,而是鼓勵人們積極地去追求真正的知識,并在這個過程中提升到“通觀” (synopsis)的高度,達到一種實質意義上的“明智”。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蘇格拉底提出了一種“最有用的知識”,即“與善和惡相關的知識”或“對于善和惡的認識”,并把它與那種單純的、無用的“對于知識和無知的知識”區分開來。他在這裡并沒有進一步闡釋“對于善和惡的認識”具體是怎樣一種知識,因為真正的重點在于,“善和惡”代表着一般意義上的對立(即是說我們也可以把它切換為“健康和疾病”、“對和錯”、“美和醜”、“悲劇和喜劇”等等),因此這是一種具有實質對象的、并且同時把相互對立的兩個方面包攬在一起的知識,即一種整全性的辯證知識,(關于柏拉圖辯證法的本質規定和具體特征詳見先剛,2013年)而這才是真正的“明智”。⑥雖然這部對話錄在結尾處看起來也陷入了“疑難”,但如果我們理解了上述分析,就能領會到,蘇格拉底-柏拉圖實際上已經給出了一個解決問題的方向,即我們應當在“明智”的指引下追求一種實質性的、整全性的知識。這樣我們也會發現,蘇格拉底在這部對話錄的開始就給予我們足夠的暗示。因為夏米德受困于“頭疼”的病症,而蘇格拉底告訴他,真正的好醫生(指著名的希波克拉底)一定是采取一種整全性治療方法,即并不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毋甯說,如果一個人眼睛生病,醫生必須看他的頭,如果一個人的頭有病,那麼必須看他的整個身體,因為治療是指向全身的,一旦治療了整體,自然就治療了部分。在這裡,蘇格拉底更托借色雷斯國王查莫希斯 (Zamolxis)之口發揮出這樣的觀點:“要治療眼睛,不能不管頭;要治療頭,不能不管整個身體;要治療身體,不能不管靈魂。” (Charm.156b-e)靈魂所患的最大疾病,就是“無知”,所以相應的治療方法,就是通過辯證交談讓靈魂裡産生出“明智”。而正如我們反複強調的,蘇格拉底心目中真正的“明智”不是簡單地“知道自己的無知”,而是要掌握一種整全性的知識。
四
迄今的論述表明,《申辯》是以一種隐晦的方式指出“知道自己的無知”是“明智”的一種表現,而《大阿爾基比亞德》和《夏米德》則明确地把“自我認識”等同于“明智”。除了這幾部對話錄之外,柏拉圖談論“明智”最多的地方,是在《理想國》裡面,其中,“明智”和“勇敢”“智慧”“公正”并列為一個城邦最重要的四種美德。相對而言,對于“明智”的讨論明顯少于另外三種美德,仿佛它在這裡居于次要地位,但這種理解是錯誤的。對于這一問題,筆者已論述過,沒有“明智”,“公正”就不會得以實現,因此前者是後者的直接前提。(參見先剛,2014年,第392頁)原因在于,雖然“公正”意味着“各司其職”,但人們憑什麼就要做公正的人,心甘情願地做自己的事,而不去插足應當由别人來做的事呢?除非他已經知道,什麼是他自己的事,什麼是别人的事。
就此而言,“公正”和“明智”關系尤為密切。此前筆者已提醒大家,《夏米德》曾把“明智”定義為“每個人做他自己的事情” (Charm.161b),而這恰恰是《理想國》對于“公正”的定義 (Rep.433d)。在筆者看來,這并非柏拉圖疏忽大意,正相反,他這個表面上看起來的“混淆”實則确證了“明智”與“公正”的内在聯系。在《蒂邁歐》裡,柏拉圖已明确指出:“自古以來,人們就正确地宣稱,唯有一個明智的人才會做他應做的事情,并且認識他自己。” (Tim.72a)而在《普羅泰戈拉》和《會飲》裡,我們看到柏拉圖已經有這樣的思想,即“明智”取決于知識,而“公正”又取決于“明智”。(cf.Prot.332a-334c;cf.Symp.209a)此外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節制”與“明智”之間也具有一種内在的聯系。誠然,按照《理想國》的說法,“明智”(“節制”)美德主要是對于代表着欲望的勞動階層和商人階層提出的要求(因為這些人最容易失去自我控制,僭越自己的本分),但這并不意味着軍人階層和國家護衛者階層就不需要具有這種美德,因為他們同樣有可能做出越界的事情。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柏拉圖明确指出:“‘明智’(‘節制’)貫穿全體公民,把最強的、最弱的和中間的(不管是指智慧方面,還是指力量方面,或者還是指人數方面、财富方面,或其他諸如此類的方面)都結合起來,造成和諧,就像貫穿整個音階,把各種強弱的音符結合起來,産生出一首和諧的交響樂一樣。” (Rep.432a)和“勇敢”專屬于軍人階層,“智慧”專屬于國家護衛者不同,“明智”和“公正”是全體公民都應當具有的美德,因而占據着一個甚至比“智慧”更高的地位,而它之所以能夠占據這個地位,就在于它在本質上是這樣一種整全性的知識:既是對于具體對象的知識,同時也是對于自己和别人的“知識”(能力)和“無知”(界限)的知識。
由此可見,蘇格拉底的“無知”根本不是一種以“不具有知識”為旨歸的“謙虛”心态的表現,而是一種作為整全性知識的“明智”的必然結果。如果我們要贊美蘇格拉底的“無知”,就必須把這種意義上的“明智”當作自己的追求目标,這才是蘇格拉底-柏拉圖的教誨的真正目的。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