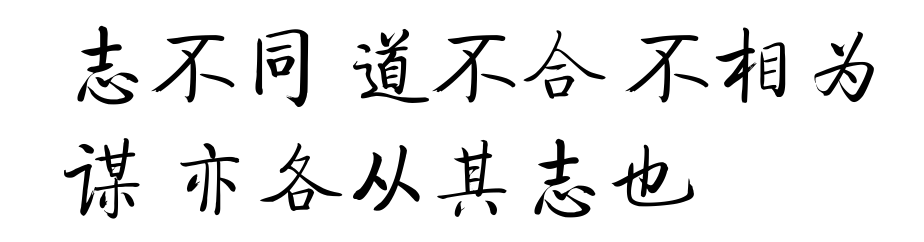作者前言
近幾年來,“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或Deeper Learning)在國内暴得大名,無論是理論界還是實踐界都對此趨之若鹜,許多學者對此有過論述,幾乎所有一線教師都非常關心這一論題。就國内研究而言,短短五年(2013.01—2018.06)就有論文500篇之多。然而,我們不無遺憾地看到,絕大多數理論及實踐成果都有一種“單向度取向”,即主要是基于學習心理學認知學派的“信息加工”理論而展開的研究成果,鮮有“全視角”觀照;其中國内研究多數又以“譯介”為主,實證成果稀少。不可否認,基于“信息加工”的心理學層面上的探索必不可少,它的确可以切入深度學習的内在機理。但是,如果始終停留在“信息加工”層面是無濟于事的,而且很容易出現價值取向上的重大偏差。因此,我們應當超越認知學派,轉向“全視角”或“全域理論”,對深度學習再做一番厘清。

本文選自《課程·教材·教法》2019年第2期。作者吳永軍系南京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導師,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南京師範大學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教材專家工作委員會委員。
一
對當前深度學習研究的檢視
對于“深度學習”研究的檢視,我們拟從兩個方面來展開:一是考察深度學習研究的“譜系”,二是揭示深度學習的認識誤區及其背後的原因。
學術界基本達成這樣的共識:深度學習緣起兩方面研究——計算機領域中的“機器學習”(或“人工智能”)研究以及教育領域中的學習研究。相對于教育領域,計算機領域的機器學習對于深度學習更為廣泛,影響也更為深遠,這方面的海量研究最終積澱為後續研究與生俱來的基因——大腦内部極為複雜的信息加工。據研究,最早搶注“深度學習”概念的是機器學習領域,對機器學習進行研究,實質上是對人的意識、思維和信息過程的模拟,是一門人工智能的科學,而深度學習是機器學習中表征學習方法的一類。在機器學習中,深度學習被定義為“一系列試圖使用多重非線性變換對數據進行多層抽象的算法”。機器學習算法是一類從數據中自動分析獲得規律,并利用規律對未知數據進行預測的算法。
教育領域中的深度學習研究關注點是在學習科學視域下展開的。目前比較公認的是,國外教育領域中的“深度學習”概念最早由來自瑞典歌特堡大學的馬頓(Marton)和薩喬(Säljö)提出,他們在1976年研究大學生在進行大量散文閱讀任務時,所表現出的不同學習過程和使用的學習策略以及理解和記憶的差異化學習結果時發現,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處理信息存在不同水平,呈現淺層和深層的差異。當學生使用淺層學習策略時,隻能獲得對問題的淺表回答,學習過程表現為機械的死記硬背。當學生使用深層學習策略時,則能關注到文章主題和主要觀點。兩位學者由此提出了“深度學習”概念,指出深度學習是一個知識的遷移過程,有助于學習者提高解決問題并做出決策的能力。
此後,許多學者紛紛加入深度學習的研究行列中,其中比較著名的有澳大利亞學者比格斯(Biggs)與柯利斯(Collis)于1982年基于皮亞傑的認知發展階段理論,提出的SOLO分類法(Structure of the Observed Learning Outcome,簡稱SOLO),依據學習結果的複雜性進行分類,分别為學習結果的前結構水平(Prestructural)、單一結構水平(Unistructural)、多層結構水平(Multistructural)、相關結構水平(Relational)和拓展抽象水平(Extended Abstract)五個層次。
進入21世紀,2006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欣頓(Hinton)教授和他的學生薩拉赫丁諾夫(Salakhutdinov)在《科學》上發表了一篇關于深度學習的文章,開啟了21世紀深度學習在學術界的熱潮。而由美國威廉和弗洛拉·休利特基金會(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發起,美國研究院(AIR:American Institutes for Research)組織實施的SDL項目(Study of Deeper Learning:Opportunities and Outcomes),則在全美建立了500餘所深度學習實驗學校。SDL項目在理論建樹與實踐普及方面都具有劃時代意義。在筆者看來,這一劃時代意義在于SDL項目突破了傳統深度學習限于“信息加工”的窠臼,無論是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NRC)的深度學習能力三維度劃分(認知領域、人際領域、個人領域),還是SDL項目所界定的深度學習的六維度能力(掌握核心學科知識、批判性思維和複雜問題解決、團隊協作、有效溝通、學會學習、學習毅力),都充分考慮了社會文化因素,具有了“全視角”特性,是一種比較完整的關于深度學習的理解。
正因為深度學習研究與生俱來的“基因”的型塑,我國早期研究深度學習(2005年)以及近幾年來異常活躍的學者,其學術背景絕大多數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純粹的教育學者,而是“教育技術學”領域學者,如被認為是引進“深度學習”概念的黎加厚教授就是教育技術(信息技術)方面的研究專家。而在2013年以後深度學習研究風起雲湧态勢下,比較活躍的一些學者如祝智庭、董玉琦、張寶輝、張浩、吳秀娟等都是教育技術領域有影響的學者。而刊發深度學習一些重要論文的刊物也以“教育技術”類雜志為主,如《中國電化教育》《遠程教育雜志》《中國遠程教育》《電化教育研究》等。
上述研究至少存在三個問題。一是對于深度學習的認識,偏于心理學認知學派的“信息加工”理論,尤其是試圖以人工智能、機器學習研究所得成果來反觀人類學習,從某種角度講,這種學習觀是沒有“價值取向”的學習觀,是沒有“靈魂”的學習觀。
深度學習對于“學習”的理解還是比較狹隘與局限的,更多的是以信息加工理論來揭示“認知”方面的心理過程機制,而價值、情感、态度以及精神領域的學習被有意無意地忽視,這其實是典型的認知學派的基因使然。深度學習的學習之所以被稱為“深度”,在于研究者們有這樣的認識:早在20世紀80年代,認知科學家從深度學習與淺層學習的“關鍵區别”中發現:當學習者運用“深度”學習方式時,不僅能獲得知識,而且清楚知道在真實世界和實際情況中如何運用這些知識,這樣的知識會在學習者頭腦中保持得更為持久。而死記硬背和簡單記憶對個人的知識建構的作用隻是淺表的、易忘的,這是淺層學習。也就是說,深度學習之“深度”的最重要表征是:應當能夠使知識保持長久,并能運用。而要做到這些,學習者必須把握知識之間的有機聯系,在頭腦中建立知識之間的有機聯系,即使知識結構化,而不是碎片化、孤立化地保有知識。從這個意義上說,深度學習理論其實是對美國心理學家、認知學派代表人物奧蘇貝爾的“有意義學習”理論的繼承與發展,或曰“有意義學習”的升級版或擴展闆。簡言之,深度學習就是學習者在理解的基礎上,把握知識間的有機聯系,旨在做出決策或解決問題的學習。
實際上,在早期研究中,大多數研究者認為深度學習是相對于淺層學習的一種知識加工方式(或者說是一種學習方式)。比格斯認為,深度學習包含高水平或者主動的認知加工,對應的淺層學習則采用低水平認知加工,比如,簡單記憶或者機械記憶。我國學者黎加厚等認為,深度學習是指在理解的基礎上,學習者能夠批判地學習新思想和事實,并将它們融入原有的認知結構中,能夠在衆多思想間進行聯系,并能夠将已有的知識遷移到新的情境中,做出決策和解決問題的學習。且不說這一定義幾乎是西方學者定義的雜糅與翻版,如比蒂(Beattie)、柯林斯等認為,深度學習方式意味着學生為了理解而學習,主要表現為對學習内容的批判性理解,強調和先前知識與經驗連接,注重邏輯關系和結論的證據。就其對于學習的本質認識而言,是經典的認知學派的信息加工理論的體現,後續的一些研究對于深度學習的認識幾乎沿用了這一定義(也有少數教育學者如郭華教授等具有比較廣闊的視野)。
更加令人擔心的是,大量從人工智能、機器學習視角來比照或反觀人的學習的研究成果,更是一種“單向度”學習觀的體現,在價值取向上出現嚴重偏差。本來人工智能、機器學習等方面的研究是“機器”模仿“人類”學習,現在反過來将“機器的學習”簡單移植到人的學習中,要求人要像機器一樣學習,變成“機器化的人的學習”,這絕不是“人的深度學習”,而是“機器人的深度學習”。這種簡單比附及移用的做法背後反映了對“人的學習”與“機器學習”的根本看法的殊異。的确,人工智能、機器學習在模仿人的學習上取得了許多重要成果,但是人工智能與人在學習上具有本質區别。這種區别主要表現在:人工智能與人雖然都具有理性思維能力(思考有限的、邏輯的、程序化的、必然的事情),但人還具有人性,具有情感、價值、精神、意義、靈魂等,還具有超理性能力,即具有思考整體性、無限性和不确定性的能力,尤其是變通能力和創造力。“真正的創造力并不能還原為自由組合和聯想,而在于能夠提出新問題,或者改變舊問題,改變既有思路,重新建立規則和方法……而要能夠提出新問題或者改變規則,就需要能夠反思事物的‘整體’或者‘根基’的思維能力,或者說,需要有一種‘世界觀’或者改變給定的世界觀……人工智能顯然不具備思考世界或系統整體的能力……(它)隻能思考有限的、程序化的、必然的事情,卻不可能思考無限性、整體性和不确定性。”
進一步來講,如果我們從“信息加工”理論視野下的深度學習以及人工智能中的深度學習背後的“形而上學”基礎來看,這是一種典型的“工具理性”,尤其是“技術理性”的哲學觀。誠然,理性思維是人區别于動物的最主要的特征,但是“理性思維實非人類之特異功能,而是一切智能的通用功能(人工智能就具有這種特異功能),以理性去定義人類是一個自戀錯誤。人類思維的真正特異功能是超理性的反思能力——反思能力不是理性的一部分,相反,反思能力包含理性而大于理性。反思首先表現為整體思維能力,尤其是把思維自身包含在内的整體思維能力”,而且人類還具有大量非理性特質,如精神、道德、價值、情感、自由等,正是因為有了這些非理性特質,人類生活才充滿意義和價值。因此,這種基于對技術理性的崇拜導緻的教育的工具主義傾向,把制度、計劃、秩序、組織形式等視為學習的法寶,而把“人類精神”,尤其是人的自由踐踏到無以複加的程度。這樣的學習觀培養出來的人隻能是“單向度的人”或具有“平庸之惡”的“巨嬰”。
二是對于深度學習所發生的“情境”做了相對簡化與孤立化,這一情境不是真實的學校學習,尤其是課堂學習所歸屬的情境,這實際上簡化了人類複雜的真實學習,尤其是學校情境下的中小學的課堂學習。
我們注意到馬頓與薩喬的經典研究是在“測試”(考試)情境下進行的(即在讓兩組大學生閱讀完相關内容後作答試卷),包括比格斯在内的後續許多學者的研究基本都是這樣(這也是認知心理學派的基因),而且以大學生樣本為主。這種“測試情境”是相對孤立的、靜态的、簡化的,從方法論角度講還是“個人主義方法論”,即學習者是“個體”狀态下的學習,是“去情境化”的學習,以“個體”作為最終解釋依據,缺乏真實學習情境中讨論、交流等人際互動,以及特定社會文化的制約,更沒有“學習共同體”的介入,完全不同于真實的學校或課堂學習。人工智能對于深度學習研究的情境也是一樣,是對真實學習情境的一種簡化或純化。真實的學校學習是一個“他人在場”的學習,學習通常是發生在群體中的,是與具體情境相聯系的,而不是孤立的“原子式”學習。完全孤立的、靜态的、簡化的情境中得出的深度學習機制或規律,一定難以解釋真實學校情境中的深度學習機制或規律。
正因為如此,20世紀末美國學習科學開發委員會編寫的《人是如何學習的——大腦、心理、經驗及學校》一書,特别強調了知識建構的情境性和社會性,“認知心理學應該做出更加現實主義轉變,主張以生态學的方法取代信息加工的方法,強調研究自然情境中的認知,更多地關注環境對于智能的影響”,應當從“實驗室研究”到“真實的學習情境”轉向,而“有關認知與學習的情境理論已成為一種能提供有意義學習并促進知識向真實生活情境轉化的重要學習理論”“所有學習離不開特定的文化模式、社會規範和價值期望,這些情境以強有力的方式影響着學習和遷移”。所有這些關于學習的闡述,都是對認知心理學“信息加工”理論的糾偏或完善。
三是就國内研究而言,主要問題是“移譯性”有餘,本土化不足;思辨性主導,實證性缺乏。經過整理,我們發現,我國深度學習研究,無論在“量”上(研究人員與發表成果之多)還是在“質”上(關注的問題涉及面之廣以及探究的深度)都取得了初步的成績。但我們不能不看到,我國該項研究尚存在一些問題,研究成果多而雜,有一定的“泡沫”。其中的主要問題表現在“移譯性”有餘,本土化不足。由于深度學習研究的産生、發展以及所持有的理念、模式均來自西方,我國這方面的研究深受西方研究的影響,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從研究的概念、範疇、模式到研究方法等幾乎都是在翻譯、移植基礎上的一點推進。許多研究文獻在涉及諸如深度學習的界定、标準、類型等專題時,無不具有“移譯”的痕迹。許多論文的展開路徑都是“文獻整合—理論推演—案例佐證”。而理論探讨又以“譯介”為主,或相互引用,引來引去,難免就有疏漏,如有些文獻竟然把馬頓、薩喬寫成美國學者。
針對上述情況,我們認為,早期初涉某一課題,大量移譯、借鑒尚屬正常,而且是十分必要的,但一直持續下去則與實踐毫無裨益。實際上,我們所引用和借鑒的國外的研究成果多半是以西方國家的經驗為原型,其理念、模式、措施等帶上濃厚的西方色彩,如果将這些經驗無保留地轉移到其他國家和地區,其前提本身就很成問題,并且這些模式的效用性也值得懷疑。這實質上是一種“去曆史性”“去社會性”的思維,它忽視了本國的特殊曆史性、文化性與社會性。這種隻滿足于國外成果的介紹與引進,未能有效本土化的研究無益于我國深度學習研究及其實踐的發展,很難轉化成推動實踐的“教育生産力”。

二
走向全視角深度學習
一切現代的教育教學或學習都必須以學生全面發展作為根本出發點和最終歸宿,從這個角度講,應摒棄“單向度”深度學習觀,呼喚建構一種全域或全視角深度學習觀。這種學習觀至少包括以下三個方面内容。
一是對于深度學習的理解必須是整體的、全面的。所謂整體性或全面性理解的意思至少有兩個相互交織的層面。
首先,人的深度學習是一種整體的學習狀态,是學習者全身心投入的過程,而絕不僅僅是學習者大腦内部信息加工的過程;它既是一個信息加工過程,同時還是一個充滿着情感、意志、精神、興趣的過程;它不僅是一個個體學習過程,還是一個社會過程、文化過程,對于中小學生來講又是一個學習過程(學習如何深度學習)。
學生在深度學習時的學習投入是全身心的,不僅僅局限于思維,更是情感、意志、動機、精神乃至身體等全方位的投入。因此,丹麥著名學者克努茲·伊列雷斯(Knud Illeris)提出“如果要理解人類學習的整體複雜性,就需要将多種資源納入到我們的視野之中”,也就是說,對于學習的一個基本理解是“學習具有個體和社會的雙重性”,就“個體性”來講,是指“心理的獲得過程”,而“決定獲得過程的基本上來說還具有生理屬性”,不僅如此,“獲得過程還有一個動機要素,在相當基礎性的意義上,指的是實現一個學習過程所需的心智能量”,而動機要素包含動力、情緒、意志、欲望、興趣等。近年來的腦科學研究最有關鍵性意義的研究發現是:在一個正常的腦中,“理智”的過程不能離開“情緒”的東西獨立發揮功能。可見,就學習者“個體層面”而言,學習是一個整體性投入,既有理智、思維的要素(盡管這些要素被認為是關鍵要素),同時更有情感、意志、精神、興趣等方面的要素,它們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共同決定學習者的學習是否是深度學習。因此,美國著名學者琳達·達林-哈蒙德(Linda Darling-Hammond)在談到有效教學時提倡“一種以學生的思維為核心的理解性學習,使學生全身心地投入,用啟發式的教學方法将他們的身體、心理、認知、邏輯和情感統一起來”。
此外,學生深度學習過程不僅是一個個體心理過程,還是一個社會文化過程。真實的中小學學生在學校情境中的深度學習更多地發生在“群體情境”中(課堂、課外集體活動等),而不是在一個“真空”中展開(就像認知心理學家實驗的情境)。這樣的學習場域中,學生不可能以個體的“原子方式”進行學習,而是在群體互動中進行共同學習,這就必然涉及社會文化因素。即使學生處于“個體狀态”(如課外的自主學習或獨學),但是當“個體”在理解相關知識、文化、價值時,其理解不可能不“镌刻”着特定的社會文化,不可能不受限于社會文化的影響或規範。因此,社會文化因素與其說是學生學習的“情境”“條件”,還不如說是學習“内在機理”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如克努茲·伊列雷斯所說:“學習并非僅在單個的個體身上發生。相反,學是嵌入在一個社會性的情境中的,這個情境提供沖動,設定能夠以及如何學習什麼的框架……這些情境賦予了學習在基礎性條件上的本質差異。”不僅如此,“學習具有個體和社會的雙重性。這意味着必須将傳統學習心理學的個體導向與現代社會導向整合起來,它們中的任何一面都不能單獨闡明問題的答案,提供一種完全和‘正确’的理解,因為它們中的任何一面都是根基上有缺陷的觀點”。這樣看來,“所有學習都包含兩個非常不同的過程,這兩個過程必須都是活躍的,我們才能夠學習點兒什麼”,一個是個體與其所處環境的互動過程,另一個是心理的獲得過程。
其次,學生在深度學習中所能學到的不能僅僅是知識或思維,抑或是解決問題等理智方面的能力,更應當是全面的發展,像情感、意志、精神、激情、德性、靈性、自由、理想、卓越性、超越性等這些能夠賦予學生的整體生活以意義乃至對于學生終身幸福至關重要的品質與價值,理應是深度學習過程中相伴随的、内在具備的特質,否則“如果不去或不能追求幸福,生活就毫無意義”,學習也就毫無意義,因為學習會變得像“機器人”那樣的學習,而“使得生活具有趣味和意義的事情都來自道德和美,如果一切都替換成經濟利益,那麼人就以新的方式退化為動物了”。因此,教育就應當是“人的靈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識和認識的堆集”,是“人與人精神相契合”,是使受教育者“頓悟的藝術”,是促進受教育者自覺“生成”的一種方式,“教育即生成”,就是要讓每個受教育者都能夠主動地、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天賦的潛力,使其“内部靈性與可能性”得到充分的發展。深度學習也是如此,它應當是一個自我喚醒、自我生成、自我創造、自我超越的過程,而隻追求心理過程的“信息加工”式的技術理性思想,實質上是“反人性”的,從根本上違背了人的自由及其超越性之根本特征。
早在20世紀上半葉,針對當時日本國内教育的“嚴酷現實”(單純的智能施教,為了升學考試競争),著名教育家小原國芳就提出了著名的“全人教育思想”。他認為,教育的目的是培養人格,是育成多方面和諧發展的完美的人,而不是單純的智能施教,更不是為了升學考試競争……教育内容必須包含人類文化的全部,理想的人必須是全人,要具備文化的全部,即由六個方面組成:學問、道德、藝術、宗教、身體、生活……全人教育就在于培養智(真)、德(善)、美、聖、體(健)、勞(富)全面發展的人。深度學習也應秉持這樣的價值取向,培養“理性、道德和精神力量”的人(赫欽斯),所以深度學習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培養心智(mind)、心靈(heart)和精神,而不僅僅是學科知識的學習。否則就是沒有“靈魂”的機械過程,沒有“價值旨歸”的單純的知識習得與内化過程。
行筆至此,我們似乎可以這樣來界定深度學習:在特定的社會文化情境中,學習者在與他人互動以及環境互動中,關注知識之間的有機聯系,最終能夠遷移并能夠解決實際生活問題的意義生成的過程。
二是深度學習品質是可以學習的,促進深度學習的策略必須是整體的、系統的、全方位的,任何單一的策略(如設計高階思維問題)都不可能奏效或取得持續性效果的。
首先,我們應當秉持“深度學習品質不是天生的,而是可以學習和發展的”這一核心理念,相信每個學生都有無限發展的可能性,每個學生在教師的有效引導下,在與同伴的良性互動中,在自我砥砺、自我鍛造中獲得深度學習之品質。當代多元智能理論給我們的巨大啟示就是:如果我們考慮學生之間的個體差異,在确保深度學習的基本特質前提下,在盡可能了解每位學生興趣愛好、家庭背景、學習風格、智能特點等方面的基礎上,為每位學生設計适合其發展的教學方式與教學策略,以求學生形成個性化學習方式,那麼,每位學生都有可能得到最大限度的發展,都有可能通過不同的方式獲得深度學習品質。
其次,關注深度學習的重點應當根本轉變,從“結果”轉向“過程”。中小學生要具備“深度學習”品質,必須在教師指導下,在群體互動中“學習”如何進行深度學習。因此,我們應當關注深度學習過程,關注深度學習發生的内在機理與外在條件,運用綜合化、系統化教學策略,促發學生深度學習的發生。這與馬頓與薩喬等人的研究不同,他們隻是研究了大學生的終極學習狀态,也就是說隻關注了解決問題(解答試卷中的問題)過程中呈現出來的“結果性狀态”,而沒有考慮這種狀态在學校教育中是如何得以培養和形成的。因此,研究者們與一線教師必須關注深度學習過程究竟發生了什麼,我們如何促發學生深度學習的發生。在此,我們必須摒棄“單向度”思維,不能認為深度學習隻是一個“認知過程”或單純的“信息加工”過程,它還是一個社會文化過程,一個關涉情感、價值、精神的過程。因此,我們必須在思維上有所創新,建構系統性、複雜性思維,用整體的、系統的教學策略,促進學生深度學習。以往的研究或實踐隻關注“信息加工”過程,很少涉及社會文化過程、情意過程。所幸的是,近幾年來,美國研究院組織實施的SDL項目中的“深度學習能力框架”關注了社會文化因素、情感态度價值觀因素,丹麥學者克努茲·伊列雷斯倡導的“全視角學習理論”,我國少數學者也開始關注這些因素,這為我們以一種系統性、複雜性思維來建構整體的、綜合的教學策略,既考慮認知層面,又考慮情感态度精神層面,還考慮社會文化層面,整體地促進學生深度學習提供了可供借鑒的框架。
最後,我們還必須在實際的學校教學情境中結合具體學科的教學,細緻入微而不是大而化之地探讨促進學生深度學習的具體教學策略。任何學校情境的學習展開的主要方面還是圍繞具體學科開展的學習,因此,深度學習的主流若脫離了具體學科的學習,那是不可想象的神話或是烏托邦的臆想,國内一些所謂的“全課程”之類的草率實驗之挫敗即是明證。
三是在深度學習研究上必須摒棄“個人主義方法論”,徹底變革研究思維,這也是全視角深度學習的題中之意。以往的深度學習研究之所以限于認知心理學“信息加工”層面,從哲學角度講,其立論基礎是孤獨的“原子式”個人主體觀,在考慮深度學習内在機理時,其計算單位是完全獨立自主的個體,“個人”成為理解一切的最後依據,但是這種個體隻能表達人的身體存在,卻不能表達人的精神存在。正如趙汀陽指出的那樣,“人不可能僅僅作為個體而生存,而必須是群體存在,否則無人能夠生存”。因此,從哲學存在論角度講,我們必須建立一種“共在存在論”(ontology of coexistence),即共在先于存在,并且,共在規定存在,共在決定了任何存在都是一種相互存在。那麼,我們為什麼需要一個“共在存在論”來作為解釋生活實踐(包括學習活動)的基礎呢?因為“與他人相處正是人生意義之所在,無共處就無生活……生活隻能在與他人的積極共處中去創造和展開,或者說,隻有積極的共在才能肯定存在,才能實現存在之生生本意,否則必是存在之否定”。因此“解釋事的世界就需要一個與個體存在論(ontology of individuals)完全不同的共在存在論。”
可見,全視角深度學習觀召喚方法論的創新,必須摒棄以往的“個人主義方法論”,賦予社會學視角、文化學視角乃至人類學、管理學等多維視角以合法地位,充分考慮真實的學校情境中深度學習所關涉的諸多因素:生理、心理、社會、文化、管理,等等,在理論上、方法論上拓展、深化深度學習的研究。

三
未來深度學習研究與實踐值得關注的問題
深度學習的問題異常複雜,整體上的突圍僅僅是萬裡長征剛剛走完第一步,還有很多具體的問題有待揭示,如學習者頭腦中内部的信息加工如何與社會文化因素相互作用,其機制何在。筆者認為,至少有三個具體的操作問題值得進一步探尋。
第一,目前在我國主要作為一種理念或理想的深度學習,如何轉化為教師的有效教學行為,即在教學中,教師如何變革自己的教學行為,以促進或支持學生的深度學習,亟待需要“建章立制”。不管承認還是不承認,教師總是現階段教學的主導力量,教師的教學行為往往決定着或制約學生的學習行為,因此,教師行為轉變是必要前提。雖然深度學習研究從“學生角度”業已提出了一些可供操作的策略,如項目學習、大觀點組織(big ideas)、結構化思考等,但是超越這些點狀、碎片化策略,而從“教師角度”提出普遍化的“要求”應當是大範圍推進深度學習的必要前提。因此,在深度學習理念與教師行為之間尚存在一個轉化的中介,這就是指向于學生深度學習的“教學規程”的制定。所謂教學規程是指在一定的教育教學理論或理念指導下,旨在培養學生的某些特定素質或體現某種理念而對教師教學行為提出的若幹規定及其相關的操作策略,它是引導教師轉變教學行為以符合某種教學理念的規則、要求及其操作策略。目前,我們至少可以從教學前、教學中、教學後等幾個方面提出一些教師變革教學行為的教學規程,如教學前“教師應當運用多種方法探明學生對于将要學習的概念或原理的前理解,并運用相應方法解構學生前概念”這一規程,就是指導教師促進學生深度學習的一個有效教學行為指導,而這一規程指引的教學行為的轉變是有着理論基礎的,正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特别顧問、法國學者安德烈·焦爾當指出的那樣,“不論是兒童還是成人,要讓一個學習者掌握一項知識,就必須對他的先有概念進行真正的解構”。
第二,具體學科教學中如何促進學生的深度學習更是未來一個基本問題。衆所周知,每個學科的設置都有獨特的、不可替代的價值,尤其是2018年1月出台的新一輪高中課程方案中,各學科課程标準都是圍繞“學科核心素養”來研制的,如語文學科核心素養就規定了語文素養的核心要素和關鍵内容,主要包括“語言建構與運用”“思維發展與提升”“審美鑒賞與創造”與“文化傳承與理解”四個方面。語文學科中的深度學習必須指向這四要素的培養。因此,真實的學校情境中的教學總是而且首先必須落實在具體學科教學中,學生才有可能獲得該學科核心素養。因此,教師在具體的學科教學中,如何結合學科知識的教學,引導學生深度學習,就成了教學實踐中的重要課題。在學科教學實踐與研究中,我們必須面對一系列問題,諸如是否存在促進學生深度學習的統一的、一緻的方法或策略?人文學科與數理學科中的教學策略或方法有無區别?如果有,區别又在哪裡?如果用比較公認的有效策略,如“大觀點”來整合信息,文理學科是否有不同?另外,我們還要探明:為什麼有的學生能進行深度學習,而有的學生隻能停留在淺層狀态,僅僅是因為其大腦中“信息加工”的不同而導緻的嗎?為什麼有的學生在某些學科能夠進行深度學習,而在另一些學科則呈現淺層學習狀态,原因何在?中學生與小學生之間的深度學習的差異在哪裡?等等。如果我們不結合特定學科的具體内容,不結合每個學生的具體學科學習來研究或實踐,就會流于空談,徒留浮誇的議論。
第三,更具體的是,學界一般将“項目學習”作為深度學習的有效路徑加以推崇(有研究表明項目學習可以以“大觀點”來組織跨域内容,有利于課程整合,可以有效遷移學以緻用等),但現有的項目學習多半是“拼盤式”學習,如圍繞“春天來了”這一所謂的主題,語文課讀春天的文章、寫春天,科學課探尋春天的節氣,美術課畫春天,音樂唱春天,體育課玩春天的遊戲等,這樣的拼盤式學習是無法讓學生真正走向深度學習的。那麼,如何摒棄拼盤式學習,并以問題驅動、任務驅動來開展項目學習就是不二選項,但問題是,怎樣的問題、任務才能驅動項目學習,有無學科差異,中小學生的項目學習有無差異,等等,這些都是值得進一步探究的問題。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