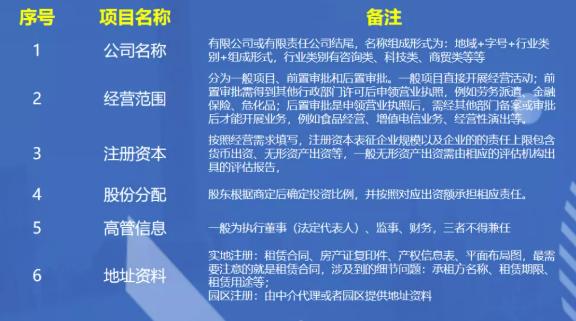腌作“黃菜”那時光
馮兵緒
走過鄰家馮大娘的門口,一股煮菜的濃味兒撲鼻而來,院子裡已有一籃子剛撈出的蔓菁葉子菜冒着濃濃的白氣,暗綠色的菜葉子格外滑嫩……年已八旬的大娘仍不忘年年冬天腌作“黃菜”啊!
那籃子冒着熱氣的暗綠色的菜葉子,将我的思緒拉回了那個遙遠又好似近在眼前的時光裡。
每天秋天,收完了玉米,種下了麥子,摘完了柿子,也就到了“小雪”的節氣了。“小雪不拔菜,必定受傷害”。一近小雪,人們紛紛忙着拔蘿蔔,窖白菜,薅蔓菁,刨胡蘿蔔。該曬條兒的曬條,該入窖的入窖,該裝袋的裝袋,剩下的菜纓子就都腌作“黃菜”了。

小時候不懂為啥叫“黃菜”,明明綠綠的菜葉子,一煮一炸,就改變了名字?老人們也回答不了我的困惑,反正就叫“黃菜”了。
這些菜纓子要将黃葉子,老梃子都剔出來,留給豬和雞們食用。擇出的好菜,用水沖洗幹淨,再到五筲水的大鍋裡去煮熟,山裡人叫這為“炸菜”。那時候,誰家都要“炸”七八十來鍋的。
頭天炸好,第二天再到河灘的泉水裡去涮幹淨,切碎,山裡人叫這為“投菜”。
這“投菜”可是個熱鬧活兒。頭天晚上,母親就得去找左鄰右舍的大娘嬸子們來幫忙的,往往十幾大鍋的菜,也得找七八個人。曾記得鄰居秋枝大娘是位切菜的好手,年年這時光幾乎天天有人請去切菜,并且還要排号了!

一大早,父親就将一籃籃的青菜擔到河灘泉眼處。早飯之後,嬸子大娘們各人提着一個筐子和一把磨得锃亮的菜刀來到泉眼邊,帶隊的大娘一聲令下,整理菜的,涮洗菜的,刀切菜的,各司其職。整菜的,将籃子裡淩亂的菜梃子一把一把理順溜,以便好切菜;涮菜的将整好的菜放到筐子裡,連筐子帶菜放到水裡漂洗幹淨。切菜的接過涮幹淨的菜把子,用手瀝幹水份,左手按住菜把子,右手操刀,“嚓嚓嚓”不停地切起來。邊幹活邊閑話,“三個女人一台戲”,況且這七八個,甚至十幾個嬸子大娘們聚在一起,那熱鬧場面無法言狀了。她們的話題離不了東家長西家短,誰家的媳婦孝順,誰家的婆婆厲害……
我見過秋枝大娘切菜,隻見她利索地兩手掐起一大把菜,放在筐子裡,先擠去水份,左手先撫平菜把子,再按住,右手操刀,手起刀落,菜便切斷。來不及細看,半把菜已切過去了,隻見右手在不住勁地點動,令人眼花缭亂。眨眼間,一把菜已切完,另一把已到了筐裡。别人剛切好了一筐,她早已又切半筐多了。

臨近午時,菜就收拾完畢了。年輕的嬸子擔起切好瀝幹部分水份的菜籃子,扭起楊柳腰,返回了家去。大娘們端起切菜的筐子,踮着小腳随後趕來。不用說,中午必是蘿蔔熬菜湯,特意再炒一小鍋大蔥配剛投好的“黃菜”了,那個香啊,似乎還留在唇邊。
父親早已把母親提前洗好的幾個大甕排放到了屋門的背後了。這投好的菜,就要一一腌作在這幾個大小不等、高矬不一的幾個大甕裡了。把上午投好的菜再一一放到筐子裡,用木闆再擠壓一遍,盡力瀝出水份,才一一放到大甕裡去。放到甕裡之後,再用擀面杖一層一層壓實,離甕口大約一尺高就不再放入菜了,最後選一塊洗幹淨的橢圓的大石塊壓在菜上面。這項“黃菜”入甕的活就算結束了,這叫“按菜”。随後,母親在做早晚飯時,再從煮開的豆沫兒湯裡向外舀半盆,待晾涼後,倒入菜甕裡。這叫腌作菜的“漿水”。這“漿水”不能一次倒好,隔幾天倒一次,天天得觀看菜甕的變化,以防甕裡的菜倒甕變壞。這樣約摸半月之後,菜甕裡有一股淡香的酸味兒,這“黃菜”便做好了。

之後,這幾甕“黃菜”要相伴一冬,直到春暖花開了。每頓豆沫兒湯中,少不了半碗黃菜搭配,這就是山裡人口中的“菜飯”;每頓的幹糧中少不了“黃菜”的調配,這就是山裡人口中的“菜餅子、菜窩窩、菜團子”;這“黃菜”還讓山裡人變出了各種花樣,在滾開的菜湯中,撒入玉茭面,再開過一陣後,就做成了“菜苦累”;更有手巧的大娘們,用“黃菜”調餡兒,配以大蔥,烙出了香噴噴的“菜角子”,或者包成噴噴香的“菜餃子”。
曾記得有一年的下雪天,我被凍感冒了,持續發燒,鬧騰了好幾天,什麼東西也吃不下。就在這時候,姥姥特意給做了大蔥黃菜餡兒的菜餃子,在姜湯中煮出來。我吃了幾個後,又喝了半碗姜湯,便退了燒,開了胃口,這感冒也随即好了起來……

如今青睐“黃菜”的人少之又少,除了鄰居大娘仍在傳承這道荒年中傳留下的“美食”之外,恐怕現在的年輕人連蔓菁胡蘿蔔都吃不下了,更别說“黃菜”了。但“黃菜”的功勞永遠不會從記憶中抹去的。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