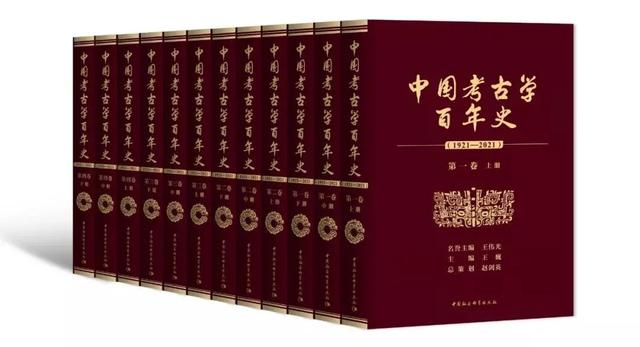刑法上最難認定的身份,就是職務犯罪的主體身份“國家工作人員”。是否國家工作人員,最難判斷的,就是在國有參股企業(不是國有企業)中,不是國家出資的機構直接委派的那些中高層管理人員,很多時候,他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算不算國家工作人員。

國有企業中的管理人員,根據刑法第93條,“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可以直接認定為國家工作人員。國有參股企業中,直接受到國有投資機構委派,根據刑法第93條“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及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國家工作人員論”,也可以直接認定為國家工作人員。
那麼,那些國有參股企業中,沒有受到國有投資機構委派的管理人員,還是國家工作人們嗎?對這個問題,2010年以前,答案是否定的;2010年以後,這個答案又在司法實踐中變成了肯定答案。

2001年最高法《關于在國有資本控股、參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從事管理工作的人員利用職務便利非法占有本公司财物如何定罪問題的批複》嚴格依照九十三條第二款規定,指出“在國有資本控股、參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從事管理工作的人員,除受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從事公務的以外,不屬于國家工作人員”。
2005年最高法《關于如何認定國有控股、參股股份有限公司中的國有公司、企業人員的解釋》隻有一句話“國有公司、企業委派到國有控股、參股公司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國有公司、企業人員論。”言外之意,并不是國有企業國有公司委派,而是由國有控股、參股公司任命的其他人員,則不是國家工作人員。

最高院、最高檢于2010年發布《關于辦理國家出資企業中職務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幹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規定“經國家出資企業中負有管理、監督國有資産職責的組織批準或者研究決定,代表其在國有控股、參股公司及其分支機構中從事組織、領導、監督、經營、管理工作的人員,應當認定為國家工作人員。國家出資企業中的國家工作人員,在國家出資企業中持有個人股份或者同時接受非國有股東委托的,不影響其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的認定。”
該司法解釋突破了刑法就是九十三條第二款明文規定的“委派”界限,把不屬于“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違法解釋,納入到了國家工作人員範圍,擴大了職務犯罪的打擊面。
當然,最高法也是明知該司法解釋對國有出資企業中僅是受到本單位黨委、黨政聯席會批準或者研究決定擔任中層領導的人員認定為國家工作人員是對刑法第九十三條的突破。例如,《刑事審判參考》第959号“宋濤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案——如何認定國有控股企業中一般中層管理幹部的國家工作人員身份”,指出“《意見》第六條已對刑法的規定有了突破”“首次将‘代表人員’納入國家工作人員的範疇”。正是基于這樣一份“愧疚之情”或者是“歉意”,最高法給出的方案是:限制《意見》第六條中的“經國家出資企業中負有管理、監督國有資産職責的組織”限定在上級或者本級國家出資企業黨委會和黨政聯席會;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包括公司的人事組織部門,均不是适格的任命主體。對此,又在《刑事審判參考》“第974号“章國鈞受賄案——如何認定國家出資企業中的國家工作人員”重申了這樣的限制态度,指出“組織”指國有出資企業内部的黨委、黨政聯席會,給出的合理性根據是“黨管幹部的組織原則”,并将這樣的認定“美化”為“将部分‘間接委派’人員有條件地納入‘國家工作人員’範疇”。

上述章國鈞受賄案中的被告人章國鈞,雖原系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交通銀行”)湖州新天地支行業務管理經理、支行行長助理(合同制員工),但是因為他的任命是經交通銀行湖州分行黨委研究決定的,他被認定為了國家工作人員。而宋濤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案中的被告人宋濤原系上海國際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國有控股、中外合資公司)生産業務部生産調度室經理,負責上港集團下屬港區碼頭貨物裝卸、船舶到港、浮吊作業計劃、分配、調度和管理等工作,因他的職務系由上級部門領導個人提出意見,人事組織部審核,公司總裁批準通過,而不是由黨委會或者黨政聯合會通過,他“幸運”地被依法認定為非國家工作人員。
兩起權威指導案例想告訴我們什麼?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讀到的更多的是背離刑法條文類推解釋導緻的個案不公平,最高法越是想通過限制解釋來縮小《意見》中“組織”的認定範圍,越是在現實辦案中造成的各種擰巴。代表着新世紀立法解釋以來,理論與實踐關于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的認定從“身份論”走向“公務論”的倒退與逆流。“黨管幹部原則”不能成為這種類推解釋、“身份論”回流的擋箭牌和合理性根據。

或許正是基于這種是否國家工作人員,很可能在涉及國有出資企業個案中“傻傻分不清”的情形時有出現,帶來個案不公,《刑法修正案十一》已經将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與受賄罪、職務侵占罪與貪污罪、挪用資金罪與挪用公款罪的法定性拉平,似乎隻要是能夠認定上述犯罪,在受賄、貪污、挪用這三類行為類型下,都不會造成量刑不公。但果真這樣就可以減少個案不公嗎?顯然不會。
一是三類犯罪除了主體外,司法實踐中還存在其他方面的構成要件要素認定的不同。比如,非公受賄和受賄的構成要件在感情投資類型下,兩者就有顯著不同;在認定是否謀取利益這一點上,也還是有差别的。較非公受賄,受賄原本就更容易構成。
二是一旦将原本不是國家工作人員的人員認定為國家工作人員,會造成這些人員的收入、境外存款受到更為嚴格的約束。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條規定了巨額财産來源不明罪和隐瞞境外存款罪。這就意味着一個國有出資企業中未被直接委派的管理人員,原本個人财産狀況、境外存款狀況不需要申報,因司法解釋突破刑法,導緻他們有了巨額财産來源不明或者隐瞞境外存款犯罪的風險。

作者:丁慧敏律師,清華大學刑法學博士。天津師範大學刑事風險防控中心特邀研究員,廈門大學法學院法律碩士畢業論文評審專家。曾辦理廳局級職務犯罪案件五十餘起,非法吸收公衆存款等經濟犯罪多起。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