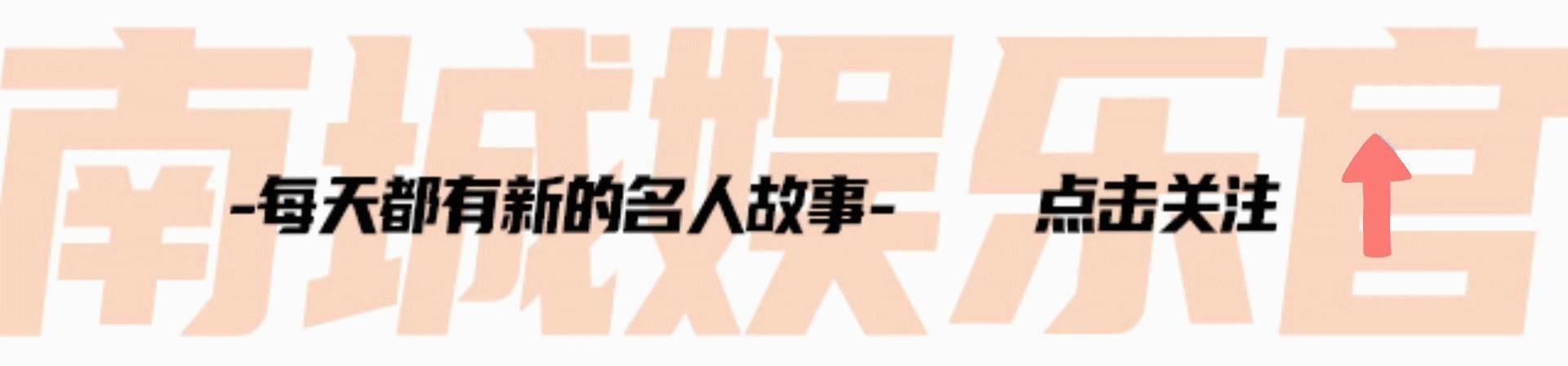文章節選自圖書《實務刑法評注》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8月版轉自實務刑事法評注
【刑法條文】
第二百七十一條 【職務侵占罪】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将本單位财物非法占為己有,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數額巨大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别巨大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國有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國有單位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和國有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國有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以及其他單位從事公務的人員有前款行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條、第三百八十三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立法沿革】
本條系1997年《刑法》吸收單行刑法作出修改後的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自1988年1月21日起施行)将貪污罪的犯罪主體修改為“國家工作人員、集體經濟組織工作人員或者其他經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懲治違反公司法的犯罪的決定》(自1995年2月28日起施行)第十條規定:“公司董事、監事或者職工利用職務或者工作上的便利,侵占本公司财物,數額較大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數額巨大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處沒收财産。”第十二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犯本決定……第十條……規定之罪的,依照《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的規定處罰。”1997年《刑法》将貪污罪的主體規定為國家工作人員,将非國家工作人員的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人員,侵占本單位财物的行為規定為職務侵占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第二十九條對本條作了修改,調整法定刑,将兩檔刑罰調整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三檔刑罰。

【立法工作機關意見】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對〈關于公司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采取欺騙等手段非法占有股東股權的行為如何定性處理的批複〉的意見》
最高人民檢察院: 你院法律政策研究室2005年8月26日來函收悉。經研究,答複如下: 據刑法第九十二條的規定,股份屬于财産。采用各種非法手段侵吞、占有他人依法享有的股份,構成犯罪的,适用刑法有關非法侵犯他人财産的犯罪規定。
【司法解釋】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村民小組組長利用職務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行為如何定性問題的批複》(法釋〔1999〕12号,自1999年7月3日起施行)
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 你院川高法〔一九九八〕二百二十四号《關于村民小組組長利用職務便利侵吞公共财物如何定性的問題的請示》收悉。經研究,答複如下: 對村民小組組長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将村民小組集體财産非法占為己有,數額較大的行為,應當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款的規定,以職務侵占罪定罪處罰。
注:“問:村民委員會成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為,能否适用該司法解釋? 答:不能适用。本解釋隻針對村民小組組長。他們中有的可能是村委會成員,但批複中很明确是村民小組組長利用職務便利實施犯罪行為,而不是利用村委會成員的職務便利。村民委員會成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将本單位财物非法占為己有的行為如何處理的問題,将來司法解釋還要做出規定。”(參見《本刊編輯就〈關于村民小組組長利用職務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行為如何定性問題的批複〉采訪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有關負責人》,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辦:《中國刑事審判指導案例4》(增訂第3版),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貪污、職務侵占案件如何認定共同犯罪幾個問題的解釋》(法釋〔2000〕15号,自2000年7月8日起施行)
為依法審理貪污或者職務侵占犯罪案件,現就這類案件如何認定共同犯罪問題解釋如下: 第一條 行為人與國家工作人員勾結,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便利,共同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以貪污罪共犯論處。 第二條 行為人與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人員勾結,利用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人員的職務便利,共同将該單位财物非法占為己有,數額較大的,以職務侵占罪共犯論處。 第三條 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中,不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的人與國家工作人員勾結,分别利用各自的職務便利,共同将本單位财物非法占為己有的,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質定罪。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國有資本控股、參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從事管理工作的人員利用職務便利非法占有本公司财物如何定罪問題的批複》(法釋〔2001〕17号,自2001年5月26日起施行)
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 你院渝高法明傳〔2000〕38号《關于在股份有限公司中從事管理工作的人員侵占本公司财物如何定性的請示》收悉。經研究,答複如下: 在國有資本控股、參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從事管理工作的人員,除受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從事公務的以外,不屬于國家工作人員。對其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将本單位财物非法占為己有,數額較大的,應當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款的規定,以職務侵占罪定罪處罰。 此複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妨害預防、控制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的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法釋〔2003〕8号,自2003年5月15日起施行,節錄)
第十四條 貪污、侵占用于預防、控制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的款物或者挪用歸個人使用,構成犯罪的,分别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條、第三百八十三條、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三百八十四條、第二百七十二條的規定,以貪污罪、侵占罪、挪用公款罪、挪用資金罪定罪,依法從重處罰。 挪用用于預防、控制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的救災、優撫、救濟等款物,構成犯罪的,對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三條的規定,以挪用特定款物罪定罪處罰。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法釋〔2016〕9号,自2016年4月18日起施行,節錄)
第十一條 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條規定的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第二百七十一條規定的職務侵占罪中的“數額較大”“數額巨大”的數額起點,按照本解釋關于受賄罪、貪污罪相對應的數額标準規定的二倍、五倍執行。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條規定的挪用資金罪中的“數額較大”“數額巨大”以及“進行非法活動”情形的數額起點,按照本解釋關于挪用公款罪“數額較大”“情節嚴重”以及“進行非法活動”的數額标準規定的二倍執行。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條第一款規定的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中的“數額較大”“數額巨大”的數額起點,按照本解釋第七條、第八條第一款關于行賄罪的數額标準規定的二倍執行。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虛假訴訟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法釋〔2018〕17号,自2018年10月1日起施行)
第四條 實施刑法第三百零七條之一第一款行為,非法占有他人财産或者逃避合法債務,又構成詐騙罪,職務侵占罪,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貪污罪等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從重處罰。
【規範性文件】
《全國法院維護農村穩定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法〔1999〕217号,節錄)
三(三)關于村委會和村黨支部成員利用職務便利侵吞集體财産犯罪的定性問題 為了保證案件的及時審理,在沒有司法解釋規定之前,對于已起訴到法院的這類案件,原則上以職務侵占罪定罪處罰。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國家出資企業中職務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幹問題的意見》(法發〔2010〕49号)
随着企業改制的不斷推進,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在辦理國家出資企業中的貪污、受賄等職務犯罪案件時遇到了一些新情況、新問題。這些新情況、新問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複雜性,需要結合企業改制的特定曆史條件,依法妥善地進行處理。現根據刑法規定和相關政策精神,就辦理此類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幹問題,提出以下意見:一、關于國家出資企業工作人員在改制過程中隐匿公司、企業财産歸個人持股的改制後公司、企業所有的行為的處理 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受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委托管理、經營國有财産的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在國家出資企業改制過程中故意通過低估資産、隐瞞債權、虛設債務、虛構産權交易等方式隐匿公司、企業财産,轉為本人持有股份的改制後公司、企業所有,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條、第三百八十三條的規定,以貪污罪定罪處罰。貪污數額一般應當以所隐匿财産全額計算;改制後公司、企業仍有國有股份的,按股份比例扣除歸于國有的部分。 所隐匿财産在改制過程中已為行為人實際控制,或者國家出資企業改制已經完成的,以犯罪既遂處理。 第一款規定以外的人員實施該款行為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的規定,以職務侵占罪定罪處罰;第一款規定以外的人員與第一款規定的人員共同實施該款行為的,以貪污罪的共犯論處。 在企業改制過程中未采取低估資産、隐瞞債權、虛設債務、虛構産權交易等方式故意隐匿公司、企業财産的,一般不應當認定為貪污;造成國有資産重大損失,依法構成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條或者第一百六十九條規定的犯罪的,依照該規定定罪處罰。二、關于國有公司、企業在改制過程中隐匿公司、企業财産歸職工集體持股的改制後公司、企業所有的行為的處理 國有公司、企業違反國家規定,在改制過程中隐匿公司、企業财産,轉為職工集體持股的改制後公司、企業所有的,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六條第一款的規定,以私分國有資産罪定罪處罰。 改制後的公司、企業中隻有改制前公司、企業的管理人員或者少數職工持股,改制前公司、企業的多數職工未持股的,依照本意見第一條的規定,以貪污罪定罪處罰。三、關于國家出資企業工作人員使用改制公司、企業的資金擔保個人貸款,用于購買改制公司、企業股份的行為的處理 國家出資企業的工作人員在公司、企業改制過程中為購買公司、企業股份,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将公司、企業的資金或者金融憑證、有價證券等用于個人貸款擔保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條或者第三百八十四條的規定.以挪用資金罪或者挪用公款罪定罪處罰。 行為人在改制前的國家出資企業持有股份的,不影響挪用數額的認定,但量刑時應當酌情考慮。 經有關主管部門批準或者按照有關政策規定,國家出資企業的工作人員為購買改制公司、企業股份實施前款行為的,可以視具體情況不作為犯罪處理。四、關于國家工作人員在企業改制過程中的渎職行為的處理 國家出資企業中的國家工作人員在公司、企業改制或者國有資産處置過程中嚴重不負責任或者濫用職權,緻使國家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條的規定,以國有公司、企業人員失職罪或者國有公司、企業人員濫用職權罪定罪處罰。 國家出資企業中的國家工作人員在公司、企業改制或者國有資産處置過程中徇私舞弊,将國有資産低價折股或者低價出售給其本人未持有股份的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個人,緻使國家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九條的規定,以徇私舞弊低價折股、出售國有資産罪定罪處罰。 國家出資企業中的國家工作人員在公司、企業改制或者國有資産處置過程中徇私舞弊,将國有資産低價折股或者低價出售給特定關系人持有股份或者本人實際控制的公司、企業,緻使國家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條、第三百八十三條的規定,以貪污罪定罪處罰。貪污數額以國有資産的損失數額計算。 國家出資企業中的國家工作人員因實施第一款、第二款行為收受賄賂,同時又構成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規定之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五、關于改制前後主體身份發生變化的犯罪的處理 國家工作人員在國家出資企業改制前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實施犯罪,在其不再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後又實施同種行為,依法構成不同犯罪的,應當分别定罪,實行數罪并罰。 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在國家出資企業改制過程中隐匿公司、企業财産,在其不再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後将所隐匿财産據為己有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條、第三百八十三條的規定,以貪污罪定罪處罰。 國家工作人員在國家出資企業改制過程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事先約定在其不再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後收受請托人财物,或者在身份變化前後連續收受請托人财物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第三百八十六條的規定,以受賄罪定罪處罰。 六、關于國家出資企業中國家工作人員的認定 經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提名、推薦、任命、批準等,在國有控股、參股公司及其分支機構中從事公務的人員,應當認定為國家工作人員。具體的任命機構和程序,不影響國家工作人員的認定。 經國家出資企業中負有管理、監督國有資産職責的組織批準或者研究決定,代表其在國有控股、參股公司及其分支機構中從事組織、領導、監督、經營、管理工作的人員,應當認定為國家工作人員。 國家出資企業中的國家工作人員,在國家出資企業中持有個人股份或者同時接受非國有股東委托的,不影響其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的認定。七、關于國家出資企業的界定 本意見所稱“國家出資企業”,包括國家出資的國有獨資公司、國有獨資企業,以及國有資本控股公司、國有資本參股公司。 是否屬于國家出資企業不清楚的,應遵循“誰投資、誰擁有産權”的原則進行界定。企業注冊登記中的資金來源與實際出資不符的,應根據實際出資情況确定企業的性質。企業實際出資情況不清楚的,可以綜合工商注冊、分配形式、經營管理等因素确定企業的性質。八、關于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具體貫徹 辦理國家出資企業中的職務犯罪案件時,要綜合考慮曆史條件、企業發展、職工就業、社會穩定等因素,注意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嚴格把握犯罪與一般違規行為的區分界限。對于主觀惡意明顯、社會危害嚴重、群衆反映強烈的嚴重犯罪,要堅決依法從嚴懲處;對于特定曆史條件下、為了順利完成企業改制而實施的違反國家政策法律規定的行為,行為人無主觀惡意或者主觀惡意不明顯,情節較輕,危害不大的,可以不作為犯罪處理。 對于國家出資企業中的職務犯罪,要加大經濟上的懲罰力度,充分重視财産刑的适用和執行,最大限度地挽回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的損失。不能退贓的,在決定刑罰時,應當作為重要情節予以考慮。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盜竊油氣、破壞油氣設備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幹問題的意見》(法發〔2018〕18号,節錄)
四、關于内外勾結盜竊油氣行為的處理 行為人與油氣企業人員勾結共同盜竊油氣,沒有利用油氣企業人員職務便利,僅僅是利用其易于接近油氣設備、熟悉環境等方便條件的,以盜竊罪的共同犯罪論處。 實施上述行為,同時構成破壞易燃易爆設備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依法懲治妨害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違法犯罪的意見》(法發〔2020〕7号,節錄)
二、準确适用法律,依法嚴懲妨害疫情防控的各類違法犯罪(七)依法嚴懲疫情防控失職渎職、貪污挪用犯罪。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負有組織、協調、指揮、災害調查、控制、醫療救治、信息傳遞、交通運輸、物資保障等職責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緻使公共财産、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的規定,以濫用職權罪或者玩忽職守罪定罪處罰。 衛生行政部門的工作人員嚴重不負責任,不履行或者不認真履行防治監管職責,導緻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傳播或者流行,情節嚴重的,依照刑法第四百零九條的規定,以傳染病防治失職罪定罪處罰。 從事實驗、保藏、攜帶、運輸傳染病菌種、毒種的人員,違反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的有關規定,造成新型冠狀病毒毒種擴散,後果嚴重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三十一條的規定,以傳染病毒種擴散罪定罪處罰。 國家工作人員,受委托管理國有财産的人員,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人員,利用職務便利,侵吞、截留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用于防控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的款物,或者挪用上述款物歸個人使用,符合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條、第三百八十三條、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三百八十四條、第二百七十二條規定的,以貪污罪、職務侵占罪、挪用公款罪、挪用資金罪定罪處罰。挪用用于防控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的救災、優撫、救濟等款物,符合刑法第二百七十三條規定的,對直接責任人員,以挪用特定款物罪定罪處罰。
《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充分發揮檢察職能服務保障“六穩”“六保”的意見》(高檢發〔2020〕10号,節錄)
3.依法保護企業正常生産經營活動。深刻認識“六穩”“六保”最重要的是穩就業、保就業,關鍵在于保企業,努力落實讓企業“活下來”“留得住”“經營得好”的目标。一是加大力度懲治各類侵犯企業财産、損害企業利益的犯罪。依法嚴格追訴職務侵占、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和挪用資金犯罪,根據犯罪數額和情節,綜合考慮犯罪行為對民營企業經營發展、商業信譽、内部治理、外部環境的影響程度,精準提出量刑建議。對提起公訴前退還挪用資金或者具有其他情節輕微情形的,可以依法不起訴;對數額特别巨大拒不退還或者具有其他情節特别嚴重情形的,依法從嚴追訴。二是依法慎重處理貸款類犯罪案件。在辦理騙取貸款等犯罪案件時,充分考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實際情況,注意從借款人采取的欺騙手段是否屬于明顯虛構事實或者隐瞞真相,是否與銀行工作人員合謀、受其指使,是否非法影響銀行放貸決策、危及信貸資金安全,是否造成重大損失等方面,合理判斷其行為危害性,不苛求企業等借款人。對于借款人因生産經營需要,在貸款過程中雖有違規行為,但未造成實際損失的,一般不作為犯罪處理。對于借款人采取欺騙手段獲取貸款,雖給銀行造成損失,但證據不足以認定借款人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不能以貸款詐騙罪定性處理。三是依法慎重處理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犯罪案件。充分考慮企業生産經營實際,注意把握企業因資金周轉困難拖欠勞動報酬與惡意欠薪的界限,靈活采取檢察建議、督促履行、協調追欠追贓墊付等形式,既有效維護勞動者權益,又保障企業生産經營。對惡意欠薪涉嫌犯罪,但在提起公訴前支付勞動報酬,并依法承擔相應賠償責任的,可以依法不起訴。四是嚴格把握涉企業生産經營、創新創業的新類型案件的法律政策界限。對于企業創新産品與現有國家标準難以對應的,應當深入調查,進行實質性評估,加強請示報告,準确認定産品屬性和質量,防止簡單化“對号入座”,以生産、銷售僞劣産品定罪處罰。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試行)》 (法發〔2021〕21号,節錄)
四、常見犯罪的量刑(十四)職務侵占罪 1.構成職務侵占罪的,根據下列情形在相應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點: (1)達到數額較大起點的,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點。 (2)達到數額巨大起點的,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點。 (3)達到數額特别巨大起點的,在十年至十一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點。依法應當判處無期徒刑的除外。 2.在量刑起點的基礎上,根據職務侵占數額等其他影響犯罪構成的犯罪事實增加刑罰量,确定基準刑。 3.構成職務侵占罪的,根據職務侵占的數額、危害後果等犯罪情節,綜合考慮被告人繳納罰金的能力,決定罰金數額。 4.構成職務侵占罪的,綜合考慮職務侵占的數額、手段、危害後果、退贓退賠等犯罪事實、量刑情節,以及被告人的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認罪悔罪表現等因素,決定緩刑的适用。
【立案追訴标準】
《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标準的規定(二)》(公通字〔2022〕12号,節錄)
第七十六條 〔職務侵占案(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款)〕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将本單位财物非法占為己有,數額在三萬元以上的,應予立案追訴。
注:本條關于職務侵占罪立案追訴标準的規定與法釋〔2016〕9 号第十一條第一款不一緻,系根據經《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改後《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款的規定作出。——本評注注
【法律适用答複、複函】
《公安部經濟犯罪偵查局關于宗教活動場所工作人員能否構成職務侵占或挪用資金犯罪主體的批複》(公經〔2004〕643号)
山西省公安廳經偵總隊:你總隊晉公經〔2004〕034号《關于淨賢能否構成職務侵占罪或挪用資金罪主體的請示》收悉。經研究,并征求國家宗教事務局意見,批複如下:根據《宗教活動場所管理條例》(國務院令第145号令)等有關規定,宗教活動場所屬于刑法第271條和第272條所規定的“其他單位”的範圍。宗教活動場所的财産屬于公共财産或信教公民共有财産,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侵占、哄搶、私分和非法處分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的合法财産。宗教活動場所的管理人員利用職務之便,侵占或挪用宗教活動場所公共财産的,可以構成職務侵占罪或挪用資金罪。
《公安部經偵局關于對非法占有他人股權是否構成職務侵占罪問題的工作意見》(2005年6月24日)
近年來,許多地方公安機關就公司股東之間或者被委托人采用非法手段侵占股權,是否涉嫌職務侵占罪問題請示我局。對此問題,我局多次召開座談會并分别征求了高檢、高法及人大法工委刑法室等有關部門的意見。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二庭書面答複我局:對于公司股東之間或者被委托人利用職務便利,非法占有公司股東股權的行為,如果能夠認定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則可對其利用職務便利,非法占有公司管理中的股東股權的行為以職務侵占罪論處。 現予網上公布,供各地公安機關辦理類似案件時借鑒參考。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關于對通過虛假驗資騙取工商營業執照的“三無” 企事業能否成為職務侵占罪客體問題征求意見的複函》(法研〔2008〕79号)
公安部經濟犯罪偵查局: 貴局《關于對通過虛假驗資騙取工商營業執照的“三無”企業能否成為職務侵占罪客體問題征求意見的函》收悉。經研究,答複如下: 根據1999年7月3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第1條的規定,私營、獨資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隻有具有法人資格才屬于我國刑法中所指的單位,其财産權才能成為職務侵占罪的客體。也就是說,是否具有法人資格是私營、獨資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成為我國刑法中“單位”的關鍵。行為人通過虛假驗資騙取工商營業執照成立的企業,即便為“三無”企業,隻要該企業具有法人資格,并且不是為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而設立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或者公司、企業、事業單位設立後,不是以實施犯罪為主要活動的,應當視為刑法中的單位,能夠成為刑法第271條第1款規定的“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這些單位中的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将單位财物非法占為己有,數額較大的,構成職務侵占罪。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關于個人獨資企業員工能否成為職務侵占罪主體問題的複函》(法研〔2011〕20号)
公安部經濟犯罪偵查局: 貴局公經商貿[2011]13号《關于請對薄××、周××案有關犯罪主體問題進行認定的函》收悉。經研究,我們認為,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款規定中的“單位”,包括“個人獨資企業”。主要理由是: 刑法第三十條規定的單位犯罪的“單位”與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款職務侵占罪的單位概念不盡一緻,前者是指作為犯罪主體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單位”,後者是指财産被侵害需要刑法保護的“單位”,責任追究針對的是該“單位”中的個人。有關司法解釋之所以規定,不具有法人資格的獨資企業不能成為單位犯罪的主體,主要是考慮此類企業因無獨立财産、個人與企業行為的界限難以區分;不具備獨立承擔刑事責任的能力。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款立法的目的基于保護單位财産,懲處單位内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侵占單位财産的行為,因此該款規定中的“單位”應當也包括獨資企業。 《個人獨資企業法》第二十六條規定,被依法吊銷營業執照的個人獨資企業應當解散。鑒于本案被害單位在2007年12月11日已被吊銷營業執照,對于此後實施的相關行為的性質認定,需要進一步核實相關案件被害單位是否已經解散。 以上意見供參考。
《公安部經濟犯罪偵查局關于範×涉嫌職務侵占案犯罪主體問題的批複》 (公經〔2012〕898号)
範×利用其擔任業主委員會主任的職務,将小區警衛室用房對外出租後所得租金占為己有,屬于職務侵占犯罪行為。
【刑參案例規則提煉】
《董佳、岑炯等僞造有價票證、職務侵占案——以假充真侵占門票收入款行為的定性》(第213号案例)、《于慶偉職務侵占案——單位的臨時工能否構成職務侵占罪》(第235号案例)、《趙某盜竊案——如何區分盜竊罪和職務侵占罪》(第246号案例)、《林通職務侵占案——名義職務與實際職務不一緻的應當如何判斷是否利用了職務之便》(第247号案例)、《張珍貴、黃文章職務侵占案——受委托管理經營國有财産人員的認定》(第274号案例)、《賀豫松職務侵占案——臨時搬運工竊取鐵路托運物資構成盜竊罪還是職務侵占罪》(第452号案例)、《虞秀強職務侵占案——利用代理公司業務的職務之便将簽訂合同所得之财物占為己有的,應定職務侵占罪還是合同詐騙罪》(第484号案例)、《劉宏職務侵占案——用工合同到期後沒有續簽合同的情況下,原單位工作人員是否符合職務侵占罪的主體要件》(第516号案例)、《譚世豪職務侵占案——單位員工利用本單位業務合作方的收費系統漏洞,制造代收業務費用結算金額減少的假象,截留本單位受托收取的業務合作方現金費用的行為,應當如何定性》(第1137号案例)、《韓楓職務侵占案——如何判斷行為人侵占單位财産的行為是否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第1440号案例)所涉規則提煉如下:1.職務侵占罪的主體範圍規則。“‘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人員’,一般包括正式職工、合同工和臨時工三種成分。是否構成職務侵占罪,關鍵在于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人員非法占有單位财物(包括單位管理、使用、運輸中的其他單位财産和私人财産)是否利用了職務上的便利,而不是行為人在單位的‘身份’。單位正式職工作案,沒有利用職務便利的,依法不能定職務侵占罪;即使是臨時工,有職務上的便利,并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單位财物的,也應當認定屬于職務侵占行為。”(第235号案例)“臨時搬運工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占有本單位财物的構成職務侵占罪。”(第452号案例)2.“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的判定規則。“當名義職務與實際職務範圍不一緻時”,應以實際職務範圍為标準判斷行為人是否利用了職務之便。(第247号案例)“利用門衛之職,與……合謀把貨櫃偷運出驗貨場的行為,雖然利用的是從事勞務的便利,但仍屬職務便利。”(第274号案例)“利用代理公司業務的職務之便将依據合法、有效的合同取得的單位财物占為己有的,應當認定為職務侵占罪。”(第48号案例)“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出售僞造的觀光券行為,構成職務侵占罪。”(第213号案例)“犯罪行為發生在用工合同到期日之後,但當時……在實際行使管理職責,對車間倉庫财物具有管理職權,符合職務侵占罪的主體特征。”“雖然被告人……對所侵占财物無獨立管理權,但其單獨利用共同管理權竊取本單位财物的應當認定為利用職務便利。”(第516号案例)“單位員工利用本單位業務合作方的收費系統漏洞,制造代收業務費用結算金額減少的假象,截留本單位受托收取的業務合作方現金費用的行為”,構成職務侵占罪。(第1137号案例)此外,“實踐中,單位财物的管理權、處置權有時由兩人或兩人以上共同行使,這就導緻行為人為順利非法占有本單位财物,不僅需要利用自己職務上的便利,還需要借助其他工作人員職務上的便利。行為人在犯罪過程中可能會實施多種行為,有時利用其自身職務上的便利,有時利用其熟悉作案環境等工作上的便利,甚至有的行為與職務上的便利并無關系,這就給罪名認定帶來一定争議。在這種情況下,從刑法因果關系的角度分析,應根據行為人職務上的便利對其完成犯罪所起作用的大小來确定罪名,如果職務上的便利對整個犯罪的完成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則其行為構成職務侵占罪。”(第1440号案例)3.職務侵占罪與盜竊罪的界分規則。“明辨職務之便還是一般的工作之便,在把握單位内部人竊取本單位财物行為的準确定性上具有重要意義。”“舉例而言,某單位會計擁有經手、管理本單位某項财物的職權,如其利用該職權将其本人經手、管理的财物竊為己有,即是利用職務之便竊取本單位财物,應構成職務侵占罪(如該會計同時還是國家工作人員,則可能構成貪污罪)而非盜竊罪。相反,該會計如利用其工作所提供的便利條件,竊取其他同事經手、管理的财物或竊取不屬于其直接經手、管理的其他單位财物,或者該會計的其他同事利用某種工作機會竊取該會計經手、管理的某項财物,就不屬于利用職務之便,而僅是利用一般的工作之便,應構成盜竊罪而非職務侵占罪。”(第246号案例)另,《王一輝、金珂、湯明職務侵占案——利用職務便利盜賣單位遊戲“武器裝備”的行為如何定罪處罰》(第461号案例)提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将所在單位的财産盜出後出售牟利的行為構成職務侵占罪”,與本評注所持立場不一緻,故對所涉規則未予提煉。
【司法疑難解析】
1.職務侵占罪的主體問題。實踐中,有的單位為請他人代為處理特定事項而任命職務,約定特定事項完成後該職務自動解除,雙方未簽訂勞動合同,單位也不為其發放工資報酬、繳納社會保險等費用,隻是約定事成後按一定比例提成。對此,應當認為雙方未形成實質上的勞動關系,而實質是平等的民事合同關系,單位任命其職務,主要是為了便于從事對外活動,以順利完成特定事項。對此,本評注傾向認為不成立職務侵占罪的主體。2.非公有制經濟的平等保護與相關涉企犯罪的适用。雖然法律應當平等保護公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等所有市場主體,但同時也要注意公有制經濟和非公經濟實際運行情況的差異,不能簡單地将“平等保護”等同為“同等處罰”,以真正體現黨中央提出的“以公平為核心原則”的要求。主要理由:一是根據法律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包括以國家工作人員論的人員)和非國家工作人員實施類似行為的,部分情況下後者的法定最高刑低于前者。在刑法中,主體身份往往是影響定罪量刑的一個重要情節,因為行為主體身份不同,職責不同,實施類似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和實際造成的危害後果會有大小、輕重之别,因此,在是否定罪、罪與非罪、量刑輕重上可能會需要有所區别,這也符合權責一緻和罪刑相适應的原則。二是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不平衡,大量的非公有制經濟仍是個人企業、家族企業,企業産權不清晰、經營不規範、資産處置較為随意等問題較為普遍,公權力特别是刑事司法力量深度介入民營經濟經營管理活動,是否符合當前我國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和特點,是否真正有利于産權保護和民營企業發展,能否劃清罪與非罪的界限等,還需要深入調查研究,對此需謹慎對待。三是從刑事司法實踐情況來看,與國有企業相比,對于民營企業涉及刑事訴訟的,查封、扣押、凍結措施的适用存在随意擴大、忽視民營企業可持續發展等問題,鑒此,對非公有制經濟的平等保護,還需要體現在司法辦案過程中對人的羁押性強制措施、對物的查封、扣押、凍結措施的合理使用,不能通過一味提高刑罰配置來解決。(參見王愛立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條文說明、立法理由及相關規定》,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 年版,第1012—1013 頁)
免責聲明:本号所有資料均來源于網絡、報刊等公開媒體及書籍,本文僅供參考。如需引用,請以正式文件為準。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