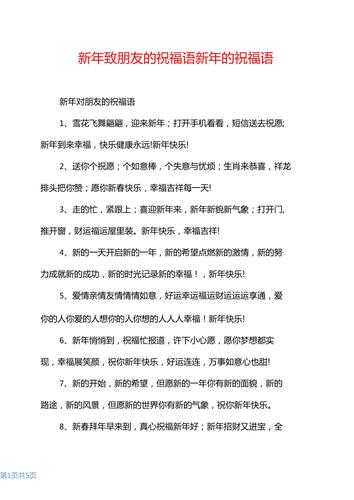蔡子谔(右四)在石家莊二中參加“詩書畫大講堂進校園”活動。 王律供圖

蔡子谔在家中作畫。記者張昊攝
他寫過報告文學,曾獲過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也寫過瓷器、服飾等專著,曾獲過中國國家圖書獎。
他無師自通油畫和書法以及刻印,加入了13個國字号協會,涉及文學、繪畫、戲曲、攝影甚至雜技。
他被業内奉為雜家。
他就是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原研究員、省老教授書畫研究院院長蔡子谔。
今年75歲的他還是閑不住。7月中旬,蔡子谔還作為石家莊市“詩書畫大講堂進校園”活動的主講人之一,走進石家莊二中為師生授課。8月下旬,河北省檔案局與蔡子谔達成收藏《蔡子谔文集》及部分手稿的意向,蔡子谔為此準備着。
雜:什麼沒琢磨過,就琢磨什麼
石家莊市平安南大街蔡子谔家。書房窗簾沒有完全打開,略微有點暗。
穿着格子上衣的蔡子谔,戴着一副眼鏡,傾着身子坐在椅子上。他的身側,一旁是頂到房頂的書架塞得滿滿當當,一旁是兩排半人高的紅色套裝書:《蔡子谔文集》。
整整30卷。
這是蔡子谔近40年來的絕大部分作品。這其中既有研究服飾文化的《中國服飾美學史》,也有研究瓷器文化的《磁州窯審美文化研究》,還有涵蓋了舞蹈、雜技、音樂等中國文化在海外傳播影響的《大化無垠》。
服飾與瓷器,雜技與音樂,各個領域都相去甚遠,一個人是如何做到多學科互通的呢?對于記者的疑問,這位河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原研究員、省老教授書畫研究院院長哈哈大笑:“我就是一個好奇的老頭兒,什麼沒琢磨過,就琢磨什麼。”
1993年前後,蔡子谔為了寫一篇關于服飾的小文章,認識了一位研究服飾的專家。交談後,蔡子谔對中國曆朝曆代的服飾産生了很大的興趣。興趣是最好的老師。蔡子谔說,服飾和中國曆代文化有什麼樣的關系,和當時的風俗有什麼樣的關系,這些他都想搞清楚,于是下定決心寫一本不太一樣的服飾史。
收集資料準備了3年,動手寫,寫了3年,校對進行了2年,這本書在2001年出版時,距離和那位服飾專家的交談已經過去了8年。
最終面世的這部大部頭共180萬字,很多人都知道它獲得了2002年第十三屆中國國家圖書獎。但很少有人知道,這背後,光是資料卡片,蔡子谔就寫了幾萬張,當時的書桌和抽屜塞滿了資料卡。
這些資料的收集,都來自于日常。
“比如說讀孟子,過去讀到一些細節,就從腦子裡過一遍,比如他說過50歲以上的人,可以穿絲做的衣裳(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50歲以上的人,身體的禦寒能力減弱,穿絲可以保暖,這就是他仁政思想的體現。首先就要把這些想法一點點提煉出來。”蔡子谔說,從海量的閱讀中,抽取和服飾有關的細節,記錄下來,為寫作打下了素材基礎。
正是這樣的積累,讓蔡子谔加入了13家國字号協會的會員:中國作家協會、中國書法家協會、中國攝影家協會……乃至中國舞蹈家協會。
已經年過七旬的蔡子谔,個頭不高,身材微胖,怎麼看也和舞蹈協會不搭界,記者提出疑問後,蔡子谔又笑,“我可不會跳,但是我研究過舞蹈。”
在作品《大化無垠》中,蔡子谔從繪畫、雕塑、民間工藝美術、建築和園林、攝影、書法、音樂、舞蹈、曲藝、雜技、戲劇、電影等十二個門類闡釋了中國藝術的海外傳播及其文化影響,這本書也獲得了第十屆中國國家圖書獎。
一個人如何做到能在如此多的領域都有涉獵,并有所成就?
“你得對生活抱有一顆好奇的心,一個東西不懂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根本不想去弄懂它。”面對記者提問,蔡子谔這麼回答。寫書之餘,蔡子谔對書法和油畫也很擅長,對鑒賞書畫作品也有一定的水準。
蔡子谔還計劃去趟聖彼得堡,為他即将開寫的新書《别樣的盜火者——中國第一批到蘇聯的油畫家》進行前期準備。“寫一部作品,不能光靠想象,我想去那一代的油畫家們待過的地方看看,收集一些素材,再回來動手寫。”
今年1月,蔡子谔剛做了肺部手術,切除了六分之一的肺葉。當記者問及,蔡子谔身體是否可以吃得消,他馬上拍了拍胸口,“我對自己很有信心,到時候就恢複得差不多了。”
鑽:隻要喜歡,就不覺得辛苦
蔡子谔的書房很簡陋,書桌上除了一盞台燈,隻有一台寫作用的舊電腦。他甚至到現在也還不怎麼會用電腦,頭幾年,寫書還要寫到格子稿紙上,再委托别人錄入電腦。
近兩年,蔡子谔學會了打字,但是盲打還做不到,要一個字母一個字母地敲。
即使如此,他每天都要到書房堅持寫作,“文集的最後一本,今年要出版。”
從1983年調入河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蔡子谔的生活就幾乎在看書和寫作中交替度過。當初,在寫《中國服飾美學史》的過程中,他給自己規定每天都要寫完3000字,除了除夕當天,就沒停過。“得管住自己,好東西是磨出來的。”
那期間,蔡子谔所住的小區進行擴建改造,入戶的裝修師傅在各家又是掄錘又是打鑽。沒多久,裝修師傅就對蔡家特别好奇起來:為了躲避施工巨大的噪音,别家都跑得遠遠的,隻有這家總是有個人關着門躲在一間屋裡不知道忙什麼。終于有一天,裝修師傅忍不住推開那扇門問蔡子谔,你難道不怕吵嗎?
“我也怕吵啊,可是沒辦法,一天要寫3000字,我跟自己說好了,不然完不成的呀。”講到這兒,蔡子谔兩手一攤,無奈地苦笑起來。
跟自己較勁,是蔡子谔的習慣。
蔡子谔年輕的時候,曾從同學那借到了一本王羲之草書字帖,因為同學要求第二天必須還,隻好連夜臨摹了一份,一直忙活到淩晨兩三點,完全忘了第二天還有一場極為重要的考試。“隻要你喜歡,就不覺得辛苦,也不覺得費時間。”
蔡子谔說,每一天,不幹點具體的事兒,都很難受。如果某一天是閑着度過的,就是找補晚上的功夫,也得補上空缺,“做學問就得有這種态度,所有的東西都是日積月累才有的。天上不會掉下來。”
蔡子谔眼下正在寫的是《印學美學史概論》,對印學的美學侃侃而談。其實20年前,對于印學他還是門外漢。
“不懂可以學啊,看得多了,琢磨得多了,自然就有了見解。”蔡子谔在手心裡寫了一個“夔”字,“比如這個字,如果刻印,字體會瘦長,不美。如果把’正’和’巳’都拉長,把底端的’夊’上提,進行美學印化,将整個字變方正,是不是漂亮多了?”
隻有中學學曆的蔡子谔能成為公認的雜家,跟他這股子鑽勁兒分不開。
當初,為了寫《磁州窯審美文化研究》,他到磁州窯去了好多趟,不僅從當地的文物人員手中,收集了很多資料,甚至連人家手裡的油印本也要帶回參考,還在寫作過程中,對磁州窯中傳統的半刀泥技法産生了很大好奇。“特别想弄明白,這到底怎麼做出來的。”
書寫了兩年多,蔡子谔對半刀泥技法的鑽研也持續了兩年多。經過反複試驗,甚至結合小時候玩泥巴的經曆,終于鼓搗了個明明白白。
在他眼裡,這種超出了寫作需要的鑽研,并不多餘。
“磁州窯的瓷器,幾乎涉及了各種裝飾,保留了民間藝人的粗犷,無拘無束地發揮中,體現出藝人的膽大心細,技法高超。有了親身體驗,再去思考這麼美的作品如何通過我的筆寫出來,不也是一件美事?”
記者追問蔡子谔,有沒有寫到一半寫不下去的作品,他擺擺手,“動手寫一個東西,就要準備好,沒有一個容易的,打算寫了,就沉下來鑽進去,總會研究出點東西。”
今年,蔡子谔的計劃也排得滿滿的,他并不認為自己退休了,就該養老了,相反,他“野心勃勃”,手中計劃寫的還有好幾個,“隻要寫得動,就想一直寫下去。因為我的興趣在這兒呢。”
趣:對一切新事物都有一顆好奇心
多少年來,蔡子谔的生活幾乎是固定的,早起溜達一圈,吃完早飯,回到家看書寫字。如果這一天沒完成當天的自我定量,他也會加班到後半夜,但總的來說,他不喜歡熬夜,“白天這麼多時間還幹不完當天的活兒,那隻能說效率太低了。”
幾乎每一個領域的涉獵,對于蔡子谔而言,都是一個偶爾機會下的深度接觸,比如畫畫。蔡子谔家,和其他退休老人的家很像,但又很不一樣:顔料、紙、書堆得到處都是。在書房隔壁,是一間幾平方米大的畫室,門口還放着他創作的巨幅油畫自畫像。
他回想起童年時,讀大學的哥哥放假回家,用鋼筆畫了一幅奧列格,栩栩如生,一旁看着的蔡子谔羨慕不已,萌生了學畫的念頭。可能就連哥哥也沒想到,蔡子谔現在油畫、國畫都能畫,在省博物院開過畫展,作品刊登在多本雜志上。
和很多作家找不到靈感需要借助香煙比,蔡子谔的生活習慣比較良好,不煙不酒,不熬夜,但他也有個不好的習慣:晚上不看書睡不着,看着看着就看興奮了,開始就書裡的内容和手頭寫的東西展開思考。“從這兒想到那兒,這一段要怎麼寫更好,那一篇怎麼發展更順暢,想着想着就睡不着了。”
有一段時間,因為晚上看書帶來的思考,蔡子谔對助眠藥物的依賴達到了一定程度,從1片的劑量吃到了5片,以至于他稍微有困意,就趕緊放下手頭的書,生怕又管不住大腦。
蔡子谔看的書,和他寫的書一樣龐雜。他最喜愛的《聊齋志異》以及書桌旁的縮印版《漢語大詞典》上,手指翻頁的位置都摸得發黑。
腿腳并不利索的蔡子谔,特意繞到卧室,從枕頭底下掏出一本《聊齋志異》。他嘿嘿一笑,“這本書讀了幾百遍,裡面的注釋都快背過了,就是覺得美。用詞精煉,描寫場景,讓人身臨其境,描寫情感,入木三分。”
捧書大笑的蔡子谔,悄悄觀察了下隔壁的老伴,繼而壓低聲音,“老伴就讨厭我進廁所,進去就不出來,我每次進去前都準備好在裡面看的書。時間久了她就喊,老蔡——”講這段經曆的蔡子谔,笑起來滿臉堆褶,像個童趣的老小孩。
已經著作等身的蔡子谔,最近在學習新詩寫作,“在學習怎麼寫更有味道,怎麼寫更有新意。”被問及為什麼還要不間斷地學習,蔡子谔撓撓頭,“就是好奇,新出現的沒接觸過的,都想試試。”
這個在多領域都有涉獵的老先生,還有狡黠的一面。除了拿社科院的工資,寫書、書法是他收入的一大塊來源,但到各地去收集材料,包括要到聖彼得堡,都需要自費前往,開銷也很大。“有人來找我寫字,我說可以的,開了一個價,對方砍價,我還讓了一點……不然就沒錢出去采風,回來怎麼寫?對吧。”蔡子谔從鏡片後頭眨眨眼沖記者笑。
請蔡子谔評價自己在各領域的成績,他眨眨眼,“從甲到乙,從乙到丙,這種觸類旁通也說明文學藝術領域是相通的。可能也是因為沒讀大學,我沒有遇到科目、領域限制的藩籬。這就像挖井,井口大了才能挖得深。或許我有一點天分,我想更多的是我比較勤奮,誰也不是一開始就做大學問,都是在實踐中慢慢摸索,在閱讀的積累中有思考,逐步形成自己的東西。”(記者白雲)
相關
探尋中國服飾的“秘密”
一部180萬字的《中國服飾美學史》,蔡子谔都寫了點什麼呢?中國曆史上的服裝變化又和社會變化有哪些關聯?
“服飾最早出現的兩個意義,分别是障和彰,障是指遮羞,彰則是彰大,為了漂亮。”蔡子谔說。
衆所周知,唐朝的服飾華麗精美,堪稱中國古代服飾之最。
“這個時期的服裝,給了古人很大的想象,反映到文化上,此時代的文學詩詞就充滿了豐贍繁複之美,最典型的就是李商隐等詩人的作品,辭藻異常華麗。”蔡子谔說。
古人的服飾,還往往配以玉飾和金銀,這也和當時的“比德”文化不謀而合。
《荀子⋅法行篇》中有這樣一段:
子貢問于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為玉之寡而珉多欤?”
孔子曰:“非為玉之寡故貴之,珉之多故賤之。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
蔡子谔介紹,“這裡的比德,就是古人用玉的特點來形容人。君子無故不去玉,可見玉在古代的裝飾作用很強,這和玉本身所具有的溫潤、純潔等特點相符。”蔡子谔說。
蔡子谔認為,古人将玉的自然屬性倫理化、審美化,将君子的“仁智行義勇”等理想道德風範和高尚人格精神進行類比,其索物托情的思維觸角,足見中國古代服飾審美文化的比德審美現象,已經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禮記⋅玉藻》載:“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锵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鸾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具體是說,君子佩玉,走路時要使玉發出的碰撞之聲,符合一定的韻律。這又将服飾和當時時代的禮儀規範結合在一起,“德佩锵鳴,顯示出中國服飾審美文化所獨有的社會倫理内涵的音樂之美。”蔡子谔說。
蔡子谔還舉例,唐王李世民的盔甲,一度用金子打造,“四年六月凱旋,太宗親披金甲,陣鐵騎一萬人,甲士三萬人。”貴金屬在古代較為稀有,為什麼帝王還會不惜重金打造金子做的盔甲呢?
“金色所反射的光是最耀眼的,這是帝王想體現出唐朝的軍威,還沒開打就能形成一種威懾,很多盔甲上的紋飾更是實用性和美觀性的結合,比如用饕餮紋,形成一種有助軍威的壓迫感,使得穿着這種紋飾的将士,通過‘移情’将勇猛轉化到自己身上,從而達到提高士氣的作用。”蔡子谔介紹。
文/記者白雲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