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附近小鎮都長這樣,和20年前的武漢差不多。”
“不,20年前的司門口不是這樣。”
◆◆◆
和從小在司門口長大的小楊,初到陽邏周邊一小鎮,我倆越過來往疾馳的麻木,望着街對面錯落的小店,她反駁我道。

司門口是不一樣的,無論你承不承認,“東方芝加哥”的峥嵘曾在此初現。
大成路與解放路一字縱橫,道兩旁的民主路聚集了各式各樣的商鋪,首飾、服裝,你講美,怎麼能不來司門口?

它最繁華,有足以匹配城市中心的輝煌時期,是在90年代。
店門口的音響開得震天響,也能聽見店員的叫賣聲,漢口、青山的班子也都愛往這兒跑,90年代線下淘寶說的就是司門口。

它摩登且新潮,這十年間,武漢所建造的商業街區,多半有意無意地,以它為藍本。
繁榮一時的光谷步行街,便是典型。

如今,“城市中心”這個詞更像一面流動紅旗,隻要努努力,大家都能上,武漢一步一個中心,卻無人提及司門口。
它垂垂老矣,事了拂塵。


司門口的石闆磚路總在翻新卻依然不規整,它記錄了這片老城區與在這兒生活過的人們的關系——矛盾的圍城,想念卻不想回來。
@小楊
考上武漢二中之後,父母為了我上學方便,一家人搬離了生活了十幾年的中華路。
回來的次數屈指可數,大多是坐在公交上,遠遠望着路邊商鋪,不知多少瓦數才能那麼亮的橘光,匆匆路過。

現在說起來有點羞恥,但是我小時候真的很喜歡去美特斯邦威。
随着微博表情包的興起,《一起來看流星雨》的土味台詞廣泛流傳,那句經典台詞總被大家拿來調笑。
“今天,端木帶我來逛了美特斯邦威,挑了很多衣服和鞋,站在鏡子前,我都不知道裡面那個女孩子是誰……”
我跟着笑,但我特别明白楚雨荨。她就是初中的我。

帶我去美特斯邦威的,當然不會是端木磊,是我媽。
周末放假,沿着解放路,從街頭到街尾。我媽愛去廣東商城,但我覺得廣東商城裡的衣服過于成熟,說難聽點,有點俗。
反正我欣賞不來。
美特斯邦威對我而言,剛剛好。店員總愛播《不得不愛》和《歐若拉》,你看它多好呀,衣服好看,歌也好聽。


店裡來買衣服的,好多是大學生,她們可以穿着自己想穿的衣服,自由地定義自己的時尚,初中的我真的特别羨慕她們。
我隻是處在青春期,她們才是青春。

@宋琦
母胎單身22年,真的不是我的問題。主要是,我家住那塊兒,不利于人找對象。

上大學之前,我家一直住在後長街,實驗小學的課間操音樂,不出意外,我應該能記一輩子。
說出來可能有點欠揍,但我真的是在帥哥堆裡長大的。
家對面是音樂學院,上學必會遇到中華路十字路口的交警,兩個字形容,周正。抖音上加濾鏡美顔的顔值,真比不上。

挺遺憾,還沒來得及早戀,我就離開了司門口。從此,被養刁的審美,再無處能高攀。
從奢入簡,難啊。

離開司門口差不多四五年了,看電影,我還是會跑回環球。對面戶部巷,旁邊青龍巷,看完不用琢磨吃什麼。
戶部巷你天天說它不好吧,離開久了,我還有點想臭豆腐和華美的五彩湯包。實在不行,一頭鑽進青龍巷,溫州燒烤走起。
回家之前,去肯德基買個冰淇淋,附近的豪客來,我小學過生日必去。什麼是排面?這就是。

之前,我不覺得司門口一成不變有什麼不好。雖然比不了父母年輕時的繁華,但也不至于落寞吧。
直到有一次我帶室友上青龍巷,買建建枯豆絲,往巷子深處走,她突然問我:“這往裡走,真的還有店開着門嗎?你是不是走錯了呀?”
那天,我才第一次意識到,在他人眼裡,司門口或許真的老了。

@阿原
住在得勝橋26年,我沒有一刻不在想——我什麼時候能離開?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NHK拍攝的深圳三和人才市場紀錄片,影片裡,深漂打工仔居住的環境,和得勝橋所差無幾,甚至這裡更吵鬧。

我家是兩層的老式居民樓,我住在二樓,與隔壁樓棟間距不過5m,一家人就擠在這幾十平逼仄的小房子裡。
明明是原住民,卻住的像個潦倒租客。

每次下雨,我很害怕。
這屋頂一到暴雨天就會滲水,我躺在床上看着雨水滴滴答答地滴在地闆上,全身都被潮濕緊緊包裹着。
每到這時,我都覺得自己好像與牆角的抹布也沒什麼不同,皺皺巴巴的。

你想象的到嗎?房間沒有門的生活。大家老在要求的“私人空間”,我從來不敢想。
夜裡為了不打擾早睡父母,我大氣也不敢出,生怕一個不小心,便會換來吵嚷到幾條街都聽見的唠叨。
家于我而言,從不是放松的地方,邁進得勝橋,便要擰緊弦。

昙華林是唯一讓我可以喘息的地方。
去年,我攢了半年的錢,買了一個二手單反。養成了沒事就到昙華林采風、撸貓的習慣。昙華林每間貓咖的貓叫什麼名字,我都記得清。
原來昙華林是真文藝。大概是14年之後,一家接一家的“文藝”小店、精品咖啡店開着,遊客和學生蜂擁而至。文藝商業化,這“真”慢慢就變成“假”了。不過,總比現在的蕭條好。

有一段時間,我看網上好多網紅、攝影師來得勝橋打卡,想要拍出黃鶴樓與武漢煙火氣渾然一體的景象。
回家的時候,我特意停在與網紅們相同的位置,停在這個我走了無數次的巷弄,看着比月色還絢爛璀璨的黃鶴樓,放空。
我什麼也沒想,但眼淚控制不住地流了出來。

說離開20年,但其實我也不知道,離開之後該去哪兒,但隻要是離開這裡,再去哪兒并不重要。
總有一天,我會搬出去的,再也不回來。


回憶美好,是因為它是回憶,沒有人想走回頭路。
但,年過半百的熊阿姨,不這麼認為。
@熊阿姨
我與先生是高中同學,畢業後成為了同事,不久又成為了夫妻。
我常聽女兒說,她朋友裡慕名去走長江大橋的情侶,沒有一對不分手的。

可我年輕的時候,幾乎天天與先生一起去長江大橋散步,日子安安穩穩過到現在,女兒都快成家了。
剛嫁來司門口的時候呀,覺得司門口什麼都好。

玩什麼、吃什麼、買什麼步行就能到,現在年輕人結婚,想住這樣熱鬧方便的地方,得花多少錢?
年輕貪嘴,總和先生帶孩子去外面吃。
一不小心被婆婆發現,她難免要念叨幾句:“家裡的飯最健康,少帶孩子去外面吃,要去你們自己去。”


婆婆這一說,我們也不客氣了,還真自己去了。拿減肥當借口,晚飯少吃點,早點出去散步。
通常走着走着,就走進了芳芳牛雜藍精靈餃子館跳跳蛙玉琬兒燒烤,光我和先生兩個人吃,不夠。還得再約上幾個老同學,夜宵吃個熱鬧。
日子一長,這減肥反倒減出了幸福肥。


你們現在坐輪渡,像旅遊體驗。我們以前坐,是不得不,和你們現在坐地鐵差不多。我想回趟民生路的娘家,隻能去中華路碼頭坐船過江。
說起來,兩段路的命運竟有些相似,極盛極衰。

因為先生的工作原因,一家人的生活重心漸漸轉到了漢口,交通方便了,我也學會了開車。這輪渡,好多年沒坐了。

如果有機會再回司門口住,我是願意的。
老城區方便,像給褲子打個扁這種小事,下樓就到,師傅手藝好還便宜,不像住新小區,難找。

況且現在婆婆還住在司門口,還有些老朋友沒搬走,若能再回到當年一起吃夜宵、打麻将的日子,也挺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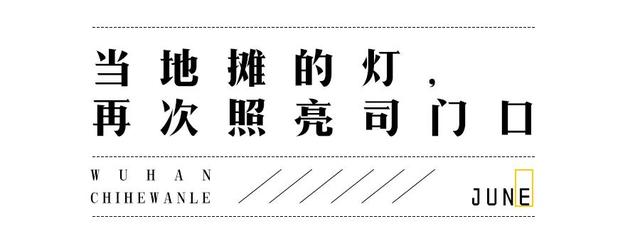
江漢路的環形天橋不見了,司門口天橋像一位堅定的錫兵,依然伫立着。

今天,重新評價司門口,“可惜”是一個想回避卻無法回避的詞彙。
拆遷的消息傳了許多年,比起懸而未決的推翻重來,眼前再次興起的“地攤經濟”,似乎像是給了司門口一次重生的機會。


“地攤”對司門口來說并不陌生。
傳聞中的司門口,由千家小店、萬家美食共同搭建的繁盛。
大成路夜市在武漢始終占有一席之地,在調侃中成形的擺地攤,從來沒在這裡消失過,隻是這一次,從暗處走向了亮光。

或許,ATM和假日樂園的小店也可以借此恢複往日人氣。希望,聊勝于無。
蒙塵的司門口,誰來拂灰?夜晚的點點星光,正照亮着它的前方。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