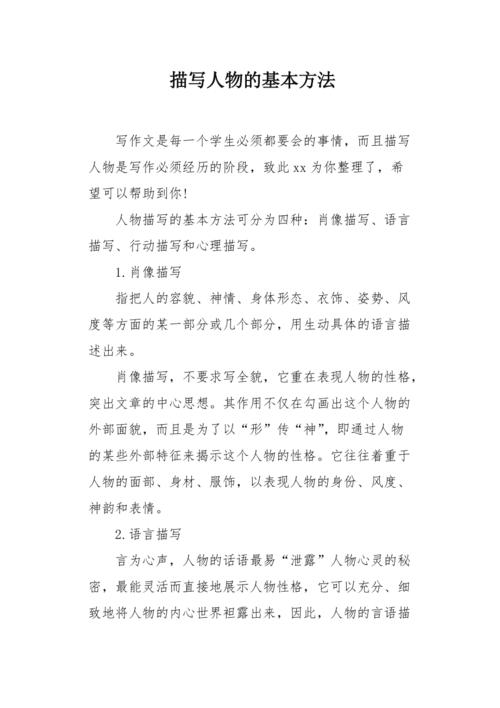文|何兆熊
出國
人生幾十年,其中總會有一件或幾件事給其一生帶來一些比較大、甚至是轉折性的變化,乃至改變生命軌迹。而對我的人生影響最大的事,莫過于上世紀80年代初我被國家公派出國進修的經曆。
1980年3月,我作為兩國外交部之間的留學生交換項目學生被派到澳大利亞進修。該項目始于1979年,第一批公派人員包括北京大學的胡壯麟、北京外國語學院(現北京外國語大學)的胡文仲、華東師範大學的黃源深、西安外國語學院(現西安外國語大學)的杜瑞清、上海外國語學院(現上海外國語大學)的侯維瑞等9名高校教師,他們這一批被派往悉尼大學。我們這一批總共8人,被派往地處墨爾本的拉籌伯大學,其中高校教師5人,我是其中之一。
記得是在1979年冬天,有一天我沒有課,沒去學校。午飯時分,我接到電話,叫我回電英語系總支辦公室,找姓曹的老師。我不敢怠慢,馬上回了電話,接電話的是總支副書記曹萃亭,他說有一個到澳大利亞進修的名額,學校決定給我,讓我下午去學校了解有關細節。
作者在拉籌伯大學留學期間在宿舍樓前留影
留學生活
1980年3月,我開始了在拉籌伯大學的留學生活。出國前,我唯一能做的準備就是把當時英語系教師閱覽室裡絕無僅有的一本原版語言學方面的著作——英國著名語言學家韓禮德的Cohesion in English從頭到尾看了一遍。我們是第一批公派到墨爾本學習的中國留學生,澳方學校對我們這批中國學生一無所知,他們感到陌生和好奇,但十分友好。澳大利亞的大學實行的是一年三學期制,第一學期我們被安排到語言中心上課。
毫無疑問,我們都以優異的成績從語言中心畢業。此時,從悉尼傳來一個消息:在悉尼大學進修的學長們開始攻讀碩士學位了。這對我們是一個觸動。研究生教育當時在中國幾乎是個空白,尤其是文科專業。經過一番商議,我們5個高校教師中的4個向校方提出讀碩士的請求。記得我們4人一起去面見教務長時,他指着幾本厚厚的、用硬皮封面精裝的論文問我們:“你們能寫出這樣的論文嗎?”說實話,那個年月,出國前我們誰都沒有做過真正的科研,沒有寫過一篇像樣的學術論文。于是校方提出要我們先在導師的指導下讀一個學期的預科,看看我們能否完成作業,是否具備讀碩士的條件。
鑒于我們4人的特殊情況,校方專門給我們指定了一位導師——來自該校教育學院的高級講師瑪塔·雷多博士。她20世紀30年代從匈牙利移民到澳大利亞,是一位哲學博士,到澳大利亞後才轉向教育學和語言學專業,主要方向是雙語教育。
第一次見導師,不知如何稱呼,她對我們說:“就叫我瑪塔吧。”
瑪塔的年齡大概在60-65歲之間,是個很要強的女性,對自己的工作非常投入。我經常聽她說的一個詞就是update,也就是不斷更新知識,跟上發展。她每天都要浏覽各種學術期刊,并且做卡片(那時電腦還沒有普遍使用),有時也讓我們幫她做,以供日後查閱或推薦給學生。由此我感覺,要做一個合格的導師,要在學術界立足,靠吃老本是絕對不行的。做一個名副其實的“學者”,做一個合格的導師,是要終生不斷作出努力、不斷提高、不斷自我完善的。
至于語言學方面上什麼課,瑪塔征求過我們的意見。那時我們對語言學這個領域知之甚少,作為教師,我們隻想學一點和教學關系密切的語言學,而不是那些過于深奧、抽象的語言學。瑪塔便根據我們的要求,指導我們在語言功能、語義、心理語言學、二語習得、語言與社會、語言與文化、語言與交際等方向去研讀。由于我們的特殊背景,瑪塔的上課方式也很靈活。她并不把自己限制在某某學科的範圍裡講課,而是根據授課過程中我們的反應、發現的問題随時修訂授課内容。為了讓學生最大程度上獲益,可以暫時放棄系統性,先把有關知識講授給學生,然後再形成系統。而形成系統的工作完全可以留給學生自己去做。她稱此為“拼盤方式”。所以,實際上她并沒有把教學限定在幾門課程内,而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融合多個領域、多個方向的“大拼盤”。
剛開始上她的課,我們這些習慣了老師把一二三都講得很清楚的學生,實在是不适應。她從來不會在我們的小班課上把某一個内容講得很全面、很透徹,而往往隻列要點、勾框架,接着就讓我們大家提問題一起讨論。每次上課瑪塔都會布置課後的文獻閱讀,她把有關文章介紹給我們,還鼓勵大家到圖書館去找更多的文獻。這其實就是研究生應有的學習方式。我們這些習慣了填鴨式教學方法的“教師學生”(teacher-student)到這時終于醒悟了。
有人問過我:“你的語用學是不是在澳大利亞進修時學的?”其實瑪塔當年并沒有給我們上過語用學這門課,實際上20世紀80年代,語用學對中國高校來說絕對是一個陌生詞,國外大學系統開設這門課的也屬鳳毛麟角。但瑪塔可以說是我語用學的啟蒙老師。到現在我還清楚地記得最早是如何接觸到奧斯汀的言語行為理論的。那天下午是瑪塔的課,她身着寬大的裙服,腳蹬高跟鞋,一手拿書,一手拿粉筆在黑闆上寫下了locutionary、illocutionary、perlocutionary(言内行為、言外行為、言後行為)3個術語。她作了很簡單的解釋,我們都沒怎麼聽懂,她大概也沒有期待我們一下子就能懂,就讓我們到圖書館去找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如何以言行事》)這本書。我就是這樣被她推進了這扇門。有時我想,漢語裡把指導研究生的老師稱為“導師”,以有别于一般的“教師”,我覺得這個稱呼很好,到了研究生學習階段,學生更需要的是被“導”,而不是被“教”。導師在課上給學生講課隻是一個方面,在研究生階段,更重要的是學生的自主學習。
瑪塔的課基本上隔周一次,每次上完課後都會布置閱讀,到下一周見面時,就要有一名同學作彙報,然後大家讨論。當然我們的閱讀并不限于她推薦的幾篇文章,還會自己到圖書館去找更多的資料,覺得有價值的就拿到讨論會上來。其中也不乏導師沒有看過的,但她不會因此而感到尴尬,反而會表揚、感謝推薦好文章的學生。導師和研究生既是師生關系,也是一種同仁關系。導師指導學生的過程也是自己學習、提高的過程。
很快就到了最後的寫論文階段,我們4個人中有兩個(包括我)選擇了語言方向,另兩個選了文學方向。選語言方向的由瑪塔指導。首先是定題,瑪塔從不指定題目,寫什麼由學生自己決定,但她會和你讨論題目的可行性。她說:“你們根據自己的興趣去定題,盡可能選我不熟悉的題目,如果你們寫的内容我都知道,那你的論文還有什麼價值呢?”此話初聽有些荒謬,導師怎麼能指導學生寫自己不熟悉的題目呢?但細想一下也有道理,導師的作用是指導學生怎麼寫,如果學生能把導師原本不懂的東西,寫到讓其能看懂,這一定是一篇成功的論文。如果都是導師熟悉的内容,學術研究還能有進步嗎?瑪塔對我們兩個中國學生的論文指導很用心,她要求我們每完成一部分就給她看一部分,而且是一對一、面對面地讨論、指導、逐字逐句修改。我還記得在她辦公室和她讨論論文的情景,時間大多是晚飯前的五六點鐘,她會備好葡萄、蘇打餅幹、奶酪、橄榄之類的食品,邊談邊吃,其實那是她部分的晚餐。雖然她的英語完全沒問題,但有一次遇到了一個語言表達上的小疑問,令我感到驚訝的是她居然說:“這個問題最好請教一下母語使用者。”可見她在學術上的嚴謹,以及對我們的負責。
如今我國的研究生制度已經十分成熟,而我所處時代的中國研究生教育還是一個空白,我有幸到國外去攻讀學位,親曆讀研的全過程,對我回國後的工作很有意義。我回國後不久就開始招收碩士生,1995年開始招收博士生,我當年的學生如果看到這篇文章,一定會恍然大悟,原來何老師指導我們的方法,都是從他的導師那裡學來的!

攝于作者的碩士畢業典禮後(1982年5月)。左為瑪塔博士,右為當時在拉籌伯大學語言學系授課的一位美國
回國
20世紀80年代,上海外國語學院的整體工作氛圍很好。從校領導到教師都熱情高漲,人人都想盡快讓教學走上正軌,重振上外在外語教學界的雄風。回到學校,我感覺人人都在摩拳擦掌,躍躍欲試,既為學校,也為自己奮力工作,每個人都想充分發揮自己的潛力。同事之間沒有太多競争和攀比,更多的是自我比較。為數不多的剛從國外進修回來的教師無疑比其他人具備更好的條件,具有更寬闊的施展才能的空間,自身的責任感也更強一些。
回國後,我立即被安排上三年級的精讀課。出國前我一直教一、二年級的基礎課,教三年級的精讀無疑是一個跳躍,困難也不小。不過憑着自己紮實的英語基礎,以及留學經曆帶給我的開闊眼界,我很好地勝任了這個工作,深受學生的歡迎和好評。三年級我一連教了9年,直到1991年底我去美國做富布賴特訪問學者。
我認為,青年教師上低年級的基礎課非常有必要,是一個很好的學習、磨煉的機會。後來我擔任英語學院院長時就規定,凡是留校的青年教師,一律從一年級的精讀課開始教起,經過幾年的磨煉後再根據個人特長考慮教授其他課程。
回國後我做的最有意義的兩件事是在上外英語系開設了兩門課,并編寫、出版了兩本相關教材。一門是給本科生開設的語言學課程。20世紀80年代,高校外語專業用外語給學生開設語言學課程的幾乎沒有。當時系裡剛從國外回來的青年教師共有3名,戴炜棟(留學新西蘭)、華鈞(留學英國)和我。我們3人在國外學的都是語言學,大家一商議,都覺得外語專業的學生應該具備一定的語言學知識,近幾十年西方語言學研究碩果累累,何不把我們學到的一點語言學知識湊成一門課呢?3人一拍即合,于是上外英語系的課程表上就增加了一門新課——簡明英語語言學,旨在給英語專業的學生介紹語言學各主要研究領域的基礎知識,包括基礎理論、發展曆史、主要原則、研究方法、應用價值,等等。
我們開這門課時手頭沒有現成教材,國外出版的語言學導論類的教材不少,但都不适合給中國學生用。于是,我們邊上課邊編著教材,參考的是我們從國外帶回來的資料和教科書,根據中國學生的英語程度和接受能力編寫。最終,我們3人合作編寫了《簡明英語語言學教程》一書,于1984年由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出版,2002年經修訂後更名為《新編簡明英語語言學教程》,2010年又出了第二版。這本适用于英語專業本科生開設學期課程的教材,因其内容覆蓋較為全面、語言簡明、難度适中,符合本科學生的實際水平而被全國許多院校的師生所接受。從1984年問世到現在,總印數已超過100萬冊,對高校英語專業的學科建設、教材建設的作用不言而喻。
另一門課是給碩士研究生開設的語用學課程。我在澳大利亞留學期間并沒有上過語用學這門課,我是受到瑪塔的啟蒙之後,自己研讀有關文獻一點點積累起來的。語用學的範圍有多大,包括哪些内容,當時還不是很清楚,哪怕是現在,語用學也不是一個邊界很明晰的學科。但在當時,我至少可以判斷哪些能算作語用研究的内容。我認為,對語言研究做最粗的分類,可以分成對語言本體的研究和對語言使用的研究。我感興趣的是後者,感覺在這個範疇我或許能夠做一些深入的研究。解釋語言使用的奧斯汀言語行為理論和格萊斯會話合作原則,當時對國内的研究生來說都是陌生的。于是我便有了給碩士生開設這門課、做點引介工作的想法,就用當初我的導師把我引進門的辦法,也把我的學生引進語言研究這塊領域。
1986年,我給上外英語語言文學專業語言學方向的碩士研究生開設了語用學這門課,現成的教材肯定沒有,我把在澳大利亞學習期間積累的文獻資料讓學生拿去複印後作為教材,上課以我講解為主,但是我已經開始注重學生的參與,要求研讀文獻、課堂讨論。
我的《語用學概要》一書于1989年出版,比廣州外國語學院(現廣州外國語大學)何自然老師的《語用學概論》晚了一年。當時國内還沒有一本比較全面的介紹這一新興學科的專著,我國的研究人員和語言專業的學生可參考的文獻資料嚴重不足,這種情況下,不論是上外的“概要”還是廣外的“概論”,都起到了把國外語用研究的主要成果向國内引介的作用,對于推動我國語用學的教學和研究具有重要意義。1989年出版的《語用學概要》隻有七章,10年後,在我的3位博士生(俞東明、洪崗、王建華)的協助下,《語用學概要》被拓展、更新為包含十章的《新編語用學概要》。由于很多院校的語用學課程是用英語開設的,不少同仁建議我們用英語編寫一本類似教材,于是2011年,我們又出版了Pragmatics一書。
我對上世紀80年代的回憶并沒有因為時間久遠而模糊,因為那個時期的記憶和改革開放緊密聯系在一起。因為那個時期的學習、工作經曆改變了我的人生。(作者系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1982年獲澳大利亞拉籌伯大學教育學碩士學位,1991年12月赴美國俄勒岡大學研修)
稿源:《神州學人》2019年第8期 未經允許 禁止轉載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