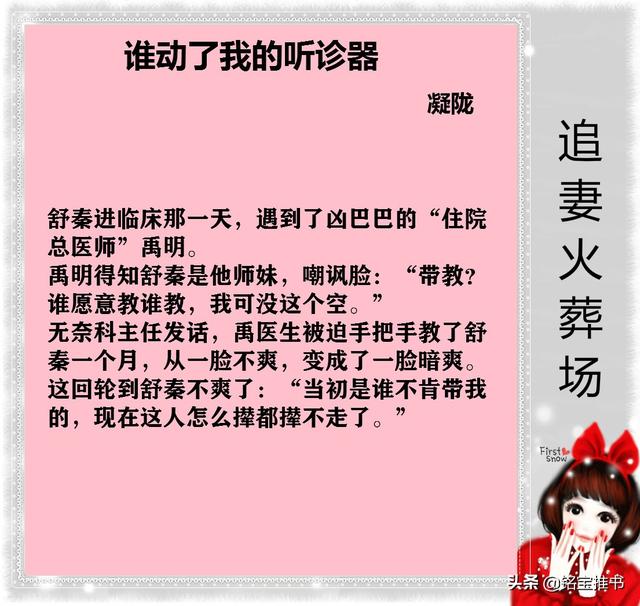以我深情換餘生小說?晚上,帶着我到廚房裡吃飯,我一動不動,拒食抗議,而這舉動迅速引起了他的不悅,他當場一把扼住我的下颌骨,“你就算常年不吃飯,我也可以吊住你一口氣,我看你能強撐到什麼時候”,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以我深情換餘生小說?以下内容希望對你有幫助!

晚上,帶着我到廚房裡吃飯,我一動不動,拒食抗議,而這舉動迅速引起了他的不悅,他當場一把扼住我的下颌骨,“你就算常年不吃飯,我也可以吊住你一口氣,我看你能強撐到什麼時候。”
他當場拿出了一隻葡萄糖酸鈣,一手掰開就往我嘴裡灌,我黑着一張臉掙紮,掙紮間,嘴唇被玻璃劃破。
他眉頭緊鎖,将液體往嘴裡倒,強行堵住我的嘴,将嘴裡的液體往我口腔裡送,順道捏住我的鼻子,液體到達咽喉時,咽喉自主做了吞咽動作。
一個遍布血腥的吻結束,他狠拽起我的手,将我摔在地上,聲音寒冷入骨,“于莫心,鬧脾氣也得有個度!我把你帶回來,不是給你受氣的!”
我下意識往小腹一摸,心裡浮起幾分擔憂,下一秒,我忽然意識到方殷還站在我身邊,猛地将手抽了回來。
可他方殷是什麼人,周圍的風吹草動都逃不過他的眼,何況是我刻意護住小腹的動作。
我猛擡起頭與他對視,他已經從包裡掏出了煙和火機,點火時頓了一下,轉身就去了陽台。
這晚我被他強從抱入了他的房間裡,什麼都沒做,靜靜地睡了一覺,次日清早我醒來時已經日上三竿,簡單地洗漱了一下之後,方殷忽然興高采烈地帶着小籠包回來。
我冷眼看着他哼着小曲兒,端着早飯走進卧室裡,将早飯往桌上一擱,走到我跟前,輕撫住我的臉頰,在我唇上烙下一個輕吻。
他眉開眼笑,“早安。”
面對他這360度的轉念,我被震驚的不輕,更是突然被打的措手不及。
一晚過去而已,難道他還人格分裂了不成?
又或者……他已經知道我懷孕了?
這個念頭一浮現,我猛地僵住。
他到底想怎麼樣?
我還沒有回過神來,他的腦袋卻已經緊湊了過來,眼底的欲火讓我無法忽視。
他忽然頓住,在離我隻有兩公分的距離處。
“莫心,我這人吃軟不吃硬,你強勢,我隻會比你更強勢。”
“以後還有無數個日夜要一起度過,你要盡快習慣這樣的生活才好。”
他說話時,溫熱的氣息撲哧在我臉上,我呼吸着他的呼吸,還有一秒就吻到唇的距離讓人禁不住的臉紅心跳。
他的手覆上我腰部的那一刻,我的心猛地悸了一下,一股難言的危機感湧上來,我下意識堆開了他。
孩子的情況還很不穩定,絕對不能跟他發生關系。
我一口将嘴唇咬破,慌亂地往後腿,随手摸起了床頭的杯子,抓起杯子往桌角一磕,玻璃杯碎裂了一地。
我撿起一半碎片,往頸動脈旁一摁,咬牙道:“你再做過分的事,我立馬就死在你眼前!”
彼時我的手已經被玻璃劃破,方殷往前頓了一步,眼底有詫異;掠過,随即有憤怒湧上來。
“于莫心,這算什麼?以死明志?當了婊子還要立牌坊,你不嫌累?”
他渾身散着冷氣,猶如在萬年冰山腳下生活了數萬年的人,“你遲早會心甘情願的爬到我床上,躺在我身下,讨好我,向我索求。”
言罷,他黑着一張臉離開了卧室。
他走後,我一個踉跄跌在床上,剛長長呼了一口氣,房門又忽然被打開,隻見方殷手裡提了個醫藥箱又折了回來,眉頭緊皺。
他走到我跟前,步伐急促,将醫藥箱往床上一擱,牽起我的手就消毒,上藥,纏繃帶。
動作溫柔又輕巧,認真的模樣映在我眼裡,我心裡莫名流過一股暖流。
這家夥嘴上不饒人,其實心裡軟的一塌糊塗。
或許是心境不同,那一刻,我差點将自己懷孕的事情破口道出,可是轉念一想,我跟淩風是最近才離婚的,如果我說這孩子是他的,他不會信。
我心裡一時五味雜陳。
眼看這孩子在我腹中待的日子一天天增加,我心裡對他的感情也一點點濃稠起來。
要不,等他出生了再讓方殷做親子鑒定吧?!
于是,我把這事埋在了心底,正琢磨着拿着方殷的毛發就離開,變故卻突然出現。
那天,我一日往常地被方殷囚禁在家裡,我老媽忽然打來電話,我剛喂了一聲,她就在對面啜泣了起來,連着叫了我好幾聲莫莫。
她在另一端哽咽,“你爸患上了重病,人現在正躺在重症監護室裡,連續昏迷了幾天,醫生已經下了好幾次病危通知書,現在需要往上級醫院轉,你……你手上有沒有一點存款?”
我焦急如焚,驚慌失措地在手機上轉了全身家當給老媽,并安慰,“媽,先讓醫生穩住老爸的病情,就算我砸鍋賣鐵,我也會想辦法!”
我抖着聲音安撫了她一會兒,最後她那邊傳來了護士的聲音,她匆忙挂斷了電話,我徹底陷入了苦惱之中。
眼看着一筆巨額醫療費擺在我眼前,我甚至動了貸款的念頭,可我沒車沒房,拿什麼來抵押?于是我在58同城逛了一天,各種瘋狂地投簡曆,可幾乎都是被秒拒。
看到搬啤酒的招聘帖子時,我看着日結薪水,定時工幾個條件動了心,可是現實無情地将我打壓,抛開肚子裡的孩子不說,就眼前來說,我根本出不了家門。
我的眼眶紅了一遍又一遍,茶飯不思地坐在家裡等方殷回來,可是我等了一天零一夜,他都沒有回來。
第二天傍晚,我終于沉不住氣,撥打了他的電話,想要告訴他,我父親危在旦夕,求他放我出去,求他借我一點錢,隻要能救我父親一命,我願意用餘生來嘗還,可是電話的聽筒裡隻傳來了冰冷的女聲。
“對不起,您撥打的電話已關機。”
我猶如深墜深海。
最終,我将牙一咬,從行李箱裡找了一間性感的衣裙,找上管家,哭着鼻子求她,“李嫂,您能不能告訴我關于方殷的行蹤,我有很重要的事情找他,我……我……”
嘴巴一憋,我立馬哭得上氣不接下氣,李嫂眉頭一皺,心疼的神色随即浮上來,拍了拍我的肩膀,“先生說這兩天要在公司趕個案子,我這就讓阿青送你過去。”
我感激淩涕地道謝,然後急急忙忙地出門,去找方殷的路上,我的心緊緊揪成一團,看着窗外眼花缭亂的夜景,我内心無法平靜。
到了他的公司樓下,我急匆匆地直奔總裁辦公室,來到了門口時,我深吸了一口氣才勉強穩住心神推開門。
可是手剛打開了門把,裡面就有女人嬌長的呻吟聲傳入了我的耳中,我腳下忽然一起踉跄,随着慣性撲進了房裡,正好看到方殷抱着一個妩媚的女人親熱。
“嗯啊……方少今天好興緻啊!看這架勢,我今晚有福可以享看。”
看的我心裡莫名一抽,仿佛有一鍋酸菜湯被打倒在心頭上。
頓時引起一陣難以言說的不爽感,之後一股卑賤感湧上來,瞬間将我淹沒。
我這算什麼?
聽到動靜,方殷将腦袋埋在女人脖頸裡微微擡了上來,将下颌往女人肩膀上一擱,看向我的目光頓時變得饒有趣味,那樣的目光,仿佛早就知道了我會來一樣。
“有事?”
我點頭。
他拍了拍那女人豐韻的臀部,對方哼哧了一聲,聲線揉媚酥骨,一看就是在男人操練到了某種境界的女人,即便我身為女人,在聽到那樣的聲音時,也還是不可自制地紅了臉。
“怎麼?大晚上穿成這樣來找我,你今晚想跟我們玩點不一樣的?”
方殷的目光直直地盯在我身上,我莫名顫栗,我緊了緊手,沒有否認這樣的說法。
自尊可有可無,腹中的胎兒,要是一個不小心大了動作,說不定也未能幸免。
方殷站起身就往辦公室裡頭的房間走。
意識到方殷是真的想來一場三人戰,我心裡開始無比抵觸,可可念到老爸的病情,最終還是膽戰心驚地跟了進去。
那女人哼笑了一聲,一扭一扭地走到我面前,伸手将我的下颌一勾,風情萬種,“一看,妹妹就是沒經曆過特殊樂趣的人,看這小臉蛋兒都白成什麼樣了。”
方殷轉過身,丢了一張金卡給那女人,“滾。”
那女人見好就收,媚笑着吻了吻卡,“要是所有客戶給錢都這麼愉快,讓我折壽三年五載我都願意。”
她道了謝就走人,順便帶上了門。
方殷坐在床上,自顧點了一支煙,眼底有毫不掩飾的得意,将我從頭到尾掃了一遍,譏笑了一聲,顯然是在嘲笑我沒穿内衣。
他在等我服務。
僵持了兩秒之後,我咬緊牙,硬着頭皮走到他跟前,伸手拿掉了他叼在嘴邊的煙,顫着手抱住了他,貼在他耳邊輕聲細語,“今晚輕點……”
他不為所動,我顫着雙手,一件件解開他的衣服,開始柔柔地吻他,不一會兒,他将我的手一把抓住,并不斷往下移,直到腰帶。
意識再下去一點就是禁區,我頓時頭腦發熱,慢慢解開了他的腰帶,恨不得像鴕鳥一樣将腦袋鑽進地裡。
一開始,方殷抱着捉弄我的态度任我鼓搗,我用盡了所有方法來讨好他,後來他被撩上火,一個反身将我壓在身下,強攻硬戰,拼命掠奪。
整整一晚上,反反複複,鮮有停頓,最後我精疲力竭地躺在他懷裡睡了過去。
次日,我醒來時,他還抱着我,我想起正事,撐着泛酸的身體爬起來,低聲問他,“方殷,你能不能借我一點錢,我爸住院了。”
我語氣近乎哀求,不敢正視他的眼睛。
他呵笑了一聲,并從床頭拿了一張支票,填了數遞給我。
“女人還是弱勢一點比較乖,早跟你說過,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我拿着那張支票,心境前所未有的沉重。
那上面是六個零,兩百萬。
對我來說,這是一筆巨款,或許這輩子都可能賺不了這麼多。但對方殷來說,卻是九牛一毛,眼也不眨就能拿出來,可見兩人的差距如此之大。
我壓下心裡亂糟糟的思緒,哽咽着嗓子輕輕說了一句謝謝。匆匆洗漱一番後便攔了個輛出租車趕往醫院,連早餐都趕不急吃。
可是到醫院的時候卻發現爸媽根本不在,心立馬無比慌亂。
我連忙掏出手機給母親打了個電話,焦急地問道:“媽,我在區醫院裡,你們去哪裡了?”
停頓了一下,母親溫柔的聲音才傳來,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錯覺,母親的聲音雖然依舊疲憊,但好似已經沒有那麼沉重憂愁了。
“莫莫,我都忘記跟你說了,今天早上你爸已經轉到史斯漢醫院治療,你趕緊過來吧。”
史斯漢醫院?
那可是A市最好的私人醫院,自然醫藥費不菲,母親哪裡來的錢為父親轉院?
我挂斷了電話,滿懷着疑惑的心情直接打車前往史斯漢醫院,在重症監護室門口見到了母親。
不過幾日不見,母親便臉色憔悴蒼白,原本還算保養得當的臉上增添了幾絲皺紋,看着老了好幾歲。
我的眼淚頓時奪眶而出,快步上前,一把摟住了母親那瘦弱的身軀,“媽,别怕,我回來了。”
母親也緊緊抱着我,滾燙的淚水滑落在我的頸部,燙得我的心揪揪的疼。
片刻後,母親的情緒才逐漸平穩了下來,我拿出紙巾為母親擦了擦淚水,視線看向了病房裡的父親。
他穿着病号服,雙眸緊閉,嘴上還帶着個呼吸機,整個人看着虛弱到了極點。
我的心裡一酸,剛忍住的眼淚,立馬又落了下來。
“爸爸他怎麼樣了?醫生有說是什麼病嗎?”
聽到我的問題,母親止住了眼淚,也看向了病房,緩緩說道:“那天你爸爸他突然口歪眼斜,我連忙把他送來醫院,結果醫生說是腦血栓,搶救了很久,之後病情一直不穩定,醫院還下了幾次病危書,我實在沒辦法了,所以才給你打電話。”
“那現在爸爸怎麼樣了?”
我心疼得幾乎快沒法呼吸了,放在身側的手緊緊攥着,這麼危急的時刻都沒能陪着爸媽,是她這個做女兒的不孝。
“醫生說你爸爸病情暫時穩定了下來,隻要度過危險期,那麼就徹底安全了。”
聽到母親的話,我一直提着的心才稍微放了下來。
史斯漢醫院是A市最好的醫院,既然醫生這麼說,那麼肯定是沒什麼大問題。
隻是……
“媽,你怎麼會突然轉到史斯漢醫院?”
聞言,母親愣了愣,連忙說道:“不是你找人将你爸爸轉到這裡,接受最好的治療嗎?是個姓方的人,說是你的朋友。”
姓方?
還是我的朋友?
幾乎是一瞬間,我的腦海裡就浮現了方殷的面容。
但下一秒我又下意識的推翻了這個想法,他真的會這麼做嗎?
可是事實就擺在眼前,不容許我都反駁,确實是方殷沒錯。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